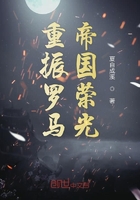每当中国陷入危殆,总能看到俄国垂涎欲滴的身影。
二十万俄军从海兰泡开进中国,把在此地做边贸的六千多中国人押解到黑龙江,强行驱赶入水。
跑得慢的全部用斧头砍杀,跑得快的多被淹死,游过江者仅八十余人。
同时,在江北的华人聚集区制造“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杀害七千多中国平民,残忍至极。
东三省相继沦陷,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盛京(沈阳)将军增祺被迫同俄国签订《增阿暂章》。
袁世凯和张之洞当即反对,慈禧也不予承认。
贪婪的沙皇对这个由地方总督阿莱谢耶夫签下的暂章亦觉不满。他同意废约,并酝酿更苛刻的索求。
俄军已打到山海关,大清分崩在即。
惶恐的慈禧急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赴京议和。
守旧派基本上都在浪迹天涯,视他为汉奸的义和团也偃旗息鼓。北上,已无性命之忧。
李鸿章闭目养神,想起前几日秘密拍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电报。
他指示伍廷芳伪造了一封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令其亲递美国总统,内称“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望贵总统作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
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对朝廷,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但对生于斯长于斯且正在沉沦的这片大陆,他又岂能坐视不理?
登船离粤前,李鸿章屏退了所有送行官员,只召安徽同乡、南海知县裴景福入见。
炎天酷暑,李鸿章身穿蓝布短衫,靠着一架小藤躺椅歇息。
裴景福恭贺道:“公调补北洋,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早已得知电报,全都额手相庆。”
李鸿章颇为得意,捋须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停了片刻,又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但慰庭支撑着山东,香涛、岘庄(刘坤一)全都有定见,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
可一谈到俄国,又无语了。
裴景福告辞欲出,李鸿章道:“船还没来,先不用忙。”
于是喝着牛奶,并以荷兰汽水待客。
裴景福又问:“公进京后打算怎么办?”
李鸿章:“洋人必会以‘剿拳匪’和‘惩罪魁’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至于数目多少,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研磨,不知做不做得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和尚也就死了。”
言讫,泪比司马青衫多。
裴景福亦怆然涕下,辞别而出。
途经上海,李鸿章特意下船去了盛家花园,同盛宣怀彻夜长谈。
灯火明灭,月光黯淡。此情此景,竟比三十年前曾国藩和赵烈文的那场夜谈更显凄切。
临别之际,李鸿章给盛宣怀留下六个字。
和议成,我必死。
一国且不好谈,况八国乎?
更悲催的是,此番俄国铁了心要吞并东北。瓜分之祸,迫在眉睫。
感谢美帝
若非门户开放政策,二人转已失传一百年。
这套由赫德提出、美国力推的政策主旨有三条:
一、各国彼此承认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如租界和通商口岸);
二、中国关税自主,对运至诸通商口岸的各国货物征收统一关税;
三、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只,各国不得收取高于本国的港口税。
门户开放并非历史教科书所写的那样罪不可恕,至少在当时的绝境下拉了清廷一把,使之保全领土,免于分裂。
比如俄国想独吞东北,势必侵犯日本在这一区域取得的既得权益,遵循政策的列国便会起而反对,使之作罢。
当然,国与国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善男信女一说。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不是美国的义务,而是手段,其目标非常纯粹:商业利益。
在美国看来,觊觎中国的领土完全是不成熟的表现——占了又不好管,还成为众矢之的。而只要大清臣民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能保证本国的纺织工人不失业。
可惜,美国到晚了。面对这块快被分得差不多的蛋糕,山姆大叔焉能坐怀不乱?
因此,门户开放就是帮迟到的美国享受利益均沾的政策。不管先来的人开了多少埠,占了多少租界,只要在这些区域能保证我自由贸易、公平交易即可。
归结到底,战争的背后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
第一个表态支持门户开放的是英国。
作为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在华利益最多,最担心后到的土鳖因为没谈拢,在英商遍布的神州大地上火拼,导致几十年来胼手胝足积累的赃款丧失殆尽。
对日本来说,百年大计,防俄第一。只要能绑住俄国到处乱摸的咸猪手,自己哪怕少得点也认了。
当然,再明白无误的事也需要人去推动。李鸿章指示驻外使节四处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之以种族感情,对英国许诺保护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
离间的结果是:除了俄国,列强均对门户开放政策表示同意。
孤立的俄国把希望寄托到李鸿章身上,毕竟签过《中俄密约》,时论都以为老李是亲俄派。
打定主意后,俄国开始演戏,向各国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将撤退到天津,恭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
摆明了拆列强的台。
并向慈禧抛去橄榄枝,抢先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放弃东北,意味着放弃清廷列祖列宗的陵寝之所在。慈禧再自私,也不敢行此不忠不孝之举。
李鸿章一到天津,就被俄兵保护起来,关着门不知搞什么暗箱交易。
等重新亮相时,列强都很紧张,以为他同俄国达成了“慕尼黑协定”。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谁让大清国实力不济,只能玩以夷制夷的把戏?
李鸿章的腹案是:把中国从交战国打造为受害国。
故事梗概如下:拳匪是叛贼,两宫被劫持,宣战诏书是矫诏,八国联军来助剿。
按此逻辑,联军将领全成了李中堂的戈登将军(李鸿章早年打太平军时雇佣的洋枪队队长),而中国对“国际维和部队”固然有赔偿军费的义务,却不再承担其他责任。
跟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鸿章,一在谈判桌上坐下,便拿出一本《摩西十诫》,讽刺洋使道:“我建议,应该把第八条戒律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
纵横捭阖下,议和条件还算温和,无非谢罪惩凶、改革总理衙门等,既无割地之虞,慈禧也无归政之忧。
当然,赔款纯属漫天要价,四亿五千万对应当时中国的人口,一人一两白银。
这么损的赔法确实有辱国门。
张之洞强烈反对,搞得李鸿章很被动。在给朝廷的电报中,他讽刺道:“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反唇相讥:“少荃(李鸿章)议和三两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浑然一副绝对。
李鸿章正色道:珍惜银两,从我做起。电报昂贵,四钱一字,不要动辄发表空洞的长篇大论了。
英美怕中国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仲裁法庭仲裁核算,因各国激烈反对而作罢。
至于惩办祸首,洋人开列的黑名单第一位原本是慈禧,在李鸿章的力争下总算一笔勾销。
余下诸公,也就没有兴趣保了,甚至巴不得列强多杀几个这样颟顸愚蠢的始作俑者,以警示后人。
载漪及其子溥儁充军,载勋、赵舒翘赐自尽,毓贤处斩,刚毅在西逃途中忧惧而死,端王党团伙的其他成员或削爵或圈禁。
西太后的保守派班子凋零殆尽。
虽如此,当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与奕劻将条约内容电奏西安时,慈禧还是大悦——竟然不用归政,竟然寸土未失。
逢凶化吉,盖有两端:英美为了自身利益帮清廷看家护院;东南互保替中国解除了交战国的身份。
因此,国际上并没有“辛丑条约”这么一说,正式名称翻译成中文很长:中国就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的议定书。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庚子之变给每个大清臣民的心头都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
北京街头的“义和昌”“义和泰”等店面招牌一夜之间杳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德占区的“德兴”“德长胜”等字号。
平民冒充教民、日本人的奇闻怪事数见不鲜。俄国占领东北后,一些文人士子对“全归俄制”高兴至极,甚至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
1903年,齐白石初游北京,记下了触目惊心的一幕:
洋人往来,各持鞭坐于车上。买卖小商让他车路,稍慢即以鞭乱施之。官员车马见洋人来,亦早早避让,庶不受打。几个国人侧立于大清门侧,手执马棒,保护洋人……
1905年,周作人游北京。浓重的阴霾仍然笼罩在京城上空,不肯散去:
初来乍到,我们好奇,向客栈的伙计打听拳匪的事。他急忙分辩说自己不是拳匪,不知其事。我们不过是问他当时的情形罢了,岂料他却如惊弓之鸟,讳莫如深……
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了一个包车。车夫承认自己以前当过拳民,但其时已是一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家里供奉着圣母玛利亚像,早晚祷告很是虔诚。
钱玄同问他何以改信宗教,车夫的回答穿透了历史的尘埃:
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
我们的菩萨从来不关心信众的死活,倒是热衷于将他们绑架到权力斗争的战车上,乐此不疲。
拜毓贤所赐,山西曾是义和团的天堂,传教士的地狱。而庚子之后,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地方官将办理教案当做第一要务,以教民之意为圣旨,随意捉拿“拳民”。更恶劣的是,辛丑年山西闹灾荒,地方政府只赈济教民,无视平民,坐看其自生自灭。
结果,连曾经的反洋急先锋义和团的团头们,也纷纷入了教,理由非常讽刺:不受辱,不受气。
晚清最后十年,中国的天主教徒激增了一倍,达到一百三十万之众。
不知上帝在云端作何感想?
列强陆续撤军,俄国赖在东北既不合情理,也面临各国施加的外交压力。
1901年10月,俄使向李鸿章提出以道胜银行的名义办约,掩人耳目,遭到拒绝。
俄人不断催逼,七十八岁的李鸿章内外交煎,连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西医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直隶布政使周馥在病榻前悉心照料,曾听到探访之人劝李鸿章保荐直隶总督的人选。
李鸿章默然半晌,道:“继任有人在,我不想保举罢了。”
周馥清楚地记得,老头说话时,愣愣地望着窗外。
那分明是山东的方向。
1901年11月7日,“内悦昏君,外御列强”了大半辈子的李鸿章撒手人寰。
身高一米八三的他,与伊藤博文、俾斯麦一道,被西方人并称为“当世三杰”。一生写了两千六百万字,堪称劳模的他,却在中国这个动辄得咎的老大帝国,刷新了被人弹劾的纪录(八百多次)。
他是第一个拍X光片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撰文介绍蒸汽机的科普作家。
临死前,俄使仍伫立床前,逼他画押,遭到拒绝。
毛子丧气而去,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
李鸿章一边哀叹“毓贤误国”,一边让于式枚代拟遗疏,鼓励慈禧振作发奋:
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举行新政,力图自强。
恍惚中,他忆起二十岁上京应试时的情景。
彼时的大清,刚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但在文人士子看来,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天朝仍然具备万国来朝的实力。
李鸿章亦作此想,连写了十首《入都》,其中一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颂。
谁知,灾难一开始便收不住脚,插曲竟是序曲,悲歌一放六十载,直至曲终人散。
一个甲子宛若一道轮回,在生命的尽头,李鸿章带着无尽的遗憾,口占一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贤良寺,落叶秋风,寒鸦聒噪。
周馥发现李鸿章断气时,只见他“双目犹炯炯不瞑”。
慈禧在行宫收到周馥的电报,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少了这样一个“安危系之,存亡系之”的中兴名臣,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黄花晚节,重见芬芳。李鸿章身后哀荣无限,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谥文忠、入祭贤良寺。
能给的都给了。
直到1908年,李鸿章去世的七周年祭日,《纽约时报》还出专刊纪念道:“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
也许,只有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的评价最为掷地有声: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