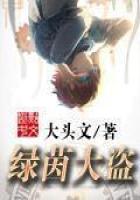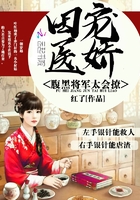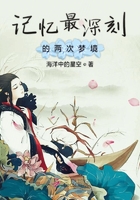詹姆斯·威廉·黑尔《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如果他(江忠源)活得长久一些,能够参与后来的战争,他的名字肯定会排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列,或许还是排在第一个。他的工作为后来曾国藩更为引人注目的作为奠定了基础。
一脉相承的事业
江忠源步入官场以后的人生轨迹,表明曾国藩识人有术,预言不虚。他在刚认识江忠源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位新朋友由性格决定的宿命,注定是铁肩担道义、忠心洒热血。江忠源死后,曾氏相术因为得到了验证,传得神乎其神。事实明摆在这里,江忠源正是曾氏所说的性情中人,湘南淳朴的民风哺育的磊落汉子。由于豪侠仗义,他的生命只过了四十二个春秋,就过早地终止了。
曾国藩喜欢江忠源,欣赏他的诚实坦荡,却又希望他收敛一些落拓不羁,劝他戒赌戒色,试图把他塑造为儒家道德模子里的文明人。江忠源愿意皈依曾氏理学的教化,但他骨子里仍是一名随性而为的侠士,而不是儒学礼教的完人。他乐善好施,不计个人得失,是出于至情至性,而不是为了遵循任何一个道德学派制定的行为规范。
一个侠士要为民除害,为社会造福,必须是一个行动派。江忠源会考不第,便不打算再把时光虚耗于寒窗苦读。社会动荡的前兆令他兴奋不已,催促他积极地行动起来。在一个沉闷到令人窒息的社会里,只有一场大规模的动乱才是大显身手的机会,而江忠源看到了动乱的前兆。他回到家乡,投身于维护社会治安。他组织民间武装打击盗抢,然后击败了雷再浩的造反,凭着这种社会实践,彰显了他生存的价值,踏入了仕途。他在浙江担任基层官员,按照自己治国安邦的理念,挥洒自如地办了几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江忠源在浙江秀水的作为,清晰地勾勒出他的为政之道。清廉自律,是他追求的品格;缉捕大盗,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劝捐赈灾,采用特殊的手段,就是变相惩罚为富不仁,颇带杀富济贫的色彩;兴修水利,劝耕劝农,是为了消除贫穷,改善民生,澄清民风。
他的作为给他带来了名望,他本来可以青云直上,在更大的行政区域内施展抱负。然而父丧中断了他的升迁之路。他回到家乡,经世济时的热情却未稍减。当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的时候,得到赛尚阿的一纸调令,他就带孝从军,积极投入到规模空前的内战中。
江忠源带领一支小部队,给官军注入了积极的因素和新鲜的理念。他自从戎之后,总是力主攻击。从永安到道州,他呼吁全力合围,全歼洪军;从郴州到长沙,他向高官们力请攻剿,毕全役于一城。但他人微言轻,兵力单薄,跟随官军主力尾追洪秀全,参与围城的防守。在防御战略节节失利的情况下,他充其量只能成为防守战中最有用的一颗棋子。于是他守了南昌守田家镇,守了武昌守庐州,最后毙命于破亡的临时省会。
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基本战略只有两种,就是攻与防。咸丰作为最高统治者,理所当然会倾心于进攻性的战略,也就是他所说的“痛剿逆贼,歼除丑类”。他希望臣子们能够忠实地执行以剿为主的积极的战略方针。但是从前线大员到宫廷谋士,不论文职还是武职,都落入了防守围城的窠臼,不是退守重点城市,就是跟在太平军后面尾追,几乎无人实施主动攻击和积极围剿。江忠源和左宗棠跟咸丰有着共同语言,但他们都是说不上话的小人物,只能郁闷地在大人物们划定的轨道上运转。左宗棠不愿奉陪下去,选择了放弃,得以全身而退,而江忠源则成了保守战略的牺牲品。
江忠源的攻击理念未能如愿以偿,但他即便困守围城,也会主动向城外出击,也许这便是咸丰对他最欣赏的地方。咸丰三年是内战开始以来清廷最为狼狈的一年,林凤祥把战火燃到了天子脚下,赖汉英和胡以晃回攻安徽、江西和湖北,官军几乎调动了全部精锐,仍然应对不暇。败报迭传,官心沮丧,咸丰祈祷上苍,渴望能人横空出世,挽救颓局。果然,官军中涌现出两员大将,独领风骚,堪称骁勇,他们就是民间所谓的“南江北胜”。
江南的江忠源和江北的胜保,是咸丰三年满清帝国的骄子。如此的盛名,江忠源当之无愧,胜保却纯粹是由于幸运。他在此年刚刚投身军旅,起点很高,部众不少,也未见他打几个像样儿的胜仗,怎么会与江忠源相提并论呢?
首先因为,胜保是满人将领。咸丰急于在自己的族类中树立一个正面的典型,看到胜保自告奋勇上前线,欣赏他的勇气,对他青睐有加,决定破格提拔。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那就是胜保一直处于攻击的地位。自领兵以来,胜保未曾防御过一座围城。他统兵来到扬州城下,打的是攻坚战,虽无骄人的战果,却也算得上主动。离开扬州以后,战开封、救怀庆、攻临汾、打洪洞,最后追着太平军来到天津,对峙于静海和独流。尽管他所谓的“攻剿”,在许多情况下也只能算作尾追,但他毕竟撵着林凤祥跑了一路,勉强算得上“攻剿”。这就很对咸丰的胃口,于是不断地提拔他,让他当了钦差大臣,总统北路官军。咸丰并非不知道,胜保对付的只是太平军人数不多的北伐部队,而他统帅的官军兵力远远超过对手,他却未能将林凤祥歼灭在黄河以南,说明他比其他满人将领强不了多少。但是咸丰对胜保仍然寄予很大的期望,有些自欺欺人。因此“南江”不是虚名,“北胜”却有些水分。
江忠源是太平天国在运动初期的真正劲敌。许多人给他贴上“儒将”的标签,其实他更注重建功立业,报答赏识他的君上。由于对清末军政形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把自己的想法很快地付诸实施,迅速地从基层脱颖而出,给北京的统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行为具有开创性,为后来的湘军巨头如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等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他尊为老师的曾国藩影响尤大。
杰出的美国汉学家威廉·詹姆斯·黑尔如此评价江忠源的去世和他在晚清这场内战中的作用:
这个不幸的事件使帝国失去了一名最杰出的将军;尽管江忠源因早夭而未能登入中国的名人堂,但他首次在广西显示了民兵在镇压造反者的战争中所具有的价值。他在蓑衣渡改变了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为湖南的省会部署防务赢得了时间,无疑是他拯救了长沙。在长沙被围期间,他指挥自己的小部队为这座城市的防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启发了曾国藩按照同样的模式组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创建了一支水师在华中的水道作战。如果他活得长久一些,能够参与后来的战争,他的名字肯定会排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列,或许还是排在第一个。他的工作为后来曾国藩更为引人注目的作为奠定了基础。
江忠源并非不懂得自己为什么会吃败仗,他是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他的性格驱使他勇挑重任,不顾生死安危,哪里艰难就到哪里去。眼见着亲信的楚勇已经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他却不愿停下来招募训练新勇,就匆匆投入几乎无望取胜的战斗,终于独臂难支,在胡以晃的进击下兵败身亡。
江忠源在晚清历史舞台上的表演有如昙花一现,他的热忱烧光了他的生命。燃烧的余晖照耀着湖南的书生,为他们指明了建功立业的道路。他组建和训练楚勇,开以勇代兵之先河,率领劲旅转战四省,直接影响了后来湘军和淮军统帅的建军事业。他在咸丰和曾国藩都对以勇代兵的做法怀疑动摇的时候,极力打消他们的顾虑。他以亲身的经验奠定了湘军的建军原则,倡导湖南的乡勇以“忠义血性”的书生为将领,招募缺少心眼的山农为部众,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兵归将有的原则,把家长制的管理方式引进军队。但他自己却没有将这一原则贯彻始终,在兵力不足、兵员不精的情况下勉力守卫庐州,导致他匆匆地结束了军旅生涯,这对后人也是一个警示。
江忠源以书生带兵,挑战职业将领的素质。在与太平军作战的官军大将中,提督向荣名重一时,江忠源却看不起这个人。曾有人问他:“乌兰泰和向荣比较谁更优秀?”他回答说:“各人看法不同吧。我觉得乌公忠勇,而向公工于心计。以永安战役为例,乌公是南路总指挥,向公是北路总指挥,向公网开一面,让洪贼逃脱了!其他就不必说了。”
那人又问:“向公是享有盛名的大将啊,这是为什么呢?”
江忠源叹息道:“这是因为,向荣还懂得征讨贼寇是自己的责任,比其他将领强了一些。天下实在缺乏人才,可叹可叹啊!”
咸丰深感官军中太缺江忠源这样的干才。如果朝廷的军队中多几个江忠源,他就不会过早地死去。江忠源在实践中发现了清末军事组织的弊端,向咸丰如实奏报。《清史稿》认为,这是关系到清廷成败大局的谋略。江忠源意识到了水师的重要性,并且实地摸索,对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具有启示作用。
江忠源不但自己带兵打仗,还把三个胞弟和两个族弟领上了战场。他的胞弟江忠浚、江忠济和江忠淑,族弟江忠义和江忠信,先后跟随他从军。江氏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这种做法形成了示范作用。罗泽南率领门徒从军,曾国藩把几个弟弟带出家乡建功立业,都跟江忠源一样,成为“一门忠义”。
新军即将上阵
江忠源战死庐州前后,曾国藩加紧在衡州组建和训练新军。这支新军的组建,最初的动机是为江忠源提供有用的兵力,而最终的动机也是配合江忠源南北夹击。同时这也是咸丰皇帝的战略性安排。所以,曾国藩和江忠源的事业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江忠源死后,曾国藩能否崛起,将对咸丰年间的军政格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曾国藩用于建军的时间并不算长,本来有望于实现江、曾联手的格局。可是前方的战局发展太快,曾国藩一时还无法对战局施加影响。
在湖北战场,太平军只是短暂地撤离武汉,随后溯江而上,再次攻陷黄州。曾国藩写信给吴文镕,请他挺住,并强调湖南、湖北两省要以坚守省会为主,必须等到他的水师建成,才可以发动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