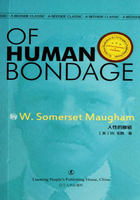那一夜我没有回家,而是来到了哥哥家。对于我的登门,哥哥稍显意外,之后便是平静,兄弟俩温了一壶酒,一边相对慢慢地喝,一边谈了最近各自的情况。我把自己在关城开洗煤厂的事告诉了他,他听了沉吟了一下说:“能不能停了?”
我有些不解,哥哥从来没有阻止过我在事业上的发展啊。
见我不语,他叹口气又说:“关城,已经失去太多太多了。譬如说吧,你走上了邪路,如今虽然重新归来,但毕竟让人伤神。”
我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悻悻地端起酒杯说:“哥,咱还是喝酒吧。”
哥哥看着我,我想他心里是很痛的,知道他并不想提及此事。我好不容易才从过去解脱出来,连父母都开始回心转意了,他又何苦再刺激我呢?但是有些话堵在心里他不吐不快。虽然为政一方,他却是无奈的,在关城煤事上,他没有发言权,有的只是满腹牢骚。今天我又提到煤,正好落到他的枪口上,他突然说:“停了,关城人会少些磨难的。钱并不能给关城带来更美好的明天,有时,贫穷却能让关城沧桑而美丽。”说完激动起来,走到暮色笼罩的窗前,忽地把窗户拉开,冷风刷地一下吹到酒劲上涌的我的脸上,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而直面寒冷的哥哥却纹丝不动。
哥哥动情地说:“关城是什么?历史的积淀,文明的负载,它的美就在于它的厚重。这里诞生过多少传奇,更让多少代人活得安宁自然,把历史当成垃圾可耻更无耻,有多少外边的人,向往关城这块饱经热血浸染的土地时,这片土地本身的主人却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了。你想想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关城出了多少富人,又有了多少穷人。那些富人是依靠什么富的?是依靠豪夺劫掠、依靠乱采滥挖。违背资源贮存规律和煤炭开发规划,任意划块抢注煤炭资源探矿权和采矿权,使宝贵的优质煤炭资源得不到综合开发和合理利用,在盲目分割之下进行无序开采。就说停水的事吧,表面上是窟野断流了,可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你眼下想要用来发财,想要用来翻身的煤炭。你想想看,连你这么个曾经落魄了的人都企图由煤来翻身,那些小老百姓又何尝不去想呢?这个想煤,那个也想煤,种地的不种地了,工作的不工作了,有些官员一直凭‘干股’分红。不光本地人挖,外地人也来挖,90年代初关城的煤炭产业开始起步时,县城常住人口不过五万多人,现在已经超过了二十万。目前,整个县里有二百多家煤炭企业,在夜以继日地挖煤,导致地下水发生大面积渗漏,不少井泉下漏、淤坝干涸、树木枯死。今天断流,明天就会风沙,后天就会荒漠,再往后就是无人区,这就是关城的结局。这不是悲天悯人,而是不可规避的事实。不否认挖煤增加了县财政收入,但那收入是带血的,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拍着良心问一问,挖完了煤你们还想挖什么?没有了关城你们以何为家?所以,还是把那点靠煤炭赚到的血汗钱省着点花吧,考虑好了再花吧。也别让那些腰包鼓鼓的煤老板们都拿着钱去好活了外国和外地,或者埋在地板下沤了粪,给他们找点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别让他们把钱都糟蹋了,也给关城这块土地这些人留下一点吧。如果谁能把古城工业园区搞起来,把卖原煤和焦炭延伸到化工方面,减少煤炭用量,增加下游产值,那么,他就绝对值得关城人尊重。但是,如果他急于发财,以机械化的手段把大量的祖宗资源廉价卖掉,让后人在煤炭价格更高的将来挖无可挖,卖无可卖,还不如把煤炭继续埋藏在地下的话,那他就会成为关城的千古罪人。谢达啊,你明白不?”
我目瞪口呆地盯着并没有喝多的哥哥,脑子里只有一个疑问,这话在他心里憋了到底有多久了?那一夜,我们无话不谈,交心良久。在我的心里,又有了新的想法。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在一首老情歌里,我的神思开始飘摇,不由自主地扭头看着身边的雪凝,发觉她是那么沉静平稳,仿佛活在世外,仿佛早已相隔永恒。自从回了一趟关城,她就这副模样,对我总是不理不睬,弄得我也搞不清她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或者随着时间的飘移,她会跟我说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关城可能给了雪凝很多自己不知道的负担。
那一夜,我跟哥哥提及雪凝,哥哥说:“相见即是缘,相爱即是分,有缘有分足矣。你是个重情分的人,这很好,但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一定会有结果的。你和雪凝,随遇而安吧。”
我猜,哥哥一定是听到了一些关于雪凝不好的传闻,毕竟作为关城有名的美人,雪凝一向是人们关心的话题。而且,她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风尘,可那些都是她情非所愿的。这个世道,男人如果不是坏到极致,只要稍稍表现得好一点,人们就会用一句“浪子回头”来形容。可是女人呢?错一步就一生错。这也是雪凝不愿意回关城的缘故吧,从回关城路上她异样的表情就不难知道。我很想向哥哥解释点什么,但被哥哥阻止了。
哥哥说:“我不是说雪凝不好,我也愿你们好。我只是说,你们一定要把你们自己之间的阻力估计得足足的,然后再考虑是否走到一起。毕竟都是成年人了,有很多事情不能感情用事。”
我一块心石落地,想只要你们不阻拦就行,我们之间哪有什么阻力啊。想到雪凝在床上的疯狂,在商场上的凶猛,在感情上的温柔体贴,我的心又软软的,一片春回大地的烂漫。脸上明显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样子,哥哥知道我这一回是真的陷进去了,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转移话题。
如今,我已经是事多人忙的人了,各样事务都得亲自打点,所以很快又进入了工作狂状态。
王玉民的表弟打来电话:“老板,关城变天了,你凑热闹来不?”
我莫名其妙:“我刚从关城回来没几天,不是好端端的吗,有什么天可变?”
王玉民的表弟幸灾乐祸:“整顿啦,收摊啦,大家伙儿该散啦,乱着呢。”
我怒道:“再不正经,扣你这个月奖金。”
王玉民的表弟嬉笑道:“别这样,老板,是真话,你赶紧看看省里刚下达的煤矿整顿文件,看对咱影响究竟有多大。”
我倒是听说了有这么一个文件,这种整顿性的文件经常下达,但多是换汤不换药,不伤筋不动骨的那种。我从关城一回来就忙着为电建公司这方面的事跑路子,所以并没有去留意。
听见王玉民的表弟的语气,我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便赶紧找了一份来看看,充分领会了其中的核心意思,就是要求关闭所有的私营煤矿,不允许私营矿主再经营煤矿,由国有大矿兼并。文件下得斩钉截铁,看来省里要动真格的了。
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关城那条不堪重负的省级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蒙着棚布的大煤车,像一只只蜗牛一样吃力地爬行着。路是残破的,开车的脸是黑的。沿途村里的老百姓就去路边扫那些撒落下来的煤屑煤块,竟然多的不仅自己再不用买煤了,而且还用不完,一辆辆拉出去卖。老农民卖煤还情有可原,而有些卖煤人就值得推敲了。
有一回,我去关城洗煤厂看煤,那边与我接洽的老板居然是初中老同学,名片上堂而皇之地印着“煤业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我看着名片开玩笑道:“屁个法律顾问,我还不知道你们的猫腻?说吧,贪污了多少,占多少股份?”初中时候,我们两个人处得还不错,属于那种非常纯净的感情,所以我敢这么开玩笑。
老同学遮遮掩掩地说:“顾问?哈哈,顾问。顾上了问问,顾不上了就不问。”
我摇头道:“哪可能不问,那是哗啦哗啦地响啊,不问怎么能行?”
老同学依旧风扇似的摇头:“不敢胡说,咱可是清正廉洁的。”
我哈哈一笑:“是吗,属于能送匾的那种?回头,我也给你送一块匾。”
老同学一本正经地笑:“匾倒没有,锦旗不少。你老哥我办案很厉害的,你不懂。”
懂不懂关不着我啥事,既然是老同学,说话好商量,谈价码的时候,我便死劲地宰,没打算多给他空份儿。两个人打算着细水长流的买卖,毕竟我这里出货快,要煤量大,所以谁都没把这事当事儿,回头送煤的照样送,要煤的照样要。本着你情我愿公平交易的原则,一晃就是大半年。
其实我非常清楚,这位同学绝对没有在煤上投一毛半分,的确干干净净的,可这挡不住那个托兰托煤业有限公司,少不了要送他干股的。当然也是见怪不怪,像老同学这种有身份的产、售煤者在关城比比皆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各路人马也没事找事,成天往矿上跑,“我们浑身的口袋里都插满了手”。一次我到矿上进煤,那个资产高达数千万的煤老板,晃着手里几百块钱的小灵通说:“瞧见没有,不敢拿好手机,我好几个高档手机,都让领导刘备借荆州借去不还了?”
整个关城从上自下,都因煤而躁动着。本着羊群效应的铁律,既然大家都是如此,自然也就大傻不笑二傻了,一个个都心安理得得很。
我也心安理得,只要不影响挣钱,只要不用做违心事,我一个平头老百姓哪管得了那么多。不过,有一些事还是对我触动挺大的。
有一回我往关城赶,进入山区路过一个矿,正在路上行驶着,突然前边“轰”的一声巨响。直感觉地动山摇。地震?滑坡?把我吓了一大跳。赶紧把车停到路边,却看到有人站在山头上往下扔东西,“轰轰轰”的,碰着什么都炸得四分五裂,灰烟飘起。而路上有人正朝上放鸟枪,“砰砰啪啪”的,那些轰然爆炸的家伙都是土制的炸弹。不能惹事赶紧躲,我开车绕道而跑。过了两天才知道是两伙盗挖煤的团伙因为争地盘相互干开了。
其实,类似事件在关城早已屡见不鲜,最疯狂的一段时期,关城处处皆盗洞,村村半夜挖煤声,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缺水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表现罢了。正是这种掠夺性的私挖滥采才使省里不得不痛下决心,要治理整顿煤炭产业,阻止结束私营矿主的肆意妄为,由国家来管国家资源。
说实话,作为一个十分期待关城有着美好明天的,与之有着血脉相连关系的企业家,我是非常愿意乐见关城好起来,这一整顿或许是难得的契机。从省里整理整合煤矿的决心,我敏感地预感到风雨要来了,有天晚上躺在床上,两个人谈起此事来:“雪凝,我想把洗煤厂停了,改做别的。”我想听听雪凝的意思。
“想关就关吧,你的钱可以随时抽走。”雪凝说。
“我的钱还不是你的?我不是要抽我一个人的,是咱们干脆不办了。”
“要走你走吧,我不走。”
“这不是赌气的事,咱们好好商量一下,我觉得这次整顿非同小可,我们如果还继续干,就可能尝苦果了。”
“我们在一起还是尝苦呢。”
“你怎么这么说话?”
“谢达,有件事,我一直在等你给我一个答案,可是我等了这么久,你到现在也没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雪凝突然翻身坐起来,逼视着我。
“我有什么事没告诉你啊?”我十分不解。
“为什么你一定要在关城开洗煤厂,为什么你一直瞒着不告诉我?”
“唉,原来是这事啊,”我不知怎么说好,“我是觉得等搞好了再告诉你也不迟。我真不是故意要瞒你什么。”
雪凝摇摇头:“我可以与你同甘苦共患难,但我容忍不了一个人的欺骗,哪怕是一点点。男人只要有一次欺骗女人,那么就会有许多次,我无法想象咱们今后是什么样子。谢达,我们分开吧?”
我目瞪口呆,像遭了雷劈。
雪凝见我不吭声,又说:“我不是意气用事,我想了很久了。谢达,我们分开吧,也许一段时间后,我会想通的。但这会儿,我无法原谅你……”
我糊里糊涂地问:“这都什么啊,至于吗?”
雪凝知道我的意思:“我就是这么个人。既然你选择了停止,明天我会让财务把我们的账理清的。”
我想,既然说到明天,那就等明天吧,明天一觉醒来,雪凝就会气消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第二天一早醒来,雪凝早不见了。不光早上不见,晚上也不见。我在家中一直守候到凌晨,这时雪凝发来一条短信:“我出去散散心,你不用找我。”
我郁闷坏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
几天后,我把所有的包括洗煤厂、参股的煤矿,还有合伙的工程等等统统倒手变现,揣着上亿资金驾车前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