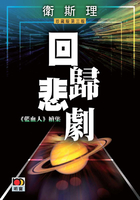我见过生豆芽的,那是一种温暖的记忆。小时候,老家的土炕上,逢年过节时,会生上一缸豆芽,第二天换一半水,天冷得厉害的时候用被子焐着,得到足够的热量温度,让那些肥墩墩的豆子们生出芽来。我描述着,老乡直摇摇头说:“那得很长时间啊,我生豆芽三天就能出缸。”我很是怀疑:“往少里说也得七天吧?”老乡一脸的无辜:“你瞧我像说瞎话的人吗?我也就跟你说说,反正你也不抢我饭碗,市场上那些豆芽是不能吃的。至少我不吃,知道为什么吗?有催产素。知道什么是催产素吗?就是女人生孩的时候,护士好让孩子生下来,给打的那玩意儿。现在拿来生豆芽,一催就大啦。”我瞅着老乡一脸憨厚的模样,心里不由得诧异,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真的呢?种黄瓜的不吃黄瓜,卖豆芽的不吃豆芽,养猪的不吃猪肉,这种赚钱的黑心何时休?我发了一会儿呆,便笑自己鸟人一个,哪管得了这等天下大事?
离开谭四牛已经有段日子了,我被一种没着没落的心情包裹着,一天天地闲来荡去,感到无聊疲倦得要命。整天待在网吧里也没意思,网吧里的颓废和沉闷像一床厚被子,捂得人头晕胸闷,但我不想承认自己真的山穷水尽了。
我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期许,或者说是一种预感,尽管这种感觉来得很茫然,也很浮躁。这天手机在我的预感中响了,我看也没看就接了起来,耳朵里传来一个小心翼翼的女声:“谢哥,是我,曹红梅。”
我很有女人缘的。不管怎么说,小曹也算是个小家碧玉式的美人,有一种乡野的自然之美。垂涎她的人比比皆是,只是没有一个入她眼的,年龄一日日拖得大了,又逢二十五岁的坎,各方面的压力也就来了。曹红梅见到我,内心深处变得清晰而稳固,一想起我她就会怦怦心跳,难道我就是她可望而不可求的爱情归宿吗?连她自己也搞不清,这究竟是爱情还是感恩,抑或两者兼有吧。
我是幸运的,正是小曹的这一次帮助,让我迎来了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转机。
龙城宾馆向来是云鹏会聚之所,富豪权贵常来常往,有许多人都与这里的服务人员关系熟络。今天,小曹接到一位熟客的订餐电话,按说这也没什么,如今做什么不都是凭关系?大事情找大关系,小事情找小关系,没有关系就托关系,没事的时候也想着关系。像龙城宾馆这类的高档休闲餐饮场所自然更难脱俗,楼层经理、大堂经理身上都装有精致的名片,遇上个可心人就散发出去,散发了就有可能遇上回头贵人,至于是因为饭菜好,还是人别致,已经不重要了。熟客给小曹打电话,自然是冲小曹来的。
今天中午订餐的是俞大有,是身价过亿的关城煤老板。曹红梅落落大方不卑不亢,早就入了俞大有的眼。像谭四牛一样,俞大有不好赌好色,手头明养着四个,至于暗地里的,自己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是夜夜笙歌萦耳,日日香风送怀。受俞大有之邀,曹红梅在桌上坐下来,听几句这帮子人的闲话。听着听着,有几句便入了她耳朵,俞大有问旁边一个人:“你手上有没有架电力线路的人?”
那个人随口道:“我回头看看供电局有没有人能干了。”
小曹一听供电局,就想到了我原先在供电局,这些人既然是关城的,我一定也认识。于是就坐不住了,找个借口出去,给我打了电话。
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俞大有一桌人酒还没有完全尽兴的时候,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电话就响了:“谁啊?”
“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了,谢达啊,供电局的谢达,兄弟在哪呢?”
“原来是谢局,我正跟老俞在龙城喝酒呢,你在哪呢?”
“我也在龙城,有时间咱们坐坐,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没问题。”
当时我的电话一停,后来小曹跟我讲,俞大有便问:“谁啊这是,提到我了?”
那个不知不觉当了托儿的人说:“谢达,原先咱县供电局的局长,把官赌掉了的那个,这会儿也在龙城,也不知道在干啥。”
旁边一个人说:“刚说要找供电局的,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吗?”
俞大有自饮一杯:“你说得对呀,给他打个电话。”
五钻深山沟
据说,百分之九十生意是在酒桌上敲定的,这话说得是有些玄乎,但也符合中国国情。我开始考虑俞大有这个人是否值得再次投入热忱,虽然我和他并无交情,但是作为关城的大佬之一,他的诸多“事迹”我还是熟悉的。俞大有原来在矿上开车,胳膊上文着两条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青龙,早年喜欢打架,曾经一个人打得十几个人落荒而逃。后来结交了一帮哥们在社会上混,没多长时间,哥们就鸟兽散,不是在监狱蹲大号,就是给人黑办了,只剩下他成了关城没人敢惹的山大王。但因为哥们的前车之鉴,俞大有尽管成了山大王,但不再像以往胡杀乱砍鲁莽了,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在了挣钱上,觉得只有有钱才是硬道理。
俞大有的发达是在私挖滥采最疯狂最混乱的时候,眼看着大家都在搞生产建设,只要不是白痴就在自家后院里挖煤,挖出煤来就能换成大把的钞票,他当然也不能落后了。于是找个机会,弄了个山头做地盘,雇了许多小兄弟把守着,让人在那里挖风化煤,干净利落地挣下了上亿资产。兜里有钱腰就粗,他便思谋着把地盘扩大,把小窟窿掏成大窟窿,让俞字大旗在山头上飘飘。作为关城的江湖大佬,他已经懒于跟那些挡在面前的人搞温恭谦和、彬彬有礼的虚套套了,但凡此类人等一概大扫帚过街,该下手的下手,该推倒的推倒。不能推不能捏的,就直接用钱砸,大票子砸下去,任你多大的爷都得仆街,都得心甘情愿地听他的调遣。不过,人在江湖上混,还少不得一个“义”字。狠是为了立势,而义则是聚人气的招儿,就是一根筷子和一捆筷子的道理。俞大有狠是狠,但是是个讲义气的人。不然,这么多年,就凭他一个人再狠,再怎么折腾,也不可能折腾到现在这么大的家业和摊子。
机会难得,稍稍迟疑就有可能花落旁家,在小曹暗中牵线下,我当天晚上就和俞大有接上了头。俞大有也是个有事不过夜的人,见有人能给他办事,自然按捺不住想要见见,见到后二话没说,就给了我十万元让去改线。
我马不停蹄回到关城,连夜找到自己熟悉的几个人,第二天就开了工,移十来根电杆对我来说轻车熟路。从进山的第一天起,看地势,察情况,出方案,连工带料,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有条有理,一项一项紧锣密鼓地落实。这得益于过去我当局长时事必躬亲的办事作风和当线工时过硬的业务能力。一番辛勤,五天完工。对我的表现,俞大有非常满意,一见面,就赏给我两万元。俞大有拍着我的肩道:“兄弟,一看你这文质彬彬的样儿,就知道是个有才的人。你的事我也听说了,啥也别说了。你能来我这里,从今往后就是我的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有什么就跟我说,我俞大有就喜欢像你这样的文化人。你来了以后,可得给我出出主意把把关。好好干,你那点儿债算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