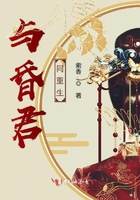《晋书·皇甫谧传》载皇甫谧著论葬送之制《笃终》,“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
遍览《三国志》《晋书》等史,终制薄葬统治整个动乱时代,相较于前朝汉、后朝唐的大肆厚葬,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华文明死亡归宿选制的一贯思维中可谓奇葩,以至于东晋桓温葬姑孰,“平坟不为封域,于墓旁开隧、立碑,故谬其处,令后代不知所在”。
第五节 入山问樵,入水问渔
——其它归宿
小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华文明对土地的情有独钟,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葬于斯,土葬是中华文明无可非议的归宿首选,然而在主流归宿选择的遮蔽下,饱受争议的火葬、惊悚慑人的崖葬、自然古朴的树葬、稍显敷衍的瓮棺葬、极悖伦理的腹葬等诸多葬法,都在中华文明的某个时期、某个地域体现出其无可争辩的合理性。“入山问樵,入水问渔”,各种死亡归宿,或以其因地制宜,或以其顺应民心,都曾被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的生者所接受,生者的接受,便也是接受其往生后子孙为其安排的死亡归宿。
火葬——升天捷径,饱受争议
火葬,中华文明最为古老的死亡归宿,依文献记载与考古实例显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先人即已尝试选择此类归宿,《墨子·节葬下》有“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的举例,《后汉书》有“羌人死皆焚其尸”的记载,然而举例与记载多限于边地区域,在汉民族主流文化体系中,火葬饱受争议。两汉前,焚尸被视为对死者莫大的耻辱;两汉后,佛法传入,火葬亦借助佛教的传道逐渐被中原地区所接受,尤其佛教信徒往往视火葬为首选。形势愈演愈烈,甚至在有宋一代,朝廷曾下诏书严禁火葬,明清两代,朝廷亦以丧伦灭理为由屡次厉禁,民间屡禁不止,火葬始终饱受争议地盛行着。
火葬的盛行或因其较之于土葬的便利性,然而纵观各地火葬过程,某些地域慎重且隆重的火葬仪式甚至比土葬更为繁琐,《马可·波罗游记》有“其焚尸也,必须请星者择吉日。未至其日,停尸于家,有时停至六月之久”“人死葬其尸,设有死者,其室友服大丧,衣麻,携数种乐器行于尸后,在偶像前作丧歌,乃至焚尸之所,取纸质之马匹甲胄金锦等物并尸共焚之”的记载,火葬归宿的选择已非因其便利性,而是暗含某种宗教信仰或生命原则在其中。
火葬归宿的选择与执着,一则受佛教影响,二则有借火焚烧之力助死者升天之意,三则希冀借火焚烧尽早摆脱尸体束缚助死者顺利抵达冥间。尤其是第三种用意,根据考古学、民俗学的研究,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确有助死者尽早摆脱尸体束缚的习俗,原始的处理方式是将尸肉吃掉,这在北京猿人间即颇为流行,然而随着文明化及,“相类残食”因其残酷性与反人类性而让位于其它手段,而火葬的迅速与整洁则成为该理念的最佳替代方式并沿用至今。
崖葬——终伴山水,惊悚慑人
崖葬,亦称悬棺葬,利用天然岩缝、人工木桩将船棺悬置于崖壁之上、岩洞之中,背山面水,悬空而置,鲜有侵扰,流行于古代南方濮越民族。
古代濮越民族对死亡归宿的选择深受其生活习性影响,安土重迁的汉民族选择土地与墓穴为其归宿,纵身江湖的濮越民族则更加青睐青山绿水。《汉书·严助传》称濮越民族为“水行山处之民”,其生前悠游摇曳于山水之间,其死后亦选择山水为其死亡归宿。独特的死亡归宿需要独特的葬具支撑,崖葬葬具船棺,由圆筒木半开刳成,似木舟,如明徐学谟《游仙岩记》记载“他岩,棺尤累累,有规形而锐者稍异。又有壑而舟横者,窦而床列者,虽去人远甚”,更有甚者,若船棺难得,干脆用死者生前所驭木舟取而代之。
不仅仅是生活习性的影响,“舟船”由此岸渡向彼岸的特殊意象内涵,也被视为从生存渡向死亡的象征,濮越民族深谙此道,将船棺视为灵魂归宿的载体,将其亡魂载往最适当的彼岸世界,即祖先处,即故乡。无独有偶,中华文明古代南方民族亦多有“魂舟”习俗,与崖葬类似,均是以“舟船”形式助死者返回本源,为灵魂寻找确切的落脚点,也为死者提供前往灵魂归宿的方式与渠道。
树葬——构木为巢,自然古朴
树葬,亦可析分为“风葬”“天葬”“挂葬”“空葬”“悬空葬”等,置死者于树杈,任其在深山野外历经风化,这脱胎于对原始巢居的追忆与无意识继承的死亡归宿,与火葬相似,古老而朴素。《魏书·失韦传》有“失韦国……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尸则置于林树之上”,契丹、鄂伦春族亦有“置死者于树枝间,任鸟雀食之”的习俗。
树葬葬仪种类繁多,有“悬尸于树”,有“缚尸于树”,有“置尸于台”,有“悬尸于架”,前两种较为原始,后两种则为后世所派生。“悬尸于树”,现今在北方鄂伦春族、南方瑶族仍有遗存,即用冰雪或河水沐浴尸身后置入桦树棺材中,寻茂密红松,悬棺材于半空,既避野兽伤害,又免冻土深埋,是北方森林民族特有的死亡归宿。“缚尸于树”,瑶族特为死婴设置的死亡归宿,即将死婴悬于枝条任野兽吞食,残忍血腥,但在瑶族看来,该归宿既可助死婴亡魂早日托生,亦可助死婴母亲再孕子嗣。无论采取何种葬仪,树葬中尸体的安放最为讲究,方位是重点,时间亦是重点,尸体悬空停留时间愈久愈好,但若尸体坠落,亦无需理会,任由雪霜风化、野兽侵食。
树葬的死亡归宿选择,根源于原始初民对树居的记忆,原始初民“构木为巢”,白天树下觅食,夜晚树上安寝;森林民族“生死同处”,生前躯体栖息于树上,死后魂灵游荡在树间,无论生死,均以树为家,让死者回家,虽无厚棺蔽体,树木却是最为安全、最为恰当的死亡归宿。
瓮棺葬——经济卫生,稍显敷衍
瓮棺葬,即以瓮为棺,将尸体或骨灰殓入瓮具,埋入地下或投入水中,《太平广记》有“袁盎冢,以瓦为棺椁,器物都无,唯有铜镜一枚”,《陔馀丛考》有“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瓮棺多凿小孔,方便灵魂自由出入。
瓮棺葬的死亡归宿选择根源于南方气候特点与中华文明陶制文化的发达,南方潮湿,棺木易腐,而瓮器可长期保存;同时,随着制陶工艺的日臻成熟与完善,陶制品的精美与易得亦为死亡归宿提供最佳葬具。
因大型瓮具制造工艺复杂,瓮棺葬多限于未成年人,半坡遗址氏族居住区中有七十三座儿童墓葬以陶瓮为葬具,若儿童体型稍大,葬具则以两个粗陶瓮对合组成。辽宁长海县上马石出土的瓮棺葬,则均为大型陶瓮盛殓尸骨,且葬式有翁口向上与翁口向下两种,与半坡遗址的受众与形态均有所不同。
此外,因民族习俗殊异,瓮棺葬多用于二次葬和非正常死亡者。瑶族有二次葬的习俗,死者多停棺野外,数年后,或拾遗骨或殓骨灰,置入瓮具,再行土葬;水族对非正常死亡者,如麻风病死者、难产死者等,为免其阴魂传染后世,采取瓮棺葬封闭其遗骨或骨灰,麻风病死者埋葬在低洼处或常年不干涸的泥潭处,难产死者则被埋葬在远离村寨的偏僻处。相较于其它死亡归宿,瓮棺葬的选择缺少一丝宗教的因缘,一抹生者对死者的温情,更多的是封闭远埋,是方便敷衍。
腹葬——人体圣餐,极悖伦理
腹葬,顾名思义,以生者腹部为死者尸体的永恒栖居,“相类残食”的独特死亡归宿多见于后人对原始社会的猜想与揣测中,《墨子·节葬下》有“楚之南有啖人国者,其亲戚死,刳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尸子》有“武王亲咋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
“犹猛兽”般悖伦理的死亡归宿,可追溯至人类产生之初为维持基本生存的本能之举,在物质匮乏的生存境遇下,为抢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不可避免,而战败者死尸的可食之肉亦是生存资源,极端的历史情境下,腹葬的死亡归宿选择顺理成章。
随着时代发展,腹葬这种诡异的死亡归宿被注入巫术等文化现象,在文明发展初期,先民认为吞食死者尸肉,不仅可获得死者生前的体质特性,也可获得其智力特性,发展至此,腹葬已超越其原有的饱食充饥初衷,演变为充溢精神寄托及自我满足的巫术行为。
时代向前,文明覆盖范围日益广阔,在人伦敦厚的礼教统摄下腹葬日益式微,荡然无存,然而,各地仍以其特有的方式以某种程度保留该死亡归宿,布依族死亡狂欢的“砍牛”习俗即是腹葬的变体,《黔记》有“卡尤狆家……凡祭事,贫者用牛一,富者数牛,亲戚族友各携鸡酒致祭,绕牛而哭,祭毕屠牛分肉毕而散”,生者不再直接食用死者进行腹葬,而是用牺牲代替死者,也希望牺牲在冥界继续为死者服务,替死者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