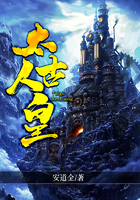那边,三两丈远的一株大垂柳上正静静地站了一只毛羽黑亮的乌鸦,在那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它跟了我们有好一阵了。半个多时辰前,我们在那溪水边洗漱时,我就有瞧见它,当时也没太在意。过了会,在村口的那条小巷前,我又瞧见了它。”姜之月轻轻道:“之后又见它几次或自檐角或从屋顶飞过,每次见到,都只离我们三五丈远的样子,瞧神情是在窥探我们的行踪呢。”
瞧见我们在打量,那乌鸦忽地警觉起来,歪着头看了我们几眼,呀的一声飞走了。
我们本来都觉得姜之月可能是多想了,你想啊,一只乌鸦这样的鸟儿怎么跑来窥探我们呢——我这话并不是说乌鸦这种鸟儿不能盯梢人,事实上,它们这一类鸟聪明得很,又爱动脑子,说到盯梢窥探,一般的禽类还真比不上它呢。
我只是有点不敢相信,哪个人那么无聊,竟然让一只乌鸦前来盯梢。
毕竟,我们又不是声名卓著,做下天大事迹的人物,窥探来去,也窥探不出什么有用情报吧。
不过,乌鸦跟着窥探我们兴许没什么作用,但我们跟着反窥探它又不一样。
隔了一会儿,那只乌鸦忽又悄然飞回,再次瞧见我们这一行人时,它似乎有些愣住了。
如果我是它,我也会愣住呢。
因为之前的队伍里少了两个人,一个是慕容嫣儿,一个是猴哥。
他们到哪去了?
乌鸦不知道,我们却知道。
慕容嫣儿已隐身跳上屋顶。
猴哥已自一处杂草丛生的灌木丛里土遁,按照既定的计划潜身到一处高三五丈的浓荫柳林上。
我们的反窥探策略也很明确:
慕容嫣儿负责近处跟踪;
猴哥负责确认乌鸦最后起落的所在;
我和姜之月则负责在四处“找”同伴。
不得不说,那只乌鸦很聪明,它竟似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反跟踪了——虽然它并没有真的瞧出慕容嫣儿、猴哥藏身何处。
饶是如此,它仍是有意无意地带着慕容嫣儿在那村里的长巷短弄里兜圈子绕弯路。
两柱香时不到,村子已被那只乌鸦飞了个遍,它的身影时常一闪一消,速度之快,变动之疾,我和姜之月瞧见了,都有些替慕容嫣儿和猴哥着起急来——这跟踪盯梢只怕不怕容易呢。
尽管如此,借由慕容嫣儿的四处跟随探看、猴哥的高处定点盯梢,一刻钟后我们仍是成功追踪到了一处浓荫树林。
这树林离那村子并不远,只七八百步的光景。林子里除了成片的葱郁大树,还种了好些花花草草和高高低低的果树——这树林确实给乌鸦的藏踪敛迹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它几次在林里乱飞一气,要带我们绕弯子。只是为时已晚,我们已经跟了过来,并确定了大概的位置,乌鸦它虽然可以飞走,但林子的尽头那个大院子却飞不走呢。
这会儿,那只乌鸦在一根斜长的树枝上落下,紧张地打量着我们,忽地呀的一声,重新往村子飞去,显是要把我们引走。
我和姜之月相视一笑,也不理它,只步行匆匆,一同穿过那林子,往那小院子走去。
门外站着一个人,却是已作寻常僧人打扮的烈炎和尚,那脖颈上还挂了一大串念珠,以前也没怎么见过,也不知他是从哪里得到的。烈炎和尚脸上正带有三五分的焦急神情,在那来回地踱着步,转首瞥见我们来了,大步走前,抚掌大笑道:“好小子,果然有些意思。”上前瞅瞅大白,疑惑道:“这只大白狗怎么了?之前见它还是精精神神,身上很有些用不完的活泼劲呢。”
我便把赵思谦他们被困陷坑,并遭遇怪尸的事情给烈炎和尚略略说了一下。
“尸毒?”烈炎和尚微微皱起眉头,“这只大白狗并不是一般的狗,传闻赵檀越当年为了饲养好它,可没少下本钱,加上它又胆大心细、奔走机敏,寻常的行尸也伤不着它,那喷毒的怪尸只怕有些棘手。”一边说着,一边疑惑地往四周瞧了瞧:“怪了怪了,小乙,只你和紫紫姑娘两个人过来么?”
我嘻嘻一笑,道:“不是。”
话音刚落,慕容嫣儿忽地在一旁急急显出身影来,目中含笑和我们打招呼,随即向烈炎和尚一抱拳,大大方方道:“大和尚,你好。”
隔了会,猴哥也哼哼嗤嗤的自一个土丘里钻了出来。
烈炎和尚瞧了一眼,哈哈大笑道:“原来是这样,怪不得那乌乌飞来飞去,和那怪医呱呱说个不停,原来,你们后边竟是分工合作,有人跟踪,有人定点,还有人放些烟啊雾啊,哈哈,这计策确实不错。”回首向慕容嫣儿一点头:“刚刚看了你的隐身法,很像南朝慕容世家的手法,再看眉眼,也和那千里驹慕容麟有些相似。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慕容家的嫣儿姑娘吧?我听宁平师弟提起过你。”
慕容嫣儿向我们吐吐舌头,道:“这大和尚看人的眼光好尖。”
好尖?
像刀子那样吗?
我们忘记了南朝那边喜欢这样子来形容一个人的洞察力,一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慕容嫣儿很快也意识到了,她性情活泼,自是不拘这些的善意讪笑,也格格的跟着笑了起来。
笑归笑,我仍是没忘嘟囔上一句:“大和尚,这个小院离你说的那个马家庄可有一小段距离——”
烈炎和尚仿佛一早便知道我要问什么,遂摆摆手道:“咳咳。不是我不想说,是这个怪医专有些怪癖,要找他的人,旧识之外,初来乍到的一例要靠他们自己找过来哩,他还说这是第一重考验。”
慕容嫣儿奇道:“大和尚的意思是,我们还有别的考验?”慕容嫣儿虽是初次见到烈炎和尚,但之前却听我谈过几次,所以她对烈炎和尚他们的称呼也是一律依随于我,这一点上,姜之月和她很像,她们到底都是和我相熟相契之人——虽然我并不是很早就意识到了这样一些小细节。
姜之月也道:“那我们算是通过了第一重考验吗?大白它的状态可不太好,能和那怪医牛伯伯说一声吗,先帮大白——”
话音未落,早有一个喑哑的笑音传了出来:“老牛我闯荡江湖三五十年,被人恭维为牛哥、牛兄、牛神医之事有之,被人讥讽为臭牛、死牛、疙瘩牛亦有之,唯独没有人如此亲亲切切地叫我一声牛伯伯的。”伴随着那话音一起出来的是个赤髯红面的细瘦老头儿,肩上站了一只毛羽乌黑、神采动人的乌鸦,顾盼生辉,正是此前一直跟踪着我们的那一只怪鸟儿。
那乌鸦瞧见了我们忽地“呀呀”叫嚷起来。
细瘦老头儿嘿嘿笑着,先是和我们打了个招呼:“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这些后辈子弟倒也机灵得很,这么快就找着老朽的寒舍。”随即轻轻拍着那乌鸦的脚趾:“乌乌它说,你们都很聪明,尤其是这个紫衣小姑娘,反应很快。”
我忍不住问道:“乌乌,是这只乌鸦的名字吗?”
细瘦老头儿轻轻点了下头:“嗯,你们不也给这只石猿起了个名字吗?猴什么来着……”他忽地止住话头,认真地回想着,那乌乌却机灵灵地叫了一声,瞅着细瘦老头儿已注意到了自己的鸣叫,又急急叫了两声。
“对,猴哥,乌乌说它叫猴哥。”细瘦老头儿恍然道,一边说着,一边还伸手恋爱地摸了摸那乌鸦的毛羽。
我和姜之月异口同声道:“您能听懂它的叫声?”
慕容嫣儿却把眼往烈炎和尚瞧去,吃吃笑道:“大和尚,张小乙说你来这里也有好几天了,该不是你在之前谈聊中和这个老伯伯提过吧?”
烈炎和尚摇头笑了起来:“嫣儿姑娘,你确实很聪明。我这人有时嘴皮子不牢靠,不过这一次和尚可真真没有说,牛神医除了医术过人,还精通兽语,擅长和飞禽走兽打成一片。”
细瘦老头儿哼道:“小烈炎,你就别给老叔戴高帽了,老叔要是特别容易和飞禽走兽打成一片,胳膊上这几道刺眼的辛辣爪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听了都疑惑地向烈炎和尚望去,烈炎和尚打个哈哈,喃喃道:“小侄也是不知道那白狮子怎么病好了就变了一个模样,连牛叔你的意见也不太听。”
哦哦,听他们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过来,原来那细瘦老头儿的几处爪痕是被白狮子抓的——竟然把牛怪医的胳膊给抓伤了,这火性可是大得离谱,我们此行又还要求他帮着治好大白的尸毒——伤他在前,求他又在后,只怕要费些周折了。
细瘦老头儿嘿嘿笑了一阵,忽地道:“老人家忘性大,愣是站在这里说了小半天,也没有招呼你们进去坐坐,真是失礼了。”向我们招招手,自己领头走了进去。
猴哥紧张兮兮地跟着我,一边瞅着我抱着的大白,一边又不住拿眼去瞟那院内情形。
姜之月和慕容嫣儿都先后走前安慰猴哥,说大白会没事呢,这院子里可是住着一个精通兽语兽疾的兽医呢。
烈炎和尚却叹了口气道:“这石猿机灵着呢,它不是怕大白有事情,而是闻出了一些危险的味道。”
“猴哥,它是有些担心里边那头白狮子。”我接过话头,对猴哥笑笑道:“放心吧,你们都是我的小伙伴,我不会让它欺负你的。”
说话间,大家已经进得院子来。
公允地说,这座大院在外表上和寻常所见的大户人家的庄院也没太大的差别,在某些地方上,它兴许还比那些庄院简陋了些,比如说,它的围墙是堵不起眼的灰墙,又如,它的大门古朴,绝少装饰,更没有什么威风凛凛的石狮子。
它与其不同的地方是入门后十多二十步便有一片三亩来大的草坪,那草的模样和外边的草并无二致,只是要更加浓绿动人。整个草坪形似一个八角形,八道边上的草或长或短,错落不一,竟隐约显出一种八卦阵的气象,让人瞧了不由暗暗称奇。
细瘦老头儿行到草坪的尽处,忽地停下脚步,将袖袍往前轻轻拂了两下,嘴里兀自念念有声,顷刻间光影晃动如流波,眼前十多丈远的地方却多了一排高矮有序的屋子——脚下依旧有一片大草坪,踩着踏着,软软柔柔,只是草坪上多了三两个身着红肚兜、兀自拖着一条半条鼻涕虫的娇憨毛孩儿,在那嘻嘻笑笑的追逐打闹。
此外目之所及,处处可见活蹦乱跳的飞禽走兽,如毛白如雪的兔子、憨憨如石的黑牛、飞来啄去的小雀儿、咕咕叫个不停的信鸽儿,那百十只动物中甚至有一只北朝少见的赤色大龟,龟甲斑驳,甲上更似印有奇形文字,歪歪扭扭,也不知写的是什么。这些飞禽走兽们大多聚成一团,见人来了,也不怎么吃惊,略略让开一条道,仍是自顾自三五成群的玩着,只那白狮子百无聊赖地在草坪东北角躺着,慵慵懒懒的神态之中仍自有一种不怒自威的王者气度,连在那附近草丛中啄食草籽的小雀儿也知趣地安静了好些,只压着嗓子在那和友伴轻轻逗闹。
那几个小孩儿见细瘦老头儿来了,个个都一脸喜色地围了过来,口口声声,“爷爷”“老头”的叫个不停。
其中两个身穿红肚兜的小孩儿,肤色白净,模样儿相仿,都很俊俏,那手儿脚儿都是肉肉的,光溜溜的青头上还顶了一根小枝,枝末长了一大一小两片掌状叶子。剩下一个则黑头黑脸,头上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半片叶儿半根树枝,脸上更带有一种煞气,它的模样儿虽不如那两个小孩儿俊俏,但一对大眼间的光亮灼灼,倒也很有神采。
这几个小孩儿并不是人族子弟,只会说一点儿人语,所以当它们在嘟嘟囔囔吵吵闹闹地说些什么时,语速又快,我是半个字也听不懂。
细瘦老头儿却半眯着眼,入神地听着,脸上露出一种欣慰的笑意。
这怪医果然怪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