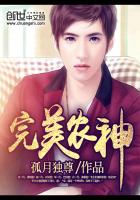我仔细看过,那些残页上的口子都是旧口,当初我翻看这本书时,整本书上积了一层灰尘,显是很久都没有人翻看过。不管那撕书之人是谁,他前来这密室撕书的日子都不会太迟。
这会儿,褚远已经重新把密室里的重要藏书检视了一遍,没有任何丢失书——褚远本来就极注重藏书的存放情况,外边的书卷自然由仆人可以代劳,但这密室之中却是他自己亲力亲为,是每个月都会检视一番的,那一千多卷的书,层层叠叠,自然不算少,但他却似早已将所有书目烂熟于胸,加上独特的点算方法,不过一个时辰即已把那一千来卷的书都核对了一遍。
“会不会是有什么人趁你不注意偷偷闯进来?”
“可能倒是可能,但成功的几率不大。藏书楼所在庄子的八名四处巡警的壮汉之身手均属不错,外加一个哨塔,守塔之人又是耳灵目聪的有名镖师,加上仆人家丁等,少说也有十五双活动的眼睛。加上这庄园也不大,要完全避开他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况且,我还有阿城那难得的一种痴心和一对冷眼呢。”
仆人家丁中,只有一个名唤阿城的长厚老仆才知道归远楼里有一个密室,并可自由出入。
此人年轻时是个落第书生,才华满腹,爱书如命,弱不禁风的他为了抄录一本好书可以毫不犹豫地顶着个大风雪在雪地里走上个一天两夜。捱到回来的半路上,他的眼眉早已结冰,手脚先后僵冷麻木,后来晕倒在雪地上,气息奄奄,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樵夫把他扶回家中,只怕凶多吉少。
正是这种好书不好命的劲头打动了同样嗜书如命的褚远,此后两人渐渐相熟,二十多年前,那书生自落第后心情惨淡,后到褚家自求为仆,他只提了一个怪条件,即农闲、雨天和晚间时节可以自由前往书楼看书。褚远爱惜他的苦读好书的心思,从不将他看成仆人,每每以知交之谊相待。
阿城骨子里仍是个笃诚的书生,最近几年腿脚不便,渐渐少上得楼来,但床头桌案,书却散放成堆,苦读乐读心思不稍减。据说他早些年曾遇一异人授法,开发了瞳术,能察秋毫于极细,是故他的瞳力远盛常人数倍,因感激褚远多年来赏识和呵护之意,常常自发巡视山庄周近及归远楼上下,以绝书患,有这样一颗爱书护书的痴心和察细于微的一对冷眼,即便盗书之人有些高明手术,却也绝难无知无觉地进得山庄来——因了他的痴心和冷眼,归远楼顺利擒下一十三个盗书人,个中不乏大盗巧寇,连当年名动一时的南朝大盗梁上人也是栽在阿城的那对冷眼之下。
褚远停了半会,续道:“除了阿城。当年大和尚还把我打造了一些特殊的防盗风铃。除非对方能在一进来就把那分散在密室里的一十八个风铃都在片刻的工夫里捂住,不让它们发出半点声音,若是慢上半拍,他的隐秘行踪只怕要被一大阵的震耳铃声搅个大乱。”
这房间藏有风铃,我倒是知道的,获准进入密室看书的几天时间里,在翻动四处的书卷时,我无意发现了其中的十三个——我以为都找齐了,不曾期想还有另外的五个静静地隐藏着,等待一丝惊动。
这些风铃都制作得极为精巧,遇到稍大的一点流动的气息就会发出一阵叮叮铃铃的响声,别处的风铃无论多或少,响起来都特别动听,这里的风铃却是特殊之极,超过三个同时响动——所合成的声音就会变得极为紊乱、刺耳,很容易引起这寂静书楼里外的人的注意;超过五个,便会触动隐藏的机关,某一道隐蔽的缝隙里便会迅速喷出无色无味的气体,可以在顷刻间将人熏晕——不消说,这气体和那奇巧风铃一样,都是宁平和尚的怪才之下的一应手笔了。
之所以知道得比较的详尽,并不是宁平和尚和我提过,只是因了初入密室的一天半时间里,我翻动书页动静稍大又或是走动时的脚步声太大,触动过其中的几种机关。
亏虽然没有完全吃,但我却长了一智,此后每每以极轻极柔的动作从书架上取出几卷想看的书,拿到密室外边的书桌看,一俟看完了再自行放回密室。
褚远也极爱看书,常常在密室里一坐就是半天。
阿城有时也上得楼来,他见人也不怎么说话,只是淡淡一笑,轻轻一点头,便径自去拿书架上抽下一本自己想看的什么书来,他的一对眼眸眨也不眨地看着书里的那一行行或娟秀或挺拔或飘逸或丰美的字,时而愁眉,时而短叹,时而会心一笑,他静静地感受着文字里边的那一个小小世界和那些凝滞的时间。
我们一老一中一小,常常在这书楼里各据了一角,光影消长,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彼此书页的翻动声。
十月初十。
无风,极闷。
黄昏过半。
四周的暮色渐起渐浓。
褚远因为接连几天只顾勤读,有些困乏,下楼休息去了,阿城午后上来一会,从书架上抽了一册书静静地下了楼。
偌大的藏书室里,我独自一人在静静地看着书。
双眼因为久视而有些暗暗作痛,我站在窗前出神地望了一会外边的萧瑟暮色。
然后,我燃起一对蜡烛,一盏搁在了书桌上,我自己却端起另一盏往一旁的书架走去,古绿的铜烛台在烛焰下闪出一点动人的光亮。
密室已经关上了,褚远又下得楼去,那开那密室的详细手法我虽一一看在眼里,但主人家不在,自己贸然去开,于情理上颇有些不便。我就近停在一旁的书架上,往那些排放得密密实实的书一阵审视,想再从上面抽下一册什么喜欢的书看看。
“啊,又找到了一册喜欢看的书。”我心头一热。
那一层书塞得满满的,我手上略略用劲抽了小半会,才把那册想看的书给抽了出来。
转身往书桌走去,只走了两三步,背后咚咚几声响,回头一看却是掉下十几册书来。
我俯身把那些书轻轻捡起,摇动的烛影之下,有好一些灰尘在四处飘动——忽地,我瞥见其中一处显出一段透明的人形的痕迹,正惊疑间,那灰尘突又一乱,仿佛受到什么气流的影响——桌案上的蜡烛烛焰兀地偏了一偏,我怀疑是自己眼花看错了,但那烛焰又是一动——几乎是同一时间里,我身边静静持拿的这盏蜡烛也是一动,奇诡地跳跃了好几下。
巧合不能同一时间出现两次——有人施展了隐身术!
来人不仅胆子极大,身手还相当敏捷,竟神不知鬼不觉地瞒过了一众守卫,然后又轻轻巧巧地来到了藏书楼里,如果不是那些意外掉落的书卷激起的灰尘,我也要被他十足十地戏弄一番,谁又能想到有人会用隐身类的法术前来偷书,而且还能把法术效果维持得那么好那么出众。
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把书一一放到那架子上,转身时却偷偷把怀里揣着的水晶匣子掀开一角,掐断了其中一节月灵草——化解师父身上的蟒毒只用掉了一大株月灵草,然后他取走了三无株存放在道观。其余的,师父却没怎么理会,只让我妥善保管。
悄悄往指上染点些汁水,然后我以袖遮面,一脸困倦的打着哈欠却把手往脸上一抹——不知情的人见了,怕要以为我是在揉脸醒神呢,其实我正是借机把月灵草的汁水弹入眼眶里。
双目闪过一片清凉,片刻工夫之后,月灵草即已经完全生效。
眼前的事事物物维持着原有的色彩和大小,但光影却变得灰白、暗淡了些——受暮色和烛光的限制,原本只能看清六七尺范围内的东西,但现在我却惊讶地发现——只要我凝神去看,再细小的事物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现在我就清晰地看瞥见一朵远十丈远近的篱笆旁长出的酒盏大小的黄花——这月灵草提升了我的基础瞳力只怕不下十倍!
我在书架间随意地踱着小步,左手拿着的那一盏蜡烛有烛光轻轻跳动着,诸事如常——除了一个透明的人形影像站在倒数第五行的书架右侧,他轻轻地移动着步子,伸出一根手指往那些书脊上极轻地划过,似乎正在找寻什么似的。
我故意放缓脚步,不时在书架前停下,东翻西看,眼角的余光却始终不离那神秘的盗书人。
那个透明的人形影像在书架间转了几圈,在地上愤愤地跺了几下脚,他的心里大概十分气恼,脚下用了点力以至于地板上发出一点声响来——我故意把灯光往那边一照,他果然站定,似有些紧张地望向我,我奇道:“怪了怪了,什么都没有,难道是我听错了?”
那个人形影像闻言,仿佛很得意似的的,伸手比划了几下,却是在冲我做鬼脸。我暗暗觉得好笑,这盗书人怎么竟像个女孩子似的,生气烦恼时就不由自主地跺脚,得意时还做鬼脸相戏弄——这保密功夫做得也太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