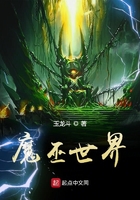“嗯,好狂的小子,我的手就在这里,有本事你便来拿!”范希真拍拍自己的左手,嘴角露出一丝轻蔑、讥诮的笑。
我反手将剑擎出,一个箭步蹿前,挥剑便砍,刷刷刷!
范希真只把身子先往左边一侧复又向后一旋,轻松松地躲过头三剑。
我手上的剑力不减,但往前猛刺,同时把左掌屈指成爪,凝出点点焰火滚动于五指指尖,只管朝他胸前狠狠抓去。
“哦,中阶火技的‘火龙爪’吗?”范希真脸色微变,闪过我的爪剑合击,随之一个纵身高高跳起。
我瞧个真切,一把抓过腰间的小葫芦,把里面所剩的梨花白尽数倒进嘴里,手上一晃,却把一个空葫芦朝自己预判的范希真落脚处猛掷过去,人亦如只利箭跟着飞了出去。
范希真是心思极慎密的人,早把我的举动一一看在眼中,只在空中使出几个飞旋,往另一侧急速落下。
这一变动,离我原来预判的落脚处便差上两丈来远。
我觑他的身形将落未落之际,使出“隐步”,连闪了两次,欺身赶到了他的跟前,手中剑一擎,朝他左肩疾疾砍下。
范希真神定气闲地把双手向外一张,支起了“寒冰盾”,砰然挡下我的辣手一击。那盾与其说是一个盾,倒不如说更像一个罩,里边的寒冰真气流动如罩,可以随时将空出的寒冰调动,强化到任意一处罩壁的防御,眼下它就把范希真整个人牢牢罩住,固若金汤,
我将手腕急转,剑势一变,顿成横削击出,但往那寒冰盾的当头一处攻去,一连数剑,总是集中在前一剑的击打处。范希真目中闪过一丝赞赏的神情,随即精光暴盛,竟把被攻击处之外的罩体尽数催动成百十道尖细冰棱齐齐刺出。
“啊!”
我错步急退出八尺,不料那冰棱却诡异之极,先头刺空的冰棱虽掉落在地,但别的冰棱却以邻近的冰棱为桥为梁,随附其上,如一根根长枪激刺过来。
嗤嗤。
我身形急转,一边把手上的火焰尽数弹出,一边将口中那“梨花白”酒急急喷出,一道炽热的火舌熊然立起,登时把先后袭来的冰棱一一挡下,灼烧成水汽。
范希真脸色微变,鼻子里“哼”出一声:“应变还可以。”
我没有理会他的话语是冷嘲还是热讽,趁着火势未尽,又把口中的残酒一股脑喷出,火舌膨胀,如一条大火蛇呼啸着撞向范希真。他的“寒冰盾”已耗损大半,虽是有及时补充着相应的寒冰罩壁,但眼下又需调动许多寒冰来抵消火舌的冲击,可供别处防守的寒冰所剩无几。
心念一转,我整个人快闪到了范希真的背后,我本来可以引剑给他狠狠一击。
但,气归气。
说到底,我对他的愤怒和失望并没有强烈到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地步。我将剑半收,却把剑柄冷冷地撞向他的腰部。
岂料,范希真的背后竟似长了眼睛一般,竟在剑柄及腰前诡异地躲开了。
“你为什么不出手,刚刚那么好的机会!”范希真冷冷瞧着我。
“还要我跟你说几次,立场一明,临阵对敌,就不能再心存仁慈!”见到我没有反应,范希真改为怒目相向了。
“……”我一脸愕然,范希真真的不可理喻,别人不想伤害他,他反倒以为是浪费了难得的机会,违背了他往日的教诲,那他怎么不想想,他今日的所作所为,辜负了多少师门重望、同道期许。
“我不需要你的手下留情,别忘了,是谁砍掉那个人的左臂!”范希真冷冷地道。
“你曾是我的长辈,我……”
“你什么你,你以为我会对你感恩戴德吗,你以为你的哪个对手会为你的心软感动吗?”
“……”我实在想不通范希真为什么动这么大的火,心里又是疑惑又是失望。
“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吗?没错,就是因为我讨厌你们这群不分青红皂白的老好人!凭什么以为自己什么都扛得下!”
此时,我的斗志虽然松懈了些,但怒气却增多了,于是也气愤地回顶了一句:“很好,我也讨厌你这样自以为是的人!”
“嘿嘿,那就好。很快,你就会发现憎恨讨厌我这一类的人,可以让你活得久一点。”话音未了,范希真的身形骤现,阴沉沉道:“呆小子,你不杀我,对么?很好,那么换我来杀你!”侧腰拧身,一记重脚狠狠地踹在我的小腹上,我顿时连人带剑摔出了两丈多远。
唔,眼里直冒金星,腹内是一阵剧痛,我强撑着把巨阙往地上猛地一插,正要趔趄站起——一截散着幽蓝冰气的冷冷剑尖早已指在我的喉咙上。
那剑捏拿得很稳很准,并没有半点颤抖,显然是动了信心十足的杀意。
我抬头望了望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范希真。
他的脸上带着一股浓浓的杀气和怒意。
下一刹那,便要施下毒手。
正在这时,自山顶附近的天际极速划过一道弧线的火线,线头是一个熊熊的火球,轰的一声,落在这方圆不过五六丈的平地之上,震得大地都颤了几颤。
浓浓的火焰里缓缓走出一个人,一个横眉怒目的烈炎和尚,他拍拍身上几处过分活跃的火,整个人散出一种难以直视的威严刚猛气象。他的身上跳动着许多或大或小的火焰,却不向四周逸散,反倒殷勤地簇拥着,仿佛大和尚是他们的王一般!
“姓范的,你的剑敢再向前伸出半寸试试!”烈炎和尚沉声道,目中火光一闪,随即大步走来,身后兀自跟了一道长长的流动火焰,猎猎腾腾的火光把他的八尺高大的身体衬托得越发威猛了,宛如一个掌控着天火的不世神将。
“炎系的秘术?嘿嘿,大开眼界!”范希真冷冷地笑着,随即把剑收起。
“跟这个和尚多学学,再去维护你那什么狗屁正义和不知所谓的心软吧。”范希真望了我一眼,意味深长,人即高高飞起,眨眼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中。
我和烈焰和尚默默地凝望了一会天际。
“怎么样了,臭小子?”烈炎和尚关切地问,说着把双掌轻轻一旋一扭,似在施用什么手印,很快地,他身上的耀眼火焰也开始消散。
“我挨了一记重踢,胸口很痛,还有……”我拾起落在一边的剑鞘,轻轻着把巨阙插入鞘内。
“还有什么?”烈炎和尚急切地问。
“还有,我胸前的地玄镜好像裂……”话没说完,我眼前涌来一大片的黑,人随即晕了过去。
师父在受创后的第四天就可以较自如地下床活动了,脸上的气色也很渐渐红润起来。但他整个人看起来却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对于失去的左臂,他只用了一种淡淡的自我解嘲:“都一把老骨头了,还要重新学习一种平衡,真让人头大。”
话虽如此,第七天开始,师父就又有声有色地练起功来。我和烈炎和尚都劝他,多休息几天再练习好点,他“哼哼”着表示不满:“我才刚满花甲而已,又不是七老八十了,哪有整天怕着赖着当躺尸的道理。”
考虑到师父本身的调理护养知识远远要丰富于我们,见他如此有信心,我和烈炎和尚只得依了他,但也提了个折中的条件——在创口没有痊愈之前,只能进行一些轻缓的拳脚习练,断断不能选用动作剧烈或需要耗用真气灵力的。师父含着笑点头表态,说是就这么定了。
我们的话,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稳妥——依靠着观里的金疮药、还元丹等灵药和他以往修炼所得的强健体质,他的创口处已基本收口了。
这一天,见我和烈炎和尚仍在一旁小心地看着,他不满地皱了皱眉:
“好了好了,你们忙各自的事情去。我这个老头子既有狮子似的雄心,又有狐狸般的谨慎,不会自折了老本的。”
我和烈炎和尚只好各自离开,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三五天后的黄昏,我正在灶房里引火烹茶,师父像个小孩子似的手舞足蹈着走过来:“哈哈哈。”
“师父,什么事情那么高兴?”我带了几分疑惑和惊讶。
“呶,就是这个了。”一条蓝影从眼前迅疾闪过,我的手中一沉,定睛一看,竟是多了两块木柴,再往前一看,那条蓝影已经柔柔地回落到师父的身上——却是他左手处那空荡荡的长袖。这速度真不简单,虽然我能基本跟上这一动作,但里边的伸缩收展轻重缓急,繁繁复复,讲究得很,我这时却不能一一看得过来。
“怎么样?”师父一脸笑意地望向我。
“真厉害!”我挤眉弄眼的,直挺起大拇指。
“臭小子,少拍为师的马屁,在这‘袖子功’上,为师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老头儿呢,离登堂入室还远着呢。”师父把脸上的笑容一敛,双眉微动,正色道。
“您老人人家说的甚是。”看到师父恢复得如此有精神劲儿,我的心情也是轻松了不少,笑笑着把手中那两块木柴塞入炉里。
“对了,一会给我泡一壶茶,浓一点,不要太淡了。”这一会儿,师父的人已出了灶房,不过他的声音却远远地传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