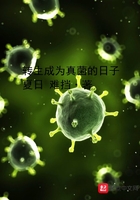拖车憨说:我一个破拖车的,值得用这么大礼?我能给办什么事?要是想拖东西,她用钱顾我不就得了,还用绕这么大弯?
妻说:这事是有点儿怪,既不托你办事,她是你的人客,就请一个拖车的,这不更大礼。是你向人要的?
拖车憨说:我要,那也得要得来呀?我就向她要一碗卤面,五角钱,她没粮票外加两角钱。
妻说:这一桌得多少块?比包你几天车的钱还多呢。
拖车憨说:想不明白就别想,省得脑仁子疼。傻人傻福气,就落个口福吧。可他不想也得想,半天说,不知道番仔婆这是怎么啦?
儿子冷冷地说:也没准是请错了。
拖车憨不爱听:怎么就请错了。请错又怎么样?
儿子说:请错了你就得白给人拉几天车。
凭什么?拖车憨有点儿要犯狗了:错就白错,吃就白吃。那你吃,你去拉她。
儿子是个慢性子:她又不是请的我。
拖车憨一下给咽住了。
妻说:这有什么好吵的?有吃的了就闭嘴。没吃的叫有吃的了还叫。现在是他养你还不是你养他。
儿子不吭声了。
女儿说话倒甜:要我说没准这是有缘,要不一个番仔婆跑咱家门口来干什么?你不是说她还一再地给咱们的房子拍照。番子婆没见过咱这样的房子,她觉得新奇。
儿子不服,又蹦出一句:你还把咱们这破房子说出花来。
女儿说:自己还不自己说句好的,就听人家踩好呀?
拖车憨缓了过来:这样的人客我不嫌,苦找不来呢。剩菜我也不嫌,吃还吃不上呢,我还臭讲究什么?我只要有吃,有喝,有人客,有钱挣,我怎么都可以。咱穷可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咱也不是下三烂,一开始我也怕把剩菜带回来丢人,是老板说得带回来,这是人客好意,我想想也对。
儿子、女儿都没再说什么。
妻说了一句乡下人的大实话,早点拿回来赶上吃日罩顿。
拖车憨说肚子都太素,又不是装不下想吃就接着吃呀,要不搁到下顿也不新鲜了。孩子都馋。
两个孩子不由地都站到桌边。
拖车憨看看他们说:想吃就吃,这也没有谁看着。
儿子抓了半只豆。
女儿抓了一只九节虾。
拖车憨说:干么站着,都坐着吃。他看一眼妻,平日也吃不上,你也过来吃点。
妻就过来吃了一块炖肉,吃得嘴唇油光光的。
儿子也吃一块炖肉,嘴上也油光光的。
女儿也望着那碗炖肉,她用手指尖挑了一块瘦点儿的,小嘴也油了。
所有这些构成拖车憨今日生命的光彩。
妻站起来端走那盘豆豉鳗鱼,说是去热一热。
拖车憨说:热鱼凉肉,也好。
儿子、女儿只是埋头吃。
拖车憨这时得意地卷了一炮烟,在烟雾中看着自己贪馋的儿女。他想好好地让他们吃吃,发现妻半天还不把豆豉鳗鱼端出来。他有点儿坐不了,吼了一嗓:老在户,你怎么哪样都比别人慢?
妻这回挺拍他的马屁:来了来了。她把豆豉鳗鱼端出来往桌子上一搁,上边冒着白气。
拖车憨定睛一看,变了。拖车憨的脸也跟着变了。
妻却笑笑说:我给加一碗豆豉,就番薯吃,能多配几顿。
拖车憨火没有发出来,他自己窝回去了。看到妻那发自内心的笑,他心里感到酸酸的。
这都怪自己没本事,年轻时妻让人拐跑了,混到这节,孩子连一口好的都吃不上。一回,儿子摸黑吃番薯配豆豉,问他豆豉里怎么有一条小鱼干?他都不敢回答他,哪准是墙上的壁虎掉到熬豆豉的锅里了。妻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会做酱瓜豆豉,红红的,脆脆的,按乡里人的习惯端着两只碗出去吃饭,就这小花碗里的豆豉红得惹人的眼,酱瓜脆得惹人的耳朵。拖车憨小时候,他母亲淹的一缸子豆豉他们家吃了两年还没有吃完。为什么?家里穷,怕这一缸子豆豉撑不到一年,就下死命地搁盐,咸得能啄人的舌头,常常用箸(筷子)头碰它都有点儿怕。豆豉哪怕有点葱花油花,可那年月缺的恰恰就是油水。有点肉或是小鱼小虾的,也就好吃。那时的人有点儿傻,当然没钱买肉,但那时水里有的是小鱼小虾,割稻子时水里经常有毛蟹在爬来爬去,平日里怎么就没人想起来去抓呢?在溪窟里水潭里车水,水干了是下去抓鱼的,但不是总去车水。乡里人都是老实疙瘩,那时抓鱼摸虾让人说是不务正业。还有一条,豆豉如果总有鱼呀虾呀的这一年的豆豉可就不够吃啦。
苦日子也许就要在这里拐一个弯,但他当时还看不见。
拖车憨这一日得意的还有就是他的人客是个好漂亮的女子,闽南话叫水在户。过去,他老是拉一些歪瓜裂枣,要么是老梆梆的,要么是胖挤挤的,要么是外婆不亲舅舅不疼的,要么二傻不精的。一个黑不溜湫的拖车的是找不到眉清目秀的人客的,像今日这么水灵的还是头一回。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怎么就番仔婆比自己的女儿漂亮呢?她有钱,她穿得比自己的女儿好,她有秀嫩命,她白净,她不受风吹日晒,但好像还不止是这些。他不敢想但还是想,女儿的胸部是扁平的,番仔婆的胸部是鼓起来的。自己认为是老不正经的拖车憨在心里偷偷地认定还是鼓起来的好看。这是这一天拖车憨的一次心灵闪光。它将引出那年月让所有的乡里人都目瞪口呆的一整部的生活故事。当然,那时拖车憨还混混沌沌,感觉自己非常无耻非常萎琐非常见不得人。
拖车憨这辈子比较得意的是他的眼睛,他能躺在床上读天花板上的报纸,可从这一天开始他的眼睛花了。吃番薯的时候眼睛还没花,他还看清像黑豆豉的那只苍蝇,甚至看到那只苍蝇腿上的毛,那时他的眼睛肯定还没花。好像也不是遇到番仔婆时花的,他也是个坏眼儿,他也注意番仔婆牛仔裤中间不该有拉链的地方的拉链,他甚至连一扣一扣的拉链齿都看清楚了,那时他的眼睛肯定也还没有花。他不该拉番仔婆到溪边去,鬼使神差,那番仔婆怎么会想到要上那地方呢?她还找到那石将军被打下的头,那个头都多少年了,早就没了踪影,怎么就恰在番仔婆来的时候又冒了出来?她还抱起来给安上去,他认定是她抱上去的不可能是别人,这不是闹鬼是什么?那时他的眼睛花了吗?好像也还没有。他没跟那番罗罗的番仔婆走到溪里去,是她自己下去的,那时他就靠在车上闭目养神,那时他的眼睛不会花。会不会是那番仔婆到甘蔗地里撒尿,他在外面给她看着的时候?不是呀,那时他不由地从外边往里看,番仔婆走得挺深,连影子也不见了,但他还看清甘蔗叶子上的细毛毛,也不是这个时候花的。是吃饭的时候,她给他夹菜的时候,他的眼睛从她宽松的衣领溜了进去,看到她的乳沟。后来,他一直骂自己不是人,简直是天地不能容忍。但也还不是,他当时看到了后来懂得了叫乳罩的很好看的花边。应该感谢那东西,叫他没有犯下更加深重的罪。他真是老不要脸。可是吃饭的时候他还是每一道菜都看得清清楚楚,那诱惑他的每一滴油的光泽,都这样让他感叹不已。但他确实是眼花了,最根本的一条,他拉的人客究竟是什么样的他怎么也说不清楚。闭着眼睛他怎么也想不起她到底长什么样?后来想想,好像每一个线条都有点儿朦胧,都有一点虚虚的光,让他总有点儿目眩。
既看不太真又有点儿面熟,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啦是啦,她是长得像他的前妻,这让他无法相信让他不敢相信。整整几天,他就像做梦一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大白天的,他总是想这不是做梦吧?
拖车憨想他的前妻了,他头一回感到愧对前妻,几十年过去了,他恨了几十年,骂了几十年,到现今才明白她是一个好女人。真该死,他现在恨自己当时怎么会那样没心没肝,他到底干了什么呀。他害了她也差点儿把自己的小命丢了,全村人都以为他死了,让边防军打死在国境线上了。他真真是捡了条狗命。而她呢?命运是怎样折磨她的呢?她居然不恨他,把一个女儿养大了还这样让她不远万里地来找他,还从番给他带来那么多的东西,这真叫他没脸见她了。拖车憨也真的不能见他的前妻了,他自己已经有了老婆孩子,老婆又黑又丑又老,那是一面镜子,照出他也是又黑又丑又老。拖车憨的心早就虚掉了,他站在洋气的成了番仔婆的女儿面前都觉得自己也就是一个下人。现在,他的前妻只是他的恩人,是他的观音佛祖。他对她,从此只能仰视了。
原先是三个孩子伴,好得不能分开。吃饭从自家盛了一大碗番薯夹一小碗豆豉还要凑到一起吃,睡觉时也找机会凑一块块挤一张老式的眠床睡,一块脱光了从古井里打水冲冷,一块沿路捡拾甘蔗渣,一块在麦地里挖番薯秧。他们好到成人。好到那次台风,一场台风到底把他们台散了。三个人,憨仔,大粒,阿士。后来,他拖车人就叫他拖车憨,大粒去番因挣了钱没人叫他番仔粒而叫他金粒,阿士没去番可他办事不贴谱就都叫他番仔士。
悲剧已经酿成了到底是谁的错?怪那场台风?怪房子塌了?怪自己没钱修房子?怪大粒他老母逼他在家里成亲?怪番仔士出的鬼主意?怪大粒真的把钱拿出来?怪大粒还要假事真办?怪来怪去还得怪自己,怪自己穷,怪自己没本事,有本事谁会把妻子借出去?怪自己疑心重是自己生生地把那么好的一个妻子推出去的。后悔已经来不及,二十几年再后悔怎么来得及?想来想去只能说他就没那命,命里注定不是他的得到了也还得失去。可既然是命定为什么过了二十几年她还要来找?还让像仙女似的女儿不远万里回来找他?而且是这么一个叫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女儿。
拖车憨怀念起他的前妻那短暂的贫苦却恩爱的日子了。拖车憨的眼花是他想不起他的前妻究竟长什么样。那时他想仔细看看妻子,妻子在他热辣辣眼睛面前总是很害羞。乡下人那时白天是不关门的,他没有机会好好地看看他的妻子,没有好好地细细地看过她的脸,更没有好好地仔细地看过她的身子。夜里两个人睡在一起了,两个人做那个是不开灯的。他也对妻说过:让我看看。妻总是难为情。两个人是瞎子做爱。那时乡里人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躺下时是黑的,妻又总是比他先醒,他睁开眼睛时妻已经在做早饭了。只有一回他先醒,妻睡觉还穿紧身内衣,中间的一排扣子还密密的,他刚解开她的两个扣子妻就醒了,还敏感地一下捂住了。妻那儿都让他动过,却没有让他好好看过。他居然是看了女儿的胸部才发现那样才好看。前妻那达也是压得扁扁的,她从未充满弹性地鼓起来让他看过。
拖车憨突然惊讶地想起来,最近几年,倒是他的后妻经常是半裸体。乡下女人先是有了孩子,后来孩子大了女人的羞涩,甚至女人的感觉便都淡薄了,变得又粗又俗又黑又丑,自己索性就不把自己当女人看。乡下女人要洗身子只是拿块湿毛巾在身上擦,谁会看谁想看?大热天的洗了身子,算了,就光着身子,凉快。拖车憨熟视无睹,既没有唤起他男人的感觉也不觉得扎眼。妻的乳房不是两坨,是两条,是两条旧了的瘪袜子垂在胸口上。看它们跟看她的两条皱巴巴的胳膊没有什么差别。
一个故事结束了又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的就不是原来的故事。新故事是从前妻开始的,故事已经是女儿的故事。而故事的开始是一个老不正经的父亲眼睛从女儿宽松的衣领溜了进去,看到他不应该看的东西。不过拖车憨还不是一个不正经的男人,应该说他还有点儿刻板。不知不为过,他真不知道那仙女似的番仔婆竟然是自己的女儿,目不旁视的是车灯不是男人。他不得已典妻,他又耿耿一辈子。
对了,吃日罩时那一顿饭的时候,拖车憨在小饭店里遇到了阿士的儿子阿阔,那孩子都快30岁了,家里穷,还没有说上对象。村里人多叫他番仔憨。拖车憨,番仔憨,本来都差不多。但拖车憨认定自己这个憨是名字,而阿阔是个番仔,是个憨仔,番罗罗。
听人说,在地里干活累得要死,一收工,人都回家,就他是一个例外,他扛着锄就去大队部。他也不是什么干部他去大队部干什么?那里有公家订的报纸,他到那里看不要花钱的报纸。乡下人想:你学也上不成了,你回到乡里跟我们一样出臭汗,跟我们一样理锄头把,哪还显你认字,你算了吧。拖车憨当然也瞅不上这样的人。
在小饭店里,他也不合群,一个人跟谁也不搭话。这边人闹翻了天他还闷头喝自己的酒,末了剩下的酒,到底是喝不下了还是怎么着,没人招他惹他呀,他就把那酒从自己的头上浇下。酒是喝的他拿来浇头壳,这不是憨仔是什么?
不过,这是阿士家的事,拖车憨也不爱去打听。自从出了那档事,后来阿士自己又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了,拖车憨自己也差点儿把命扔在外头,回来后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很少搭话,也很少来往。拖车憨也认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但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事情却又回来了,回来找他,找他拖车憨。拖车憨就忙自己的了,还顾得了一个弄得让自己妻离子散的不管是有意无意的人的儿子,一个憨仔?
这一天对拖车憨竟是那么的重要。
拖车憨个人的这点儿丑事毕竟只是心里的事,但是,一件决定命运的事情,一个人生的转折点,难道说是从歹目,从坏眼儿,从拖车憨的老不正经开始的?
……
第三部:阿阔
一苇和早起的日光一块儿走进村子。
村子在吃饭。
……
注:《蚝壳土屋》原想分别用三个人物写三遍,《一苇》完成了,《拖车憨》未完,《阿阔》没写……但写作心境变了,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