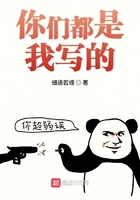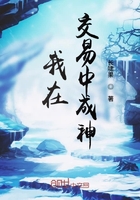世界文学作品,能够问世的,算得上是车载斗量、汗牛充栋了。但千百年来,为我们所知悉的,是经过大量淘汰的。再排除天灾人祸的劫难,沧海遗珠的厄运,它们之中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散失泯灭,屡经读者筛选而巍然留存,终能代代相传,并被公认为后世学人必读的名著,细探原因,都不是偶然的。当然,幸存与否,确有机缘遇合种种因素,但是总的说来,披沙拣金,能传世必有其本身“站得住”、“经得起敲打”的道理。本文就想从这里探求一下诗作能够传之久远、历久弥新的原因。
诗歌作品,从表面形式粗略分类,有“少而精”和“大而全”两种模式。难以名状,前者姑妄称之为短篇零句,后者暂且叫做长篇巨制。若论前者,那诗作者或仅有寥寥可数的几篇,或只有一首,甚至几行诗句,然而的确够得上立意新颖,情真意深,力透纸背,荡人魂魄的水平,读者遇之,每每不会轻易放过,有如华兹华斯,在湖边偶然瞥见那一片绵延不断的黄水仙那样地欣喜赞赏。这类诗歌的作者可以是作家,也可以不是。奇怪的是,这些作品有时自心里喷涌而出,纯属天然,以后就是同一作家再殚精竭虑,苦心孤诣,也写不出来了。
后者是巨制。这一类诗中西皆有,而以西方为多。因为西方多叙事诗,自荷马起就有写长诗的传统,各个时代都不乏长诗杰作。这类作品因其卷帙浩繁,易受重视,较易流传,不像零篇短小,易被疏漏,出生后夭殇的可能性大。同一诗人,其少而精的作品会附属在他的巨制中而幸存。当然,一个人的巨制中少不了因为蕴涵震烁古今的睿思隽语而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诗的疆域里,零篇和巨制似各有分工:零篇多横剖,巨制重纵述。荦荦长篇雄据中西诗歌这片千里沃野上,如峰峦叠见,峥嵘竞秀;零篇则如小溪清泉,澄净晶莹。在大自然界各有各的位置,在鉴赏家和批评家的严峻的尺度前面,其审美价值是一律平等的。谁能说有了太阳就废弃了月亮星辰的光辉;有了牡丹、玫瑰,就抹杀了幽兰、雏菊的芳馨?
再说,诗作或少少许有三言两句,或多多许有千句百行,落笔或疏简或满密,效果各有千秋,它们分别有不可互相替代的文学价值。下面将谈谈短篇和巨制的特征,并略举各自代表作进行赏析。
我们先从内容上来看,巨制一般具备这样几种特征:(一)它最善于写历史上的片断故事,绘影绘声,富知识性和趣味性;(二)擅长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褒善贬恶,爱憎分明,富戏剧性和生动性;(三)喜谈个人身世,不厌其烦,希求人知,有自传性……总之,作者驰骋才力,开拓诗疆:写征战讨伐,从军报国;写民族意识,爱国情操;写流浪历险,异国政事;写英雄侠少,绝代佳人;写友谊爱情,生死不渝;写个人悲欢,飞腾坎坷;针砭时事,忽喜忽嗔;写山川景物,自然风貌,体物工致,应有尽有;有时也缅怀过去,憧憬未来,鞭挞现实,寄托理想。凡此种种,几乎无所不包。这种记述和论事方法自然非长篇巨制不足以容纳。它有情节,有步骤,有层次,有起落,有时主观抒情,有时客观叙事,因其气象万千,措辞精妙,人们或听或读,沉迷忘倦,故虽长篇,并不觉其累赘繁琐,反喜其娓娓动人。其诗作有中心思想和系列故事。我们揣摩诗人的宗旨,则不难觉察他们是有为而作。他们述志论道,扬善斥恶,持现实主义的思考,也写出浪漫主义的理想。他们有对邦国社稷的恢宏意旨,寄寓遥深,对道德情操标准较高。长篇巨制气魄雄浑,叱咤风云,表现诗人不同流俗的胸襟抱负。它们在历史画册上频添绚丽的色彩,是诗歌史上绵延不绝的主脉。在具体分类上有叙事诗、史诗、神话故事诗、传记诗、情诗等等。有的先口头相传,再形成文字,所以使散文句法入诗的也不少见。它们给予我们认识价值,欣赏价值,是毋庸多说的了。
唯其如此,巨制的作者,必是彪炳史册的大家。在诗歌史上,他们的姓名显耀,无人不知。读欧洲文学史,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荷马、乔叟、歌德、拜伦、普希金、海涅,正如读中国文学,必然记得屈原、李白、杜甫、李商隐、龚自珍的名字。他们大多数人刻意为诗,终生以之,衣带渐宽终不悔,语不惊人死不休。天才与工力都能达到极高的造诣,享有世界声誉,自是理所当然。
至于零篇,有时也出自大作家手笔。但通常是人以诗名,人们或知其诗而不知其人,甚至是无名氏之作。有了零篇,人才能成为名家。或者其人本不作诗,偶尔写得少许一点,却如同美妙的琴声能拨动读者的心弦。我以为愈是这样无所依傍,纯以作品取胜的零篇,愈是难能可贵。如果说巨制可以纵览宏观,那么就应该说零篇可以横剖微观了。要谈零篇的特征,则不妨一言以蔽之:作者触物有感,如鲠在喉,急于捕捉那一刹那间的思想感情,内容贵在真淳。技巧方面又似乎是随手拈来,如有神助而成篇的。天韵自然,不假雕饰,看来容易,却往往又是大作家呕心沥血也写不出来的。比起那些宏伟的史诗、叙事诗来,它们只能算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虽一闪而过,却留给人永世难忘的印象。它们有如玲珑小巧的钻石,光度有限,却晶莹剔透,具有惊人的生命力。零篇的作者群比较复杂,既有文人雅士,也有不识字无文化的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市井平民,“贩夫走卒”,僧尼道士都有,也不乏娼妓优伶之作。他们的作品来源于生活,情发乎中,捉笔成句,可惜流传的极少。而可供我们阅读欣赏的零篇仍不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作品。这在中西社会里都是普遍的。
说到这里,不妨举几个有趣的实例。据英国史学家“可尊敬的贝德”(the venerable Bede)的记载,英国第一个基督教宗教诗人是7世纪的一位牧人,名叫开德蒙(Caedmon,约生于670年)的。他不识字,中年时在一个夜里,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使呼唤他的名字,命令他写歌颂创世主上帝的诗。于是他就照着写了,醒来还依稀记得,就照梦中的诗的模式写下一些《圣经》故事诗,如《创世记》和《出埃及记》等,叫做《开德蒙诗歌》。原作我们读不到了,但据贝德记载,有三首题为《堕落的天使》、《地狱的苦难》和《诱惑》,确实是开德蒙的作品,尽管这是难以置信的。其中有这样的诗段,是通过撒旦的口说出的:我为何要做奴隶?
我为何要为主人服役?
我双手能创造奇迹,
更高的宝座我也能在天上建立,
那为何要在他面前卑躬屈膝?
为何要向他乞怜做奴隶,
我本来可以像他一样做上帝。开德蒙的圣歌是英国土壤上幸存的最早的诗歌,而牧人开德蒙也就成为英国最早的有名有姓的诗人了。他的出现比英国文学之父乔叟要早出670年。撒旦的形象以后在弥尔顿的《失乐园》和拜伦的《该隐》等长诗中扩展而为反抗专制压迫和暴政的英雄形象了。
中国的汉高祖原本是一介武夫,不会舞文弄墨。然而在他战败项羽,统一中国,回到故乡江苏沛中时,召父老子弟纵酒,他自己击筑唱出《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气吞牛斗,把一个泱泱大国之君奠定汉帝国基础,力图永保国威的浩荡之志刻画入神。这位皇帝出身微贱,略知民间疾苦,自他以后立“乐府”,采诗夜诵,继续了一百年。变官为民,乐府就从贵族宗庙乐章演变为平民闾巷歌曲了。
开德蒙与汉高祖纯属两个阶级,他们无心做诗,却如有神助,各自倾吐了不同阶级的情怀。因其意真,所以写出了名篇。
这些是零散不全、寥寥可数的数段数句,甚至它们的作者也真伪莫辨,传说不一,但从诗的本身而论,着实富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因为其少,故极易被疏漏忽略,但因其精,其价值便不因其短小而减色,反而能传之久远,获得绵延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