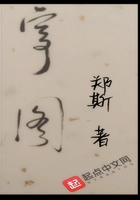我离开了被日军占领的北平和天津,但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更深地卷入了战火。由于无法进入上海,我被合众社派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从那时起,我从前线和后方两个方面报道战事动态。
还在去南京的火车上,我就尝到了挨炸的滋味。其实,我在天津就已经不是空袭的旁观者,而是亲历了南开大学被轰炸的苦难。此后,我经历轰炸的场面达数百次之多。
到达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合众社的办事处过夜。半夜,我突然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和高射炮声惊醒。我忘记了危险,一骨碌爬起来到窗前观看,只见防空系统的探照灯和五颜六色的曳光弹交叉照射。后来我下楼到外面去,看见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四肢不全,有的还完整),这时我才清醒过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在宵禁的空袭声中睡觉。合众社在上海的总部还不时打来电话,我习惯了在忙乱中偷闲打盹。我再也不会由于担心害怕而彻夜坐着,不敢入睡。不管怎么轰炸,我照睡不误。这个本事对应付以后的许多危难是很有用的。
日本对南京的轰炸起初只是偶尔为之。它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进行恫吓,另一方面谋求休战,以求达到使中国投降的目的。在国际上,它请德国的外交官进行调停;在中国内部,它利用汉奸和失败主义者。在这些努力都失败后,它在1937年9月发出最后通牒并加紧空袭,有时日夜轮番轰炸。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有意识地对一家红十字会大医院进行轰炸,那里住满了当地的病人和来自前线的伤兵。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想打击南京的士气,告诉所有有关的人:即使伤病员也不能幸免,也会在病床上被炸得血肉横飞。
我看到过一些伤兵,他们成为国际上禁用武器的牺牲品。芥子气把他们的皮肉腐蚀成许多干酪似的小洞,并深深地进入躯体,疼痛难忍。日本人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我后来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许多。后来查明,他们还在中国试用过传播病毒的生物武器,散布了像鼠疫、炭疽等致命的病毒。
但是,南京的人民没有被吓倒。每当敌人的轰炸机被中国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冒着火光和浓烟栽下来并爆炸成碎片时,欢呼的人群总是不顾危险,冲向现场。有一次我还看见宋美龄站在敌机的残骸上。作为航空委员会的头头,她似乎是在工作。她倒不缺乏勇气。
作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军政机关密集,到处是高楼大厦和林荫大道。在这里,处理紧急情况是由穿着漂亮制服的警察和宪兵负责的。每当响起空袭警报,他们立即静街,命令行人进入新建的公共防空洞里。这些所谓的“防空洞”,结构简陋,只不过是加了一个顶棚的堑壕而已,防备飞来的弹片和玻璃还可以,对直接扔下来的或者在附近爆炸的炸弹就不中用了,即使是对付轻型炸弹也不行。轿车和卡车都用绿色植物伪装起来,停在路边的树阴下。
在南京市中心,乍看起来,似乎瞅不见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的衣衫褴褛、补丁摞补丁的穷苦百姓。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这样的人,原来他们住在涵洞管道里,或在空地上临时搭建的窝棚里。
即使如此,炸弹似乎也不放过他们。侵略者试图保留那些最豪华、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以便他们占领以后自己居住。在那些既有漂亮的宫殿似的建筑物,又有简陋木屋的地方,炸弹总是落在后者的身上。
不过,社会气氛慢慢地开始发生变化。原先,有两个南京。一个是趾高气扬的新首都,那里有宽阔的林荫道,有衣冠楚楚、戴着白手套的军官,自命不凡、懒洋洋地坐在名牌轿车里的高级官吏以及住在美式豪华套间里的大腹便便、忙忙碌碌的商人。另一个南京是老南京人居住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穷。现在,被击落的每一架敌机都是老南京和新南京的共同胜利,特别使穷人和难民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穷人遭受战争灾害最大,由于家园被毁而不得不背井离乡的难民最恨侵略者。
1937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六周年,战时的南京举行了首次全市规模的群众大游行。来自北平和其他不久前被占领城市的学生们被允许进行公开的宣传鼓动活动,呼吁更加坚决地武装全民进行抗战,而不仅仅是依靠职业军人作战。首都强有力的电台第一次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它的歌词铿锵有力,具有动员力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如前所述,几个月以前我在天津第一次听到它,那时它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禁唱的。
在那个情况复杂的1937年9月,我还观看了北平和天津学生会话剧团的一次演出。他们来自沦陷的城市,在前线巡回演出。他们那些富有鼓动性的独幕“活报剧”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写成的。《保卫卢沟桥》描写了战争的爆发;《北平之夜》是沦陷后一家地下报纸编辑们创作的;《大鼓词》是在地道的农民音乐的鼓点下发出的爱国号召,是早期用民间艺术反映时事的一种激动人心的尝试,在后来中国的战时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战争不时被舞台以外的真实战争所打断—日本飞机俯冲下来投掷炸弹。一位歌手满不在乎地说:“在卢沟桥,我们经常听到敌人的炮声。”一颗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震得建筑物摇摇晃晃。他的反应是高喊:“看看敌人的暴行吧!什么东西都不能阻止我们,直到我们把敌人赶下海!”
我想采访学生领袖,记下了他的地址。一两天以后,当我去找他时,话剧团的一位女团员对我说:“他在宪兵司令部。”宪兵把他传唤去,借口是这个学生会没有登记注册,至今还没有放他回来。
这就是当时南京的情况,有好,也有坏。一方面,面对日本的侵略,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出现了结成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的迹象;另一方面,当局专横霸道,肆意镇压,一如既往。不过,比以往略有收敛,这倒也是事实。昔日,学生一旦被捕,可能无限期地被拘禁,严刑拷打,甚至被秘密杀害。如今,他们被捕后,常常过一个星期就放出来了。
不幸的是,这种缓和的局面仅仅在战争的第一年维持下来,后来就不行了。
由于同国民党达成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向南京派了一个常驻代表团。我第一次见到了它的公开的代表。虽然中共代表团的存在是合法的,但是国民党的官僚们不愿意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尽可能不让好打听的新闻记者们知道它的具体驻地。
我在去采访这些真实的红军长征战士们之前,总以为他们是一些表情严峻的老军人,经过10年的残酷斗争而变得疲惫和坚强,很可能难以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