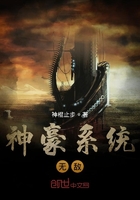一连几天,沈三白见了孙天一,说话总是冷嘲热讽、阴阳怪气的。孙天一也不同沈三白争执,只是假装没听见一样。偏偏冷云冰又说到了十佳外来工竞选的事,说,沈三白你也可以参加竞选的呀,你都是南城的名人了。沈三白说,我算哪门子名人?别看我这人平时嬉皮笑脸没个正经,可我沈三白不虚伪,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不像有些人,一天到晚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可背地里尽干着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正说着,来了个漂亮的女作者说要找沈三白看稿子。沈三白倒是认真地看了,提了些意见,又说了些鼓励的话,女作者千恩万谢地走了。冷云冰突地笑了起来,沈三白说,冷老师您笑什么?冷云冰却不说话,只是笑,笑够了才说,我发现沈三白对女作者特有耐心。是不是有好多女作者喜欢你。沈三白说,冷老师这您可就错了,我沈三白虽说是有点花心,但我从来不借文学的名义和女作者乱搞。我最讨厌的就是和女作者勾勾搭搭的人。孙天一知道沈三白这话里有话,是在影射他和简洁如,心里的怒气腾地窜了起来,将手中的一沓稿子用力地往桌上一摔,出了编辑室,一口气跑上了大楼的楼顶,呆坐了足有两个小时,心里的燥气才渐渐消了。下到办公室时,办公室的人还在有说有笑,见了孙天一,同时闭了口,各自埋头做事。孙天一知道他们在拿自己说事,也懒得理会,心想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可是,现在我还能说自己的身是正的么?孙天一苦苦地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声。至此,一连半个月,孙天一每日早上按时上班,下午准时离去,却总是一言不发,仿佛哑巴了一样。沈三白开始还说一些嘲讽话,但孙天一似乎再也不为所动,反倒觉出了自己的无聊与可鄙。渐渐地,上班时也不再像一个长舌妇一样说东道西了。
有些日子了,孙天一是逼着自己不要去想简洁如的,也有意避着简洁如,简洁如打来电话约他出去,他都借故推脱了。过了几日,觉得越是这样,反倒越是无法忘却简洁如,又觉得自己活得这样谨小慎微似乎太过于窝囊了,倒不如一切顺其自然的好。因此简洁如再次打电话来说有事要见他时,孙天一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半月未见,这次简洁如较上次见面时更加憔悴,脸色不再是苍白,而是有些蜡黄了。虽是薄施了脂粉,却也无法掩饰那份倦怠与憔悴,而那双本来让孙天一心动不已的眸子,也蒙上了一层黯淡的阴影。眼袋有些红肿,眼圈也有些发黑,见了孙天一,眼里的泪就要往外涌,居然一头扑进了孙天一的怀里。孙天一拥着简洁如。两人就这样久久地拥抱在一起,心贴着心,彼此感受着对方的心跳,感受着彼此的烦恼与忧伤。
你瘦多了。简洁如说。
你也是。孙天一说。
你………是后悔了么?简洁如将头埋在孙天一的胸前。后悔什么?孙天一问。简洁如说,后悔认识我。孙天一说,…………不后悔。你呢?简洁如说,我以前最恨的就是破坏别人婚姻的女人,没想到我也成了这样的人………不过,我不后悔,我不会破坏你的家庭。你也不要因此而为难。孙天一说,你不明白的。我不是因为这事而烦恼。如果不是你的出现,也许我现在还要烦躁的厉害………。简洁如说,我们去凌云观好么?孙天一说,去凌云观,干吗?简洁如说,想去你说的那块石头上坐一坐。还想见一见天佑和杨志。
孙天一和简洁如上到凌去观时,已是晚上七时。其时正值南城盛夏,落日刚从西边的山脊落下,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南城的高楼,已渐渐被苍烟落照笼罩。两人携手攀到山顶的凌云观,凌云观的建筑已近尾声,脚手架、钢筋横木都已清除,建筑工人也所剩无几,不过做些细致的修补工作。夜幕降临,山上已是冷冷清清。大殿的门并未合上,却未亮灯,殿里便显出了一种幽深与神秘。镀金的原始天尊像在朦胧的光影里更显庄严肃穆。孙天一轻声叫了两声天佑,却无人应答。拉了简洁如的手,在殿里转了一圈,没有见人。两人正要退出,却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雕塑一般堵在了门口。身影仿佛幽灵,何时飘到大殿门口,两人并不知晓。简洁如蓦地一见,吓呆了。孙天一也捏紧了简洁如的手,一步步挪上前,请问,在这儿画壁画的那个人还在么?那人进了殿,侧身站在门的一边,说,天佑呀?他下山有好些天了。孙天一问,壁画完工了么?黑影说,尚未完工。你可是孙天一小友?!孙天一此时也认出了眼前的黑影是广德道长,欣喜地说道,正是。道长近来可好。广德道长便摸索着将电灯开了。一瞬间灯光刺眼,半天才适应过来。天一小友,这么晚上凌云观寻天佑有急事?孙天一说,也没什么事。陪朋友一块儿上来坐坐。说着介绍了简洁如。又说,道长您忙,就不打扰了。广德道长说,那二位随意。天黑了,山上坑坑洼洼的,走路小心一点。虽没有野兽,却也要防着蛇虫。孙天一道了谢,拉了简洁如,两人便循了那日寻出的小径,摸到了那方巨石上。简洁如将身子偎进孙天一的怀中,也没有言语。孙天一轻抚着简洁如,手指在她的身上轻轻游走,蛇一样地滑进了简洁如的衣内,便触到了她那坚实小巧的乳房。简洁如没有丝毫的反抗,也没有显出兴奋,只是如同睡着了一般,任凭孙天一摆弄。孙天一的身子燥热了起来,热血在急速奔涌,尘根坚挺竖起,呼吸也急促了起来,手指笨拙地解开了简洁如的衣扣,顺着平实的小腹,侵入了那片水草风茂的湿地。孙天一正要将自己与简洁如合为一体,蓦地觉得一团蓝幽幽的光从眼前一闪而过,却浮在了头顶上方,状如草帽,在飞速旋转。孙天一惊得张大了嘴,他是想发一声惊呼,一句感叹的,却只是张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简洁如此时也看到了那团蓝光,骇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孙天一。蓝光越来越强烈,四周的草木都镀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荧光,晶莹剔透,清晰可辨。树木、山石、两个抱在一起的男女,都变得透明了起来,仿佛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水晶制作的。忽地,那团荧光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直地升向了宇宙深处,最后变成了一颗星,在深邃的天幕深处一闪一闪。一切又归复了黑暗,相拥在一起的孙天一和简洁如此时都已全身冰凉。两人足足呆了半个小时,才如梦醒一般。无言语动作,唯余山风如梳,夜凉如水。
如此沉默又沉默,两人只是将对方拥得更紧。这时在孙天一的感觉里,拥着简洁如的胴体,已无一丝肉欲,内心有的只是一种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与恐惧。他想到了一个词:相濡以沫。简洁如首先打破了沉默,是飞碟呀!真的是飞碟哩………宇宙中未知的事物太多了,相比之下,我们做人一世,真的是太可怜了。孙天一却说,我不该在这圣洁的地方乱来的。两人不再说话,只是相对而卧,何时入睡,竟然不知。
一连几日,孙天一再无同简洁如联系,简洁如也未来电话。这天一早,孙天一刚到杂志社,主编何子恒就一脸不悦,说,孙天一,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孙天一满腹狐疑地进了何子恒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却很面生。何子恒冲着那人说,这就是孙天一。那人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便作了自我介绍。原来是市十佳外来工资格评审办的张干事。孙天一心里掠过一丝欣喜,心想恐怕是那一幅字起了作用。张干事从档案袋里掏出一沓资料,却是孙天一上报的个人资料复印件。张干事粗略地问了孙天一几个问题,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结了婚了吗?孙天一说是的。张干事说,那你爱人在哪儿工作?孙天一说,本来在一家超市上班的。前不久超市搬迁了,现在闲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张干事说,哦——孩子多大了?孙天一说,五岁了,上幼儿园大班。张干事用手摸着下颌,沉吟了半晌,字斟句酌地说,是这样的,最近呢,我们接到一些反映,说你………在外面包二奶,………当然,我们是不会听信片面之词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调查的。希望你能配合我的工作。孙天一的脸早已涨得通红,终是按捺住了心头的怒火,冷冷地说,谁反映的?张干事说,这个,你就不要打听了,对于举报的群众,我们有保护他们的义务。我今天来,就是要核实这件事情的。孙天一苦笑着摇了摇头,说,像我这样的打工仔,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一家人的开销,哪里有钱去包二奶?就算我有这份心,也没有哪个女孩儿会瞎了眼跟我呀。张干事讪然一笑,说,这个,我也相信你。不过请你谈一下,你同一个叫简洁如的打工妹是什么关系?
………孙天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用手指了指张干事。现在他是什么都明白了,知道他在参加十佳竞选的人不多,而知道他和简洁如之间的事的人就更少了。
小孙你别激动。坐下来慢慢说。张干事说。
孙天一却一把抓了桌上的资料,用手撕了,边撕边说,我不参评了还不行吗?说完冲出了何子恒的办公室,摔门而去。走进编辑室,却见石古正同沈三白在一块儿嘀咕什么。孙天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冲了上去,一把抓住了沈三白的衣领,甩手就是一个耳光。沈三白被这一记耳光打懵了,张大嘴巴呆看着孙天一。孙天一又狂叫着扑上去,一把卡住了沈三白的脖子,厉声叫道,姓沈的,我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你在背后动刀子告黑状。
沈三白奋力掰着孙天一的手腕。石古见状,忙上去抱住了孙天一,劝道,天一你疯了。有话好好说嘛。孙天一也不答话,作势往前扑。沈三白没想到平时说话温文尔雅的孙天一发起狂来如此厉害,直往后退,嗫嚅着说,你别胡来。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石古却说,老孙,看我的面子,大家都是朋友,有话好好说。嘁!孙天一冷笑道,朋友?我高攀不起,不过是酒桌上的朋友罢了。看你的面子?你石古是什么人?在内地弄假新闻惹了事待不住了,跑到南城来还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以为你和沈三白演的那出把戏没人知道哇?我只是不想揭穿你们罢了。沈三白你把手放在胸口想一想,我孙天一要像你一样,把你的那点破事给捅出来,你能有什么好下场?还有,你可以去问问江上舟,当初江上舟本来只推荐我一人的,我怕影响同事之间的感情,才建议连你一块儿推荐了。我要的是我们之间的公平竞争。
公平竞争?沈三白见孙天一已不似刚开始那般疯狂了,摸着被卡痛的喉咙,冷笑道,孙天一你他妈的别一本正经了。若要公平竞争那你到沈主任家干吗去了?我是用了一些招儿,可我不像你,为了竞争十佳去讨一个老娘们儿的欢心,去吃软饭。
办公室里早已聚满了人。大家都在劝:好了,好了。内心却是巴不得他们快点打起来。开始听孙天一揭沈三白的底,听得一片嘘声。现在听沈三白说孙天一吃软饭,更是竖起了耳朵,恨不能催沈三白快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个底儿掉。
孙天一被戳到了痛处。虽说上次他去沈亦凡家送礼与吃软饭是两码事,可他内心深处是羞愧的。现在被沈三白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提起,顿时老羞成怒,顺手抓起桌上的一杯水朝沈三白脸上泼去,泼了沈三白一身的水。又抓了桌上的一瓶墨水要往沈三白身上砸,闻声过来的何子恒吼道:孙天一,你给我住手。孙天一一愣神儿,垂下了手臂。何子恒冲围观的人喝道:看什么看,还不去做事,不想干了!又说,孙天一,沈三白,你们俩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何子恒将孙天一狠狠地骂了一通,又顺带着批评了沈三白,勒令二人各自写一份检讨书。再回到编辑室时,石古已走了。沈三白伏了案去写检讨书,孙天一也拿了笔,在纸上画出“检讨”两个字,猛地又揉成一团,丢进了纸篓,却奋笔写下了“辞职书”三个字。
将辞职书交给了何子恒。走出杂志社大门时,孙天一感觉整个人仿佛被掏空了一样。在《异乡人》的这几年,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情感都倾注在了这份杂志上。他无数次的为了外来工的权益而奔走疾呼,他恍惚忆起了初进杂志社时的那份豪情与憧憬,他在名片上印下了“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的豪言壮语;还是那年,他接到一名打工者的求救信,说他进了一家黑厂,在里面受着非人的虐待,被限制着人生的自由。他冒着生命危险进了那家黑厂卧底打工,后来协助警方一举端掉了那间黑厂;他还记得,有一次正在上班,办公室突地冲进两个凶神恶煞,问谁是孙天一,幸好一位同事机灵,说孙天一不在,出去采访了。来人抽出砍刀砸在桌子上,扔下一句话,说你们转告孙天一,叫他以后少管点儿闲事,否则………;他还记得,那年他们到西区和外来工搞联欢,当主持人说出孙天一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春雷一样经久不息的掌声…………现在,这一切都将与他无关了。在这个别人的城市,他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不想回家,他怕面对于妻子的询问。也不想去找简洁如,他不想让简洁如看见他颓废的样子。他就那样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街,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手机呜呜呜地在唱,他懒得去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街灯将夜幕点缀得扑朔迷离。孙天一在街边公园的草坪上坐了下来,他觉得很累很累,他躺了下来,不知不觉,便呼呼地睡了过去。
孙天一是被查夜的治安员弄醒的。那时孙天一正在做梦,梦见自己在天空中像一只大鸟一样飞翔。猛地,被人一枪打中了翅膀,又一枪,打中了胁骨。孙天一被一阵痛楚惊醒时,治安员的第三脚已踢在了他的屁股上。
起来起来。一个治安员吼道。孙天一揉了揉腥松的睡眼,说,你,凭什么打人?凭什么?治安员冷笑道,凭老子是治安队员,你是三无。孙天一一骨碌爬起来,揉着发痛的胳膊,说,谁说我是三无?说着掏出了暂住证。治安员看也没看便抓过来丢在地上,也不待孙天一再掏其他证件,扯了他的胳膊便往停在路边的警车那边拉。孙天一踉踉跄跄地被拉到了警车前,却忽地看见了孟广虎。孟广虎这时也看见了孙天一,忙过来握了孙天一的手,说,哟,孙记者,怎么会是你?
孙天一摇了摇头,按着发痛的太阳穴,苦笑道:睡过头了。孟广虎拍了拍孙天一的肩膀说,对不起对不起。又冲那个治安员骂道:你们怎么搞的,不问明身份就乱抓人?把大记者当三无人员了。那个治安员忙过来赔礼,说:对不起,我——孙天一说,我已不是什么记者了。孟广虎一惊,开什么玩笑?孙天一说,今天刚辞了职。孟广虎默了一下,说,孙先生这么有本事,多得是好单位抢你哩。又附在了孙天一的耳边说,多谢你上次帮我写的那篇文章哩。孙天一瞪大眼说,怎么 ?孟广虎得意地说,就凭那,我参评了今年的十佳外来工。参加终评的资格审议已通过了。孙天一说,是吗?那祝贺你呀!孟广虎说,要是评上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哩!………哎,我说,你做得好好的干吗要辞职呀?孙天一说,…………干得不痛快。孟广虎说,孙先生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走,我请你去吃宵夜。孙天一也觉得肚子咕咕乱叫,便道,好吧。孟广虎让手下的治安员将抓来的三无人员押走,自己带着孙天一寻了个夜市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