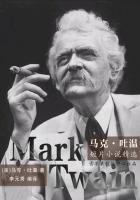月光照在荷塘上,一池的塘水被染上一层白光,时不时从里面传来一阵蛙声。
我由着阿婉将我重新带回凉亭。
月明星稀,没有乌鹊南飞。有晚归的学生自荷塘边经过,怔怔地看着我们,阿婉一眼扫过,如受惊的飞禽,一下四散开来。
天色真晚了,两个正常的女孩子不该此时孤身在这香径通幽处私会。
阿婉似是也意识到,好看的双眉微蹙。她望着满塘的荷花,目光迷离。
她说:“比起不屑,我对你更多的是恨。”
我诧异,不觉抬头望她。我不曾做过对不起她的事。
她看了我一眼,月光下,一向自信高傲的她神情落寞:“是啊,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我恨你是因为乔木,因为他说一万个我,也不及一个你。”
我难以置信。
我似乎明白了些从前不明白的。
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怕说错话让她更不舒服,让我们本就如履薄冰的关系彻底破裂,便只倾听她说。
“我想破脑袋我都想不出我哪里不如你。”她突然回转目光,望向我。“不如你说说看我到底哪不如你?”
我看着她,仔细的想了想,摇了摇头。
我确乎没什么比得上她的。
阿婉笑了笑:“那风回雪呢?”
我的眼前闪过风回雪清丽脱俗得如冰一般雪一般清美空灵的容颜:“我对她所知不多,只有其表,但就才貌而言,你没有什么不如她的。”
“也没有比她出彩,对吗?”
我犹豫了下,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阿婉看着月亮喟然长叹,“可即便如此,我不也不比她差吗?为什么他们一个一个都不喜欢我?为什么?”
相识十数载,这是她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失态,让我看见她的脆弱彷徨和无助,让我忘掉她所有的不好,想要不留余力的关怀和帮助她,让她快乐,就象我曾经奢望我们可以的那样——不必有福同享,但是有难必当。
感到她的手在微微发颤,我想伸出手臂拥抱她,给予她温暖。但忽然而起的猛烈西风让我停了停。
飒飒西风里竟连香气似是都染上荒凉寂寞的味道,花前月下的温馨场面一下变得凄凄切切。
阿婉将手搭在我的手腕上,顿了顿站起来。
她把画轴卷好,郑重地把画交到我手中,以最后的嘱咐结束了这番恳谈:“我让你得见乔木,本意虽不是为了成全你们,但决非不安好心。”然后,她迈步兀自离开。
我抬步欲相随,她却回头制止:“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见到你。我走后你再走吧。”
我没想过她会这样不留情面,立在原地一下懵了。
我更不知道自己何以平静的开口:“好。”
我只知道阿婉走后不久后,我想离开的时候开始下雨,怕画弄湿我不敢离去。想等雨停,雨却越下越大,我呆呆地听着,忽然间一阵无由的恐慌。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趴在石桌上睡着。
我做了许多悲伤的梦,梦见妈妈说的我上面那个长的重眼花皮很好看要是还活着,一定把我送人的姐姐和乔木流动着笑意却甚是忧伤的眼睛说人最要不得的便是自作多情的画面,又恍惚听到妈妈因为我逃婚,气的目不能视物,痛呼没有我这个女儿。醒来时我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