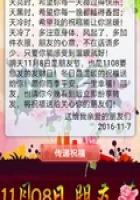一
说《再说严学章》,是因为我说过一回他的。在几年前,行文中,对他还算周正的“猫脸儿”有过几笔描写。话说的或许是有点损,文章发表后,他老婆不乐意了,电话打过来,说:“我老公长得就那么丑吗?”天下的女人们,都以为自己的男人是潘安。
倒是有张照片还说得过去。一张黑白头像,是位名牌摄影师拍摄的。据说拍了好几卷,百几十张。那一张,就是从百几十张中挑选出来的。放到报纸那么大。最早悬挂在惠安巷口一个影楼的橱窗里。这个橱窗挂的大都是襄樊文艺界的名人照儿:涂廷多、黄耀辉、杨小琳,还有谁谁谁。严学章挤在里面,头脸微微的上仰,把一只眼看向远方(侧面,只能看到一只眼),又像是没有看向远方,做思索(或是求索)状。表情拿捏得比较到位。看得出,摄影师为这张照片是费了一番功夫的,或站、或蹲、或绕着他用取景框“框”了又“框”的,并讲了一些艺术家精神气质一类的话,然后才用白亮的灯光,照准“精华”,隐去“糟粕”叭叭了好一阵子才弄到这么个效果。“猫脸儿”是没有了,但和生活中的严学章也不太一回事了。
一日,我送小儿上学,远远地瞧见他立在惠安巷口,正抬脸凝神地望着什么。
又一日,橱窗里就空出一块白。
我说:悬在那很光鲜很惹眼啊。
他说:那不是我。说话时语气恨恨的。
恨谁呢?没好问他。
二
严学章是名人。因字而名。人怕出名猪怕壮。自打他以独特的个性闯入书坛,数次入选国展,数十次荣获大奖,书坛就不怎么平静了。吵吵闹闹的,褒之贬之,莫衷一是。《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画报》、《美术报》等艺类刊物干脆辟了专栏任人评介。这么着,就有了很多的说法(印象中都是关于他的一些错觉),比如说他的字很怪,笔墨很邪气,还比如有人按美术的分类把他编排到“现代派”“前卫艺术”一路等等。凭直觉,这样分类似乎不太贴切(也不尽人情),可又不好怎么去反驳,因为他的确有好多的地方让人看他不懂,——出手就是“刀削面”、“螃蟹腿”与传统的用笔用墨(审美形态)相去甚远,常人接受不了啊!写到这儿,想起两件旧事,不妨当故事讲讲。其一,是河南的一位朋友,久慕他大名,要求一见。找到我,我说没啥见头。他不信,从千里之外赶过来,硬拽着扯着我到文联,见了人又看了字,结果却愣愣地不言声儿。我问他咋样。他趁严学章入厕的时间,叹了口气,用右手食指弹弹严递给他的名片说:“都说他是书法家,咋整的,这字儿,还不如我儿子写得好看呢?”
其二,是去年的事。樊城定中街的宝后斋,宝号是严学章写的,一位自诩为书道中人的老者,每每皱眉踟躇于前,斋主朱杰奎先生以为是观摩学习的,便微笑着主动搭腔,没想那老者一脸怒气,质问朱先生:“严学章在市委是不是有后台呀,凭么事写一手“鬼画符”的字,还当书协的秘书长、副主席?”
听到这些话,严学章不争不论,抿着嘴儿笑一笑,完事。
也有人劝他换换门庭,“大众”一点。但是没用。他说:“再怎么着,那也是我自家的面目呀!”
陡然地记起一句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就是严学章了。这样一想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取下惠安巷口的那张“美人照”了。
三
我们的书坛,百年千年地因袭二王、欧颜柳赵,这成了书法的正径,沿着这条正径,一般比较好走。即使再不济,也能把毛笔字写得工稳清秀,也能帮人写写对联儿受到人们的称道。可惜,这些严学章是做不到了。用一位大书家的话说,严学章走向了传统的背部。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是背部,少得阳光,更多阴湿,更多泥泞,路更难走?他一头扎进北魏墓志十几年,反复在《嵩山灵庙》、《好大王》、《鞠彦云墓志》等残石断碑间,寻寻觅觅,披沙拣金,再蓦然从“墓”里拱出来时,就劈面惊人了,就成了现在的“螃蟹体”了,——点画粗阔,造型扭曲,构图奇险,视觉怪诞;白处一片白白,墨处墨胆包天;其势如裂石破土,其形如醉汉过招。看他的字,有如看钟馗驱鬼,胆大者增勇,胆小者掩面。
赢得了一些人,又吓跑了一些人。想想,这样的艺术不受到争议才怪了。再想想,不能引起争议的艺术是不是绝对的好的艺术?有生命力的艺术?翻开艺术史,有那么多的闪着奇异光彩的人物(远的如徐文长,近的如陈子庄等)也是被争议了多少年的,都可以拿来作说场的,算了,这样作就显得在赌气,在做文章了,不太好了。
其实,叫书坛不安静的不仅仅是他的字,还有他的文(观点)。他的文和他的字一样,不那么“规矩本分”,今儿一篇明儿一篇,不断地在书坛上制造“事端”。他总能思他人所不能思,言他人所不能言,总能有许多的新的理论观点从他的善于思辨的头脑里冒出来,并使之成文。其中,发表在《书法研究》上的《书法新古典主义是倒退主义》一文,洋洋洒洒近万言,如巨石击水,在全国书画界引起轩然大波,其评品之文如长江之水一浪接着一浪,至今不息。他有两支笔,一支写“螃蟹体”的书法,笔锋一转,又撰“奇谈怪论”的文章,相辅相成,相映成趣。这在书坛上是不多见的,在我认识的书法家朋友中不出一二。我有时觉得他像毕加索笔下的人物:多角度,鼻子长在额上,眼睛生在后脑,看似奇怪,其实在理。有人说,严学章是一个才子型的书法家,此言不虚。
四
我喜欢严学章的字,也喜欢他的文。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了就读一读。文坛上有人把邓一光比作是“巴顿将军”,是说他的小说语言有一种“霸气”。严学章也是有“霸气”的。文也好字也好,都挺雄性的。他是一个有气概的书法家,骨子里高扬的是一股剽悍的男人味。邪气也是有的,之于他是才情,之于我是佐料。如汤里的鸡精,缺了就淡了。当然,我也喜欢清丽、简远、飘逸的作品,那完全是另外一种阅读感受。
五
我在先前的一篇写他的文章中说过,严学章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床头上贴的是郑板桥的豪言:“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霆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我以为,这,与其说是一个灿烂的诱惑,莫若说是他本能的向往。成名不等于成功,他要走的路还很长。昨天大雪(羊年正月初九),几个朋友想约他到鱼梁洲浪漫一把,他说:“我现在正写字哪!”袁中郎说过这样一段话:“大约趋利者如沙,趋名者如砾;趋性命者如夜光明月,千百人中,仅得一二人,一二人中,仅得一二分而已矣。”严学章视写字为性命,如黄牛正在使力耕作,我等浮泛之人,再去打搅他就不太好了。可少了他,又觉没啥意思。遂作鸟兽散。
羊年正月初十于三半堂
附:文艺界有帮朋友,隔三差五都是要在一起“切磋切磋”。去年秋日的一个午后,阳光很好,“一品楼”上茶香正浓,忽然的严学章就说他要出本文集。叫我写写序。严学章出集子不新鲜,叫我写序就新鲜了。序是名人的专利,是要拿名人的名往瓤子上贴金抹银的。我算什么呢?充其量是文艺的大道边上的一个求艺的“花子”。“花子”无金也无银,一阵惶恐之后,就推了。
没曾想,今年新春之际,爆竹声中,严学章又来电话,说,我不在乎名与不名,我要的就是你的实实在在的几句话。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一个传说,说是郑板桥在成名之后,要接济一个落魄故友,并不给他银子,而是对众人说,他是我的老师。那位故友的画儿,立马价值千金。
这是严学章在抬举我啊。
知非诗诗,未为奇奇。海是无边的,艺术更没有边(贾平凹语)。于是,我就大着胆,说了以上的话。
羊年正月十一于三半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