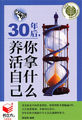竹孝才
竹孝才是镇上中药铺的老药剂。我们村离镇子有二里多地,他和我家邻居黄四儿是“拜把子”兄弟,时常来,所以我认识他。
村里有人小心眼儿,说竹孝才好吃,跟黄四“拜把子”,拜的是黄鳝(黄四会钓鳝)。可我每次看竹孝才从黄四那儿提黄鳝走,两人都要推搡半天,一个把钱,一个不收,最后了竹孝才总要说,兄弟,你再不收,我下回不来了。黄四才收下。
竹孝才高个子,戴眼镜,地包天大撇嘴,离近了说话他好喷唾沫星子。小时候,一次我和黄四的儿子保根在村口皂角树下比尿高,我输了,被竹孝才看到了。竹孝才猴下腰把我屁股蛋子捏捏,又揪揪我脸,说,看你瘦的,两个地方加起来没二两肉,叫你爹弄条黄鳝炖炖参吃,包你赢。他说包你赢时,大嘴一撇像青蛙撒尿样溅我一脸。
竹孝才是来给黄四送蛇药的。黄四夜黑儿里钓黄鳝,好被蛇咬,竹孝才就用百草给他配蛇药,——一种碾碎了的土色的粉子,叫五毒散。奇怪,蛇药也能治蜂子蜇!热天,我、要子、猫老五、保根等一群娃子到田冲里野,在渠沟边的树根上发现一个蜂窝,两个拳头大,细腰的胡蜂密麻麻的。大伙激动的两眼冒火。遂用砖块砸,用棍子戳,结果,除猫老五、保根滑头躲得远外,我们几个都被蜇了,我被蜇了十几口。脸、手、脖子立时就肿起来,发面馍似的,眼都睁不开了。尖锐的疼痛,还有恐惧,我哇哇直哭。要子、会义也哭。保根害怕了,回去喊他爹。黄四快步跑来一看,痛斥道:狗日的胡球闹,那东西也能惹得的?转回去拿来一包药粉子,调鸡蛋清,一点一点给我们抹上。等黄四走了,我问保根,你爹给我抹的啥,保根说,是蛇药。神了,一会儿真不疼了,不到天黑,肿也消了。
不过,我对竹孝才的感觉依然不是很好,觉得他这人日格外。比如在大夏天,他穿打起膝盖的皮靴子,像个日本兵。开始我不知道那叫靴子,我问他:“又没下雨,你为什么要穿深筒皮鞋?”他说:“是靴子,内蒙的皮靴子咧,看,还带拉链儿的,你没见过。”我父亲,黄四,竹孝才一起喝酒,我父亲和黄四都打赤脚,裤腿高挽,竹孝才却要靴子把腿捂得严严的。我替他急,就悄悄蹲他身边把拉链拉开。他大叫:“哎唷,不要拉,不要拉,好臭好臭。”
我父亲说,竹孝才,你黄牛黑卵子的,格外一条筋哪你。
我母亲说,人家竹先生内蒙人,是个“鞑子”嘛。
我们那儿把草原上的人都叫“鞑子”。
后来,我长大一些了,渐渐知道,这个“鞑子”,还是挺不简单的人物哩。他年轻时,曾在武汉的大学里教过书,是五七年,口无遮拦地犯了错误,才下到了我们镇上的供销社,一直在中药铺里抓草药。他说他不是搞医的,是搞中文的,懂点医道是半路货。但镇上传他在治疗蛇伤、阴癣、背疮等方面有独到的手段。我没见他给人治过病。倒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听他讲了一回课。遗憾得很,只讲了一节,就又犯下一个错误。
我们那会儿读书,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先是学工、学农、学军,后又学医。学医时,就让医生或药剂师给我们讲医药常识。不知怎么学校就请到了竹孝才。是下午,上课了,就见他背一个大麻包,打开,全是枝叶干枯的毛根、艾蒿、车前草、晕头花、老鼠藤、蒲公英等等。竹老师是要给我们讲中草药!这些草药田边地头上还长着在,大家都认识,自然很兴奋,都争着抢着回答竹老师的提问,——它们茎叶的模样,花的颜色,还有味道什么的,课堂气氛甚是热烈。可能是竹老师讲高兴了,一高兴,就深入了,——讲到某种药的配制和它的用药方法了。原话已记不太清,大意是:“女人经前下药要猛,经后下药要缓;男人月头下药要重,月尾下药要轻。”三年级小学生,连生理卫生课都没上过,哪里懂“经前”与“经后”?于是,他进一步解释:“‘经’,是指女人的月经,而女人的月经……”课堂一下子安静了,接着,女孩子低头红脸,男孩子尖声嘻笑。等我们的竹老师会过神儿来,早已讲过河了,便撇嘴瞪目,愣那儿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女人有月经。
再上中草药常识课,就换人了。据说,为这,竹孝才住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挨了好一顿批,可把他骇坏了,说随便用一顶“流氓”的帽子给他戴上,都够他“喝一壶”的。他说他怕老账加新罪,会下大狱。还好,批一顿又放还了,仍旧是当他的老药剂。
竹孝才是个讲情讲义的人。七八年平反后,秋天,他还带全家到我们村前的山上看了他的盟兄黄四(黄四已死),流了一把泪,然后就回内蒙去了。他说他不想呆武汉了,老了,该归根了。算算,如果人还健在,该八十多了。
田贵贵
在村里,田贵贵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婆娘一连生七个丫头,因为没见着个带把儿的,还准备继续生下去,生个儿子。要不然,田贵贵说,他死不闭眼。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这么重的负担,搁一般的家儿,早穷得没了裤子穿,但田贵贵会打猎的手艺,还过得不赊不欠,油盐不缺。队上人提起他,个个伸大拇指头。
田贵贵,大人们又唤他田鬼鬼,或鬼鬼。并不是贬义,是讲他白天在山上打狐子、打鹞子、打野鸡,夜黑了就下笼子、布卡子,关黄鼠狼、夹果子狸。成日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虽住一个村子,十天半月也难得打个照面。有时,你明明看他还站在哪儿,一闪身,就鬼一样没影没踪了。他每月向队里交八块钱副业费,队长不管他上工不上工,口粮照分。
田贵贵家打猎是祖传,枪法好,传他能百步穿杨。年轻时当过村里的民兵连长,每年县上集训他都获表彰,屋里奖状贴了一大排。后因拿了训练打靶的子弹去打野猪,犯了纪律,公社武装部就把他的连长给撸了。听村人私底下说,他要是好好搞,是可以转正的,那时(五十年代初)相邻有两个村里的民兵连长,射击水平远不及他,都转成武装干事了。他没有转,还给撸了,可惜得很。
倒是田贵贵对这事看得淡,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不当民兵连长了,反而自由了。就把由他爷传给他爹,他爹又传给他的那支土枪(我们那儿叫“铳”)用麻油擦拭擦拭,干脆以打猎为生了。那些年,鄂西北的山山岭岭,树高林稠,野生动物多,这使他很是大显了几年的好身手。他家住村子最北头,门前一棵老白果树,树枝上就常吊着些兔子,麂子,狗獾子,或狐子,看像活的一样,实际只一张皮,里面灌满谷壳或干草,撑得圆鼓鼓的,等风干了好卖。也有时,他是把兽皮剥开了钉在墙上,黑一块白一块的,晚上了小孩子不敢打他门口走。田贵贵个头不高,细瘦,走路一冲一冲的,有点子气势。偶尔在黄昏的时候看他由田野里归来,腰里扎个篓子,肩上扛杆猎枪,我就很羡慕,觉得他很是威武。
田贵贵比我父亲略大两岁,按说,我应唤他为田伯伯的,可记忆中似乎我从来没叫过。虽然我和他家五丫头同庚,也时常到他家玩,——猎枪,土炸药,关黄鼠狼的匣子,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田贵贵在家时我是不去的。他人寡言,夹生,在他身边会感到空气紧张。尤其是他那双三角眼,小而毒,盯住你就像刀子挖,我就很惧怕。现在回忆起来,我实际连他怎么开枪,怎么捕猎都没亲眼见过。因为他打猎,总要翻过几架山去。即便是在村前屋后,冲田河道里布置笼子和夹子,也是得等到三更天,鬼兮兮的一人去布。鸡叫头遍再一人去取。他从不让任何人跟。别人打猎还有只狗,他连狗也不要。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独往独来的,一个神秘又有点怪异的人物。
田贵贵晚景不好,五十几岁的时候,得了羊角风(医学上叫这为间歇性精神病),一会阴一会阳的,发起来要命。至于病因,村里传有几个版本。说得最多的,是讲他为追一个狐子,追了一天,眼看天色晚了,撵到一个破窑的门口,那狐子突然站住了,回过头,两眼幽幽地看着他。他正纳闷哩,这时又从破窑里窜出几只幼狐,怯怯地拥到了老狐的身下。原来是一母狐子!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母狐竟然转过身子,面向田贵贵把两只前腿跪下了。田贵贵打了一辈子猎,何时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惊愕得合不拢嘴,疑惑这到底是鬼、还是狐精?不知是他的良心发现,还是他害怕了(我想他是害怕了),当下就找了块石头砸了猎枪,回到家,又把夹子和笼子劈掉放灶堂子里烧了。可是,还是出事了,——据他婆娘说,就是从那天起,他的神情开始恍惚,并奇奇怪怪地怕起活物来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包括家养的猪、狗、鸡、猫他都怕,见着了就浑身打颤。就只好整日地藏在屋里头。后来就得了羊角风:扑嗵一声倒在地上,身子僵直,手腿抽筋,口吐白沫。那段时间经常听到他家丫头惊恐地尖叫:“快来人啊,不得了了,快救救我爹呀!”我父亲听到后,说声“不好”,丢下手里的活儿快步地跑过去,抱住头掐他人中,直到他慢慢醒过来。
好象没过多久,田贵贵还是死掉了。他夜里起来上茅厕,茅厕上栖落了一只乌鸦,好不好的呱地一声叫,他本就怕见活物,又是深夜,又是乌鸦,结果病发了,就倒进自家的大粪池里淹死了。村人迷信,讲是他杀生太多,那乌鸦就是阴曹里派来收他魂魄的。顺便说一句,田贵贵死的那年,他婆娘还真是拼老命给他生了个小八子儿,可仍然是个丫头,不知田贵贵死时是闭眼了还是没闭眼。
冯民生
冯民生人唤冯叹气。因为他跟人说话说不到两句就叹气,挖地挖不到两锨也叹气。搞不清原由的人还以为他有天大的不幸。实际没有。用村里的土话说,他那是在“显摆”哩。冯民生原是城里人,解放初读过一些书,没成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带一家五口随城镇居民大下放来到了我们村。要说不幸,大概,这就是他最大的不幸。
其实,他在城里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在牛行里当过牛经纪,粮行里干过账房先生,后来越混越不济,就在街头摆地摊钉皮鞋、补胎、修自行车,逢年节和他婆娘(他婆娘叫戚安云,我唤她安云婶子)一起挑米花机到乡下给人炸米花儿,一角钱一炮。如是而已。可冯民生毕竟是城里人嘛,生活在了农村就有了某种优越感,某种委屈。这种优越感加上委屈,就表现为叹气了。有时大伙烦了,就说,冯叹气你死娘老子了吗,一天到晚脸苦气哀的有个什么劲?
冯民生个小,人瘦,蓄大背头,平常喜欢在左上衣口袋里挂支钢笔,像个干部。虽然已落草乡里,但城里人的一些作派还依旧坚持着,比如坐茶馆。村里没有茶馆,集镇上有,三五天内他就必要去坐一次。不坐不行,他说,不坐身上的蚂蚁子就咬骨头了。“喝一大碗的茶,听听二爷的书(吴店镇有名的说书人),心里才舒坦”再比如看戏,隔段时间就要从鸡窝里掏仨俩鸡蛋,换一毛钱(戏票一毛一张),骑着他那辆除了铃子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哐当哐当奔五十几里进城里人民剧院儿看一场。那时的农村,一年上头难得有戏看,偶然放放电影,也稀罕得很。冯民生就受不了,说宁可三天不吃饭,也要看看崔兰田。崔兰田是谁?天晓得!“连崔兰田也不知道?哎呀呀这……”这一来,冯民生就更视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了,时常听到他大声吼他婆娘安云婶子:文化饥了,也要吃饭懂不懂?安云婶子回他,我懂,懂你个王八日的钱在烧包了!不过,我们小娃子还是觉得他是有点儿文化的,不是指他当过账房先生、喝茶、懂戏文,而是说他会用一个词:“悲哀”。我们那儿人好把一切的不如意都叫“遭孽”,而他说“悲哀”,就觉得很文化、很洋气。他说在村里生活没戏看,“悲哀”。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曾一度流传很广:“天一撒黑儿就上床,四顾麻麻(茫茫)闷得慌;没有戏看眼饿死,一宿干靠到天亮。”后来不知是谁使坏,把后一句改成“一宿干靠(搞)安婆娘”。为这,安云婶子跟他打了一架。“文革”开始时,还把他剃了阴阳头,弄到台上当流氓批斗了好几场。当然,留恋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发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满,也是主要的两条罪状。批得他唉——唉——唉——,叹气连连,直摆脑壳。
好在,冯民生出身好,村社两级的“小将”们,对他的思想行状只是停留在批一批上,并未划他坏分子,要不然,他后面的日子怕是不好熬过。
那时候,我和冯民生接触不多,多的是冯民生的儿子冯车(念居音)。冯民生老了,我小了,和他搭不上腔。冯车比他老子强,长得黑而粗壮,快成一个地道的农民了。可能是潜移默化,也或是遗传,冯车也爱戏。只不过,时代变了,冯车看的是样板戏,从这个村撵到那个村,同一出戏能看十几二十场,不嫌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将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戏文从头到尾背下来,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天生一个公鸭嗓子,逢到唱词,高腔处吼不出来,每每让他沮丧之极。冯车极看不上他老子,说,要不是冯民生(对他爹一直是直呼其名),老子嗓子咋会这样?我恍然大悟:冯民生迷戏,可从没听他哼过唱过,竟没在意他是个老公鸭嗓子。
七八年我高考失利,先是在镇上文化馆混饭吃,两年后又阴差阳错地进了县工艺美术厂。一日下班闲遛,走到县人民剧院旁,忽闻身后一声喊,喊的居然是我乳名三娃子。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冯民生吗?天天各忙各的,有几年没见了。这期间,听说过他们全家也已回城了。他干的还是老本行,在街头钉鞋、补胎、修自行车。人依然是瘦,依然蓄大背头,可明显腰猴多了,头发也白透了。我说,冯伯伯现今可好还?他说哪里好来?我说你倒底是回城里了,想看戏看戏,想坐茶馆坐茶馆,还有么事不好嘛!寒暄一阵,随即,我俩踅进一爿茶室里聊起来。聊得最多的,自然还是他在我们村时的那些人,那些事儿。“悲哀,悲哀。”末了了,他带总结似地说,这人哪,有牙时没锅盔,有锅盔时又没牙。我道这作何解?他说:“我现在有茶馆坐不假,可只能是坐坐呢,坐个味道,不能喝茶了,胃烂了,在乡里十几年把胃搞烂了,医生不让喝,再喝要动刀子割咧,你看看这。”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手里端着的杯子里是白开水。说着话,就见他瞥一眼斜对个儿的人民剧院,又摆摆脑壳叹起气来:“唉,乡里没意思,城里也没意思,哪儿都没意思。戏算没得看了,剧院儿里开舞场,尽跳迪士科,好好的人都跳成疯子了。崔兰田的豫梆儿没人唱了,多好的戏呀那!
伍九爷
伍九爷是我们晚辈人对他的称呼,和他年龄相近的人,或村干部都尊唤他老连长,老领导。伍九爷在队上不是个啥,但他为人正直、厚道,又热心快肠,乐于助人,村里无论大小事,都少不了他来参与张罗。像红白喜,兄弟分家之类,尤其是民事纠纷,村长书记拿不下的,找他,一准圆满解决。在村人的心目中,伍九爷是不是书记的书记。
村里人对伍九爷的敬重,除开他辈份高,德行好以外,还和他不平凡的经历有关。解放前他家里穷,十三岁跟远房一个叔叔出门跑江湖,叔叔会些拳脚,舞一把关公刀,伍九爷就随他学翻“空跟头”,“练场子”,东南西北地流浪,实际和讨饭无异。后来遇到队伍,就去当兵了。竟然,瞎猫撞了个死老鼠,撞到了林彪(那时叫林副主席)的部队里,真刀真枪干了不少仗,还在东北打过著名的“四平”战役,官至连长。也是该他不发达,四九年,解放四川达县的时候,无奈何看上了地主家的一位小姐,死活都要和她结婚,上级不批,就脱下军装丢下枪,偷偷跑回来了。干部身份,党员,自然也就掉了。这位小姐姓沈,名玉儿,伍九爷一直没改口,早年唤她玉儿,老了还是唤她玉儿。我们小孩子都唤她九玉奶奶。
九玉奶奶比伍九爷小十来岁,看着比我母亲年轻。人生得白白净净的,一口斯斯文文的四川蛮子话,软软的很好听。据说她嫁给伍九爷的时候,还是个没毕业的中学生,是伍九爷给学校作英雄报告,认识了。那时候学生要求进步,向往英雄,讲究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九玉奶奶就选择了伍九爷,选择了她心中的英雄。
“为了个地主小姐擅自脱离部队,值不值?要不还不当团长了?团长就和县长一样大了。”茶余饭后,大人们经常这样议论他,替他惋惜不已。
似乎没听到伍九爷说过后悔的话。“文革”时,九玉奶奶划成“四类分子”,造反派几次要揪她批斗游街,几次被伍九爷拿了镢头挡在院外。兴许是伍九爷平素威望高,也或是听说他练过武功,“会两手”,造反派们多少有些怵他,闹了一阵子就收场了。因为伍九爷,九玉奶奶硬是躲过了“文革”那一关。
要说伍九爷“会两手”,也只是老辈人之间的传闻,他到底有多深的武功,没谁见过。伍九爷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言语短,不张扬。夏秋的打谷场上,工间歇辰时,常有年轻人麻缠他,叫他“练”一套,他一般都是摇脑袋以笑作答。实在磨不过时,就说,你们来压我的手腕子吧:他把左(或右)胳膊肘单立在膝盖上,一用力,臂上的肉疙瘩就鼓起来,虽壮年小伙两只手也压不下他。伍九爷家院儿里倒是有一盘练功用的石锁,一根一握粗,一人多高的檀木棍,磨得光溜溜的,但那是他二子虎头平时耍的。提起儿子虎头,伍九爷也是摇脑袋,说,这娃子吃不得苦,只会些花拳绣腿。他故去的叔爷,那才叫真功夫哩!
我离开村子的时候,伍九爷已是近七十的人了,身板还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了。他家住在村头的路边口,印象深的是,冬日农闲,他好穿着黑色的棉袄,去村后队里仓库的檐下和老人们一起晒太阳,“摆龙门阵”,一摆一个上午。九玉奶奶唤他吃饭的嗓门特别亮:“憝老伍,吃饭啦!”软甜的调子像唱歌,几乎半条庄子都能听到。“憝”,在这儿是爱称。
大至是八十年代初,听进城来的村人说,伍九爷他们全家都搬回九玉奶奶的老家四川达县县城去了。原来,九玉奶奶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主,而是达县最大的一户资本家。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一清查,有半条街都是沈家的房产,可她的两个哥哥民国时就去了国外,生死不明;父亲母亲都去世了,沈玉儿就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故土难离呀,开始伍九爷咋也不肯走,后来还是走了。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选择,鱼与熊掌,伍九爷选择的是九玉奶奶。
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