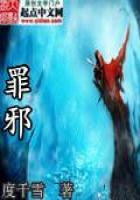(《雍也第六》)在这里,同样是在粟的问题上,孔子对冉子和原思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个想多拿点,孔子不许,还提出了批评;一个不想要,孔子反而鼓励安慰他。原来,对于财物的用度,孔子有一条标准,叫做“周急不继富”。日子能过得下去,更多的财物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日子过不下去时,哪怕是一点点的东西,也显得多么重要。这一条“周急不继富”的财物用度标准,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好参考作用。在物质尚不十分充裕的情况下,如何使用财物,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通常说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少做锦上添花的事情,钢要用在刀刃上,也是这个意思。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述而第七》)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
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第九》)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第三》)由这几段话可以看出孔子是提倡节俭精神的。但是,孔子的节俭并不是吝啬鬼或守财奴的作派。他的节俭是以合乎礼、合乎社会道德为前提的。如奢导致了不孙,因为铺张、排场,让人觉得很不谦逊,甚至有点不可一世的派头,这是人们反对的,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而俭呢,而让人觉得很固陋,一点也不潇洒气派,甚至可能让人瞧不起,但它并没有违反社会的道德。通过权衡利弊,孔子选择了俭而固,舍弃了奢而不孙。
当礼与俭发生冲突时,孔子也不是死守住教条主义,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礼的理论。比如戴帽子吧,以往的麻冕是合乎礼制的,但现在大家都戴丝质的,比麻的便宜了许多,那么就遵循大家的意愿吧。因为无论是麻的还是纯的,只要都是帽子,也还是合乎礼的,所以也纯,从众吧。不过,没有花钱的一些礼节,还是庄重严肃好。
对于某些必要的用度,还是要坚持下来,尽管形式服从内容,但绝对没有脱离形式而孤立存在的内容。如告朔的仪式,一定要有羊,如果连羊也不要了,那么就无告朔可言了。现在我们仪式尽管逐步简单化了,但是一些“意思意思”的做法还是要的。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述而第七》)禹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完美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理由是禹在食、穿、住三个方面的态度:自己吃的差些,但不能对祭祀马虎应付,平时闲居可以穿得朴素些,但行礼时却要大方美观,自己住的地方可以小一点,但为百姓兴修水利却要尽心尽力。
(三)多寡有度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对财物占有的欲望更甚,因为财物确实是人得到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但是,人的幸福并不等同于财物。那么财物的多少到底有没有一个限度?这个问题肯定是没法回答的。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第一》)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十三》)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十三》)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者,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十五》)孔子所推崇的君子应当是谋道不谋食者,然而也不完全否定衣食住行之类人之所必需,尽管可以君子食不求饱,但至少是可以有的食,足以维持生命;尽管可以居不求安,但肯定要有个住所,权且遮风挡雨。虽然可以追求谋道不谋食的境界,然而必不可少的条件还是庶与富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一谈起义利观的时候,通常是肯定前者而否定了后者,这不免让人看出“吃饱了撑着”、“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假道学的嘴脸。
(四)贫穷何处如前所说,孔子在讨论义利观时,是在讨论一种关系,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不是把义与利生生地割裂开来。如果说孔子有所取舍的话,那也只是各自对立面之间的取舍,如义与不义之间,孔子显然是取义而舍不义的,他并没有说我饿着肚皮我痛并快乐着,至少也要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然后才“乐亦在其中矣”。
(五)富而好礼
“君子不以绀诹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诊浠裕,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霓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抉。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齐,必有明衣。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孔子并不反对致富,而是思考富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富而好礼的对立面是为富不仁,因为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内心不仁之人,其表现出来的肯定是无礼;富而好礼是一种品位,一种境界,一种修为,一种维护自尊的选择。许多时候人们会产生仇富心理,其实并不是仇视富人的财富,而是仇视拥有财富之后富人的作派。贫富分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仁义的丢失或消亡。
商儒子贡
儒商现在很流行。一个人如果能得到儒商的称号,当然是很荣耀的。所谓儒商,本质上还是商人,儒只是这种商人的一方面的特点,即比较有文化素养,看上去相当儒雅。但是,从子贡的实际情况看,我以为称他为商儒可能更合适些。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儒商在本质上还是商,而商儒就不同了;商儒在本质上还是儒,只是这种儒有一个显明的特点就是能经商,或者说经商的意识比较强烈,经营的本领特别高强。从《论语》或《史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子贡以言语著称,他的作为主要是外交方面的,而且在传播孔子的思想和学术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他完全是一个儒。但是,在从事儒业的同时,子贡还特别能经商。子贡的经营显然不完全是为了赚钱,更可能是为政治、思想、学术创造条件,打下经济基础。据司马迁的说法,孔子周游列国,主要经济赞助来源于子贡,而在孔子死后,竭尽全力宣推孔子的也是子贡。如果这些说法成立,更可以说明,子贡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他的赚钱只是手段,即商是手段,儒才是目的。所以,我说,与其说子贡是儒商,还不如说他是商儒。
下面我就来看看子贡在商业活动以及对待财富方面的一些态度吧。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这是子贡与孔子的一次关于贫富之人处世态度的讨论。
子贡显然已经是富者了。但是,任何的富者都应该有一个从贫到富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从一出生就是富者(如继承而来的),这在真正意义上是不能算富者的。至少,他不可能真正享受到做为富者的乐趣,因为他未曾经历过贫困,不知道贫与富的的差别,无比较则不能判断,于是就不能深切理解富的意义。子贡大约不是生来就富的,而是经过奋斗由贫而富的,因此,他有资格来论贫富的处世态度的。
子贡是靠自己奋斗而致富的。这在《论语》中有清楚记载的。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与颜回,一个贫得不行,吃不好,住不好,而且不幸短命死矣,以至让孔老师天天为他哭哭啼啼。戏剧曲牌里有个《泣颜回》大约就是来源于此的吧。而子贡却是七十子之中最富有的。
子贡是怎么富起来的呢?第一,不受命。不受命有几种理解。有说是不相信那个时候社会认可的天命,也就是按现在人的说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说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人,不受条条框框约束的,敢于冒险,敢于创新,勇于进取。第二,货殖。就是搞贸易,通过易货而使钱增多起来,殖,大钱生小钱吧。第三,商业知识相当扎实,市场预测得很准,几乎是百发百中。如果那时候有股市,他肯定不是股市黑嘴,而是高级操盘手。至少有这么些因素,加上当时的经济环境,才成就了他不受孔子批评的富贵。
子贡向孔子提出问题:第一,人穷志不短。即使贫穷,但不向富贵谄媚,不低声下气,屈膝求哀。第二,一旦富起来了,没有骄横,不可一世,也没欺贫凌弱。能做到这样,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