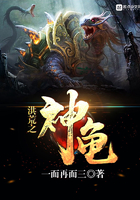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一部由统一到分裂的动乱的历史。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司马氏篡魏自立,统一全国,史称西晋。仅维持三十余年,北方少数民族相继问鼎中原,十六国连年战乱,进入分裂时代。直到五世纪初,才为北魏统一,后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是为北朝。西晋被逐南迁,偏安江左,史称东晋。五世纪初,为宋、齐、梁、陈所更替,是为南朝。
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然而又是中国文艺觉醒的年代,是文艺复兴的年代。这个时期,两汉的儒家思想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玄学和域外传入的佛教思想。
第一,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艺术的变化。原先的儒家思想出现了危机,代之而起的是融儒、释、道三为一体的新型哲学——玄学;外来佛教适时地填补了信仰的真空。思想活跃、主体意识觉醒、重视个人价值,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佛教的引入,出现了大量的宣传佛经教义的石窟壁画、佛教塔寺;玄学哲学的拓展,给中国人的艺术思维、美学理念,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诸如:
贵无。此种哲学认为,“无”为本,“有”为末。文艺也是“虚无”的一种表现,“大音希声”、“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方为上乘。贵无,使中国人确立了平淡自然的审美观。
强调主体:自娱与畅神。主张艺术不应是政治的附庸,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这突出反映在山水画的创作上。“学不为人,自娱而已”,山水“畅神而已”,成了当时艺术家的信条。
表现主体:人物品藻——风骨、气韵。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社会行为,即对有声誉地位的人,社会对他的人品、人格会有一个总体评价,名之曰:人物品藻。这个总体评价极富审美色彩,即通过对该人的外在特征——容貌、仪表、风度、举止、穿着、谈吐——的观察,对该人做出总体评价。这种对人的评价,随之运用到了艺术方面,如“风骨”,原指人的骨相,用来指艺术,往往指艺术的主干、笔法等。又如“气韵”,原指人的气质、风度,用在艺术上,就指艺术的活力与律动感等。
第二,文化地域格局的变化所引起的艺术变化。在此之前,中国以北方的中原文化为主导,形成质朴、刚健的特色;南渡以后,本来还想保持中原文化的特色,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江南的秀美自然和优裕物质条件所改造,由此形成了艺术的阴柔化、轻淡化,为以后中国南北艺术流派之别,形成了源头。
第三,庄园经济和隐逸之风的结合,带来了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和山水画的产生。庄园经济形成于汉末,在战乱年代,它集经济、军事于一体;东晋以后,生活安定,不再具有军事功能,而只成为敛财的工具。在开发江南山泽的过程中,士大夫们发现了自然美的独特魅力,他们似乎可以从“利”字上离开,而单独关注山水本身的情感价值,并由此出现了山水诗、田园诗。
隐逸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它似乎是调节士大夫与统治集团关系的一种手段。隐逸的士大夫,不在朝,而在野。在野,便有条件从事文化活动,或作诗,或作画,或游之于山林,皆听其便。文学与艺术画作,便成了他们的精神产品。
(第一节) 石窟壁画
这一时期政治混乱,儒学衰落,励精图治的统治者大都尚节崇俭而少有大兴绘饰之举,更多的统治者则把外来的佛教当作辅政的有力工具。佛教虽然在初创阶段曾经反对偶像崇拜,但为了传播教义和迎合统治者的需要,逐渐把造像当成了重要的宗教活动,故有像教之称。反映在壁画艺术上,政教壁画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创作,佛教界却一跃成为最大的绘画消费者。大量着名壁画出现在佛教寺院、塔刹和石窟之中,如顾恺之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瓦官寺所画维摩诘像、张僧繇在江陵(今在湖北省)天皇寺所画卢舍那佛像等。这些画迹早已随同建筑物荡然无存,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较为僻远的石窟壁画。
石窟是佛教寺院的一种形式,多依山崖开凿,洞前建木构或仿木构建筑,有的依附于寺院,有的由多个洞窟组成完整的寺院形式,故也称石窟寺。中国开凿石窟寺始于4世纪以前,盛行于5-8世纪,后来开新窟渐少,但重新装饰前代旧窟的做法比较盛行。我国现存石窟主要有:新疆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甘肃敦煌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有别,各石窟群的装饰手法不尽相同,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以施彩石雕为主;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石质疏松,不宜雕像,以壁画和彩色泥塑为主。
这里,我们着重介绍一下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于今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敦煌是汉武帝所置河西四郡中最西的一个,是河西走廊四端戈壁上的一处绿洲,是关中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是军事、商业、文化来往的重要补给站,也是佛教东传路上的重要环节。其居民华戎交错,既有中原移民,也有西域商人。“敦煌”一名可能来自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东汉史学家应劭则释之为“敦,大也;煌,盛也”,既符合敦煌在汉朝统治下的繁荣状况,也表明了这个军事、行政和经济据点在汉朝统治者心中的分量。公元2年,敦煌已有一万多户,三万多人口,经济、文化都比较兴盛,东汉书法家张芝、索靖都是敦煌人,以草书知名,在书史上引导了书写新风,表明敦煌地方文化已深深地融入了中原主流文化。西晋时期,敦煌的佛教势力已成气候。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敦煌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用心经营,发展更快。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沙门乐洨云游至此,似觉鸣沙山在一片金光中化出千佛之状,遂决定在此定居修行。从此,洞窟开凿和寺院兴建日盛,经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共十一个朝代(中间还经历过吐蕃等地方政权统治),一千余年,开凿塑绘不绝。现编号洞窟有492个,窟内壁画总面积四万五千余平方米。古代敦煌郡辖境内,还有几处石窟,包括今敦煌市的西千佛洞、安西县的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等,与莫高窟属同一系统,合称为敦煌石窟。
莫高窟有36个洞窟里保存有属于十六国、北魏、西魏和北周时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及窟顶、塔柱各处,除掉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有情节性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人、药叉等形象。情节性画幅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北魏254窟“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257窟“鹿王本生”、西魏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北周290窟“佛传故事”、428窟“须达挐太子本生”等,构思布局都极具匠心。
敦煌文化虽然吸收了“五胡”和西域、中亚的文化,但还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反映在绘画艺术上,敦煌早期壁画吸收外来影响后消化程度比克孜尔石窟要高,佛教艺术的民族化在这里迈开了最初的脚步。
(第二节) 卷轴画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卷轴画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许多方面出现了质的飞跃。
中国传统绘画按照媒介区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绘于地面建筑和地下墓室墙面上的壁画,一种是绘于纸、绢、布等可移动材料上的卷轴画。卷轴画采用软质底子,可以像简册和书卷那样卷起来。后来为了便于保护和欣赏,吸取书籍装帧技术的特点,逐渐发展出了别具一格的装裱工艺,在画的两端加上圆柱状的轴,观看时便于持握和张挂,收藏时可以卷成圆轴,故称卷轴画。从书卷情况来看,装裱工艺是在南北朝时基本形成的。现存南北朝画卷实物虽然都是后世的摹本,但卷轴画在这一时期形成是无疑义的。
卷轴画形成的条件,一是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了上层社会对绘画的消费欲望,并且要求在传统的壁画、漆绘和其它装饰绘画之外有更丰富的形式;二是绘画功能和欣赏风气的变异,形成了书斋案头文化。在两晋以前,绘画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用性的宣传教化,欣赏绘画一般是在公共场所(宫殿、衙署、祠宇、寺庙)进行的、带有社交色彩的活动;从两晋开始,又出现了作为纯艺术、仅供欣赏的绘画作品,欣赏绘画开始进入个人精神活动领域,可以在书斋案头细细把玩。在这方面,书法的发展对绘画具有强烈的先导作用。东晋时期,在小幅纸(当时能抄制出的纸张最大高度不过24.5厘米)上作尺牍、书法、美文,已经成为士族盛行的风气。与书法有着先天亲缘关系的绘画自然会受到影响,案头欣赏用的手卷、卷轴便应运而生。
(第三节) 绘画分科与专业画家的出现
随着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对精神生活越来越高的追求、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各个文化种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绘画题材和种类在原有的基础上日益扩大,并开始向分科发展。
人物画方面,既有起“鉴戒”作用的两汉以来的传统题材,也开始取材于文学作品,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面貌。人物描写能力在这一时期有显着提高,但出色的画家并不满足于表面相似,还注重精神内在的表现,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就特别注重揭示对象的精神状态和表现对象的特定性格。他画谢鲲,置人物于丘壑之中,形象地表达出谢鲲的林泉之志;画裴楷,颊上加三毫,顿觉神采殊胜,也更有气势。
魏晋南北朝是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萌芽时期。从文献着录中了解到有单纯描绘的花鸟作品和专工的画家,但至今尚无资料证实已形成独立的花鸟画,花鸟画当时只处于孕育阶段,发展要晚于山水画。有关山水画的着录、着述则较多,山水画的发展和当时玄学思想的盛行、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有关。东晋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刘宋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记录了他们对表现自然山水的看法,这些文字是探讨山水画起源的重要依据,然而还见不到独立的山水画作品,若干有参考价值的绘画,山水多作人物的背景和环境的衬托,较为古拙。如唐代张彦远所说:“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一卷《论画山水树石》)在顾恺之《洛神赋图》中,确实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山头的形状像女子用的角梳之类,人与自然景物的比例不真实,树、石像道具那样生硬地安排在人身边,树木则像银杏叶子,下部叶柄就算树干,上部树冠张开,如人伸臂而五指分开。山水画的真正出现是在隋唐之时。
在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批着名画家出现在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