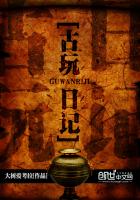白炎将叶浮清再次抱出来时,脑海中仍就回放着那老伯沉重的话语,
“公子,这位姑娘伤的太重,我也只能将她简单处理一下,去寻寻那医之圣手言老吧,或许还有救。”
“多谢老伯……”
“快去吧,这姑娘受了这么重的伤,眼睛醒来想必已经看不见了,她想要活着的意志力很强,公子,抓些吧……”
“多谢,多谢,多谢老伯……”于是,他便只能看到她的白公子抱着不知何时会死去,气息微弱的她,走过许多地方,去寻找那极有可能找不到的人,于是每每有传言说言老在的地方,他们都能看到一位白衣公子怀抱着一位女子,到处询问着那言老的下落,梦境中的那个人低声下气的求着那一个个过路人,寻求他们告知言老的下落,世间人情冷暖,也在此时被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何时这般落魄过……
场面一转,回到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那人一脸灰尘手握着那九死一生带回来的火山草,掌心已经被灼烧,满是水泡,那人既也不知疼痛,将火山草递给言老,
“我带回来了,带回来了,可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那眼中的急切和期盼,看的不禁言老也有些动容,接过那混着他血的火山草,沉声道:
“我随后便将这草入药,只是这草药烈性很强,加之她之前全身经脉尽断,纵然接好,也伤了根本,药入体之后,需要你用自身武功替她化解体内烈性,好将药迅速吸收,换个说法,这便等同于要将你的气息分她一半,只是这代价……”
“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言老也不再多说,叹了一口气,转过身,向后走去,
“既如此,你便去梳洗梳洗,这药做成还需一些时间,也将手上的伤包扎包扎,我想她也不愿看见你这般模样吧……”
后来,后来,她看到白炎的头发在为她化解草药的烈性时,一点点的从发根白到了发尾,俊朗的容颜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眼角已经有了细纹,顷刻间,竟一下老了十几岁,可是那人却仍旧没有停下来,就算口吐鲜血都未曾停下半分,那隔在她后背的手掌也在此刻再次将伤口睁开,血一点点的流下,侵入她的衣裳中,此刻的叶浮清猛的捂住自己的嘴,想要过去,将白炎拉开,自己的身体却穿透了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人的头发一点点白完,容颜也一点点的衰老,
“白炎,白炎,白炎……”可是就算如此,她活着的时间也不会多到哪里去,甚至是就算活了过来也是在挣扎着,煎熬着,可是那人从未放弃过她,从未放弃过,原来在这世间,也有这样一个人从来都不想放弃过她,可是,白炎,若是我这样,不幸要你随我一同坠落这深渊之中,我宁愿我来承受,替你扫平所有障碍,我曾想过要亲眼看着你剑指天下,大权在握,却不曾竟这般苦楚,竟连再看你一眼都已成奢侈,双手鲜血又怎样?毁家毁国又怎样?听天由命,这都是假话,我叶浮清今日偏偏要逆天而行……梦中的一切都那么真实,那心口处传来的刺骨疼痛都清楚的在提醒着她这一切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耳畔传来谁的急切呼唤声,
“清儿,清儿……”是谁在唤她,是谁在如此急切的唤着她,梦中深处顿时射来一阵阵光芒,刺眼的紧,叶浮清猛然一个激灵从床上做起,努力的想要看清楚眼前的场景,却终究眼前一片黑暗,
“白炎,白炎……”
“我在……”
“白炎,可是天黑了?”气氛一下沉寂下来,白炎定定的看着叶浮清那双无神的双眼,说不出的心疼,这还是自她醒来那么长时间,第一次提及着自己的眼睛,
“清儿……”低声唤道,也将叶浮清从梦中醒来的恍惚惊醒了些,自知自己触及了那令白炎有些为难的话,叶浮清低头,也在顷刻间想起那梦中的一个个画面,猛的拉过白炎的手,激动起来,
“白炎,白炎,你在哪?你在哪?”白炎看着突然激动起来的叶浮清,眼中尽是担忧,拉过叶浮清的手,摸着自己的脸,
“我在这里,在这里,你可是睡傻了?唉,日后定不会让你贪睡片刻了……”
“白炎,你在?”
“嗯,我在……”话落,叶浮清一把抱住白炎,哽咽道:
“怎么这么傻?你这样,以后我若是真的不在了,你要怎么办?白炎,白炎,我看不到你了,看不到你了,白炎,怎么办?我再也看不到你了……”一声声的哽咽和无助,无一不在刺激着白炎的心头,那曾经被他放在心尖上保护了那么久的人,怎么就才分开一段时间,就被人毁成了这样,偏偏那人还是他的父亲,他的叶姑娘啊,他心尖的人儿,轻轻的拍着叶浮清的背,安抚着,
“无事,无事,我日日夜夜都守着你,都在你身旁,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了,你想去那里,我便同你去,再也没有人可打扰我们了……”话语间也尽是哽咽,
“白炎,那日在大殿之中,我以为我再也等不到你了,他们都在叫我走,说坚持不住了,就走吧,可是,白炎,我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在等你,我知你会来,我知道,我有感觉的……”
“傻瓜……”
“真好,白炎,我终究是等到你了,你不要再丢我一个人了好不好?我一个人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我害怕,若是,若是,你早日来,便不会是我一个人了……”
“再不会有下次,再不会了……”
“白炎……”
“在呢……”一瞬间,那道心中的防线在顷刻间全部崩塌,自那日醒来,这么久的时间里,叶浮清从未提到过那日的种种,经脉尽断的疼痛,自毁双眼时的无助和害怕,独自一人面对周遭的一切时,那冷静面孔下逐渐崩溃的心,她都独自一人在心里压抑着,白炎也不敢再去触碰那人心中的阴影,而今,叶浮清一觉醒来,梦中的种种清晰可见,也清楚的看到白炎的牺牲,一字一句戳中白炎的心,也将自己的伪装全部撕开,眼眶中的泪顺着眼角而下,为叶浮清留着,也仅为他的叶姑娘,这一刻,曾经在人前运筹帷幄,手握大权,于阴谋诡计中步步惊心,战场之上,冷漠无情,手腕狠辣的两人,竟在这一刻,这个房间里,心心相惜,哽咽无悔……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我在,我在,我在呢……”
“嗯……”
良久之后,叶浮清躺在白炎的怀中,睁着那无神的双眼,眨啊眨啊,似是哭累了,竟慢慢的闭上了眼睛,沉沉睡去,看此,白炎抬起袖子,轻轻的拭去自己眼角的泪痕,纤细的手指轻轻的抚上叶浮清的眼睛,犹如在抚摸着这世间他最为珍贵的东西,眼眸中的怜惜和深情深的让人心惊,那一下看去十几岁的容颜,纵使已不复往昔,却让他平添了一股成熟男人的韵味,一举一动之间皆是稳重威严,那于王者之间的气质也再掩盖不住,于雄狮立于山间之中的傲然也展现的淋漓尽致,或许,这就是白炎,真正的白炎,那历经岁月沉淀后,即将傲视天地间的帝王,却在此时此刻,将毕生柔情和整颗心都给了他怀中的女子,
“此间,我的叶姑娘在怀中,心尖朱砂,吾之血肉,不割不舍,你生吾生,你亡吾随,天地,独你一人,不负。”低沉的嗓音,说着这世间最美的情话,最重的誓言,天地万物之间,除却他的叶姑娘,再无一人,可进他眼中,此情,不负天地,不负他的叶姑娘……
………………
南洲国丧,大事之中,国丧百日,南洲子嗣凋零,朝堂摇摇欲坠,除西江态度仍旧未曾明了过外,余下两国与外族都已虎视眈眈,而这想要吞并南洲的野心也已经再未曾隐藏,东疆和天启两国,于南洲平启之年,御德皇后头七之后,集结大军于边疆,随时候命,只要自家帝王一声令下,随即攻入南洲,而东疆四爷自那日回国之后,接到朝阳郡主逝世的消息之后便一直于醉生梦死中,东疆皇似乎已经打定注意要将这帝位传于东四爷,纵是打了败仗,却仍旧将四爷封为将军,带领大兵前往边疆,而作为肥肉的南洲却一直未曾有任何动作,也未曾撤离边疆百姓,就那样自顾自的过着一天是一天,也不管大军已兵临城下……
林城边疆同叶浮清那时在一般,城墙之上,黑色的玄旗插在城头之上,随风而过,被风吹的“刷刷”作响,站在城墙之上朝远处望去,是一望无际的山头,四周围山而绕,前方的那片土地中,曾死去了无数的英勇将士,埋葬了多少英魂,那边一座青山,高高的矗立在两座小山中间,偶尔有鸟群从那座山中的树林中跃起,朝远方而去,那里便是埋葬了那代表着四国盟誓的血盟碑,那里是四国先祖的见证,是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和平的记载,历经了多少风吹雨打和沧海桑田,仍旧一直那样矗立在那里,从未曾变过,而如今这些人却要在那血盟碑下,那先祖所立的盟约之下,展开一场大战,生死决斗的大战,一场会死去多少无辜人的战争,没有人再去理会那血盟碑制约的存在,楚王和莫离两人负手站在城墙之上,心中隐有淡淡的悲伤,而更多的却是悲凉,不久之后,这里,将会再次展开一场战争,而他们身后的那些百姓也即将被无辜连累,
“那时她从这里匆匆赶到于城时,她手下的副将在烟霞谷中葬身,带去的将士皆在谷中全军覆没,无一生还,那个时候她曾告诉我说,若有一日,定要东疆为她死去的副将和将士报仇,而如今这南洲再也没有朝阳郡主这个人了……”是啊,再也没有了,只要有感情的人便都爱回忆,也都爱惦念过去,而他一身未曾婚配,没有子嗣,潇洒随性,却又不是那种说放便放的人儿,莫离将军垂眸不语,那银色面具下的脸看不出丝毫情绪,
“如今,就是连她母后也走了,莫离,清儿走时要你重新换个名字生活下去,莫离将军接连让东疆损失了两位将军,若是以你的人头作为悬赏,可以鼓舞士气,也会让你陷入不必要的危险之中,而眼下南洲已经不能再有大将伤亡了,便换个名字重新来过吧,这面具……”顿了顿,抬眼看向远处,目光顿时变得悠远而又无神,“便也拿掉吧,方便你以后的生活……”
“王爷在说什么?我莫离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里,离开南洲,我既是南洲的将军,便有着作为将军的责任,我是不会离开南洲的,现下南洲的问题和隐患,莫离都明白,可是我绝不会丢下自己身后的百姓,而去独自逃生,王爷,你忘了吗?这城墙之后,也有我们的亲人和想要守护的东西……”言辞恳切,亦有些激烈,可句句在理,那话中也在诉说着她作为一位将军又怎能丢下自己的士兵独自逃生的心理,是的,那人手下的将士从来都不会是懦夫的,楚王有些惊讶的扭头看着莫离,顿时觉得在这一刻眼前的这位女子从来不比任何人差,片刻的沉寂之后,楚王从袖子中拿出一块黑色的令牌,那令牌上刻着一个仰天咆哮的老虎,栩栩如生,将那令牌递到莫离的手中,低声道:
“这是清儿生前交给承远的任务,便是为南洲建造一支骑队,作为这大军之后的一个后盾,而承远也不负清儿,如今,承远不知去向,清儿离世,这便交于你,好好替她守着……”话落,莫离低头接过那如使命一般沉重的令牌,心情也越发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