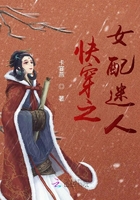那些虚无缥缈的过往也在这时随着一个人的死去而死去,说什么回忆,说什么过往,说什么佳话与功绩,都已经枉然,在这里,在这满是鲜血的皇宫里,他从此便是一个人,一个人肩负这万里山河,守护着身后的万千百姓,直至死亡,直至沉睡……
南皇站在那陵墓之前,不言不语,看着他们就那样将那人随同她的棺椁一点点葬入土中,再不见踪影,时间一点点流逝,那人的一丝一毫气息也再寻不见,一切就绪之后,转身离去,身后浩浩荡荡的跟随了许多人,任谁都未曾看见那位从来都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对自己子女无情无义,对敌人心狠手辣,却在这一刻,泪湿眼底,终不见……
淑儿,我知你怨我,所以独守梨园,十年不见,一朝出宫,我作为一位帝王,已来不及收手,却眼睁睁看着你独自一人离去,就是最后一面都未曾与我相见,如今这叶氏已如那大风之中,即将要被折断的树枝,从此以后,这叶氏也将永存于历史之中,我负了你,负了父皇,负了为我野心而死的几位孩子,亦负了这叶氏和南洲朝臣,罢了罢了,走到这里,再后悔亦无用了,听天由命吧……
这一天相爱之人,频频离间,再无相见之期,阴阳相隔,只剩那皇宫之中,昏暗烛火之下的那位帝王,每每对月相思,对月悔恨,再无机会弥补……
………………
叶浮清醒来时,白炎已在床榻间守了两日,那人那天在茶楼昏倒,吐到衣襟前的衣物都被血浸湿,昏迷不醒,气息微弱,恍然间,又回到了那个守在她床边的日日夜夜,怕她从此再也醒不过来,再丢下她一人,
“你醒了?”小心翼翼的话语声中尽是疲惫,就是再怎么掩饰,叶浮清却依旧听出来了,白炎看着叶浮清脸色苍白的样子,那想伸出去摸摸她的手,顿时僵持在空中,神情中满是害怕和不安,若这是梦,怎么办?叶浮清似有感觉一般,猛的拉住白炎的手,紧紧的握住,虚弱道:
“白炎,我不会让你再独自一个人的……”那手掌处传来的感觉,提醒着白炎这一切都不是一场梦,突地,伸手紧紧的抱住叶浮清,颤抖着声音道:
“我以为,以为你真的走了,我以为……”那般紧拥叶浮清的力度,几乎是想把叶浮清揉进骨子里一般,回拥着白炎,
“我不会再让独自一个人了,不会了,真的……”若不是此刻醒来,听道那人如此疲惫的声音,叶浮清似乎怎么也能够想象着那时她昏迷那么长时间时,白炎是怎样的状况?那日问他,那人便只是轻描淡写的只字带过,如今听他的声音,想必那些个日日夜夜都是这般提心吊胆的过着,生怕她突然就离去,又或是怕醒来时无人在身旁会害怕,那个可以顶立在皇宫之上的人啊,如今竟成了这般,从白炎怀中退出来,摸索着抚上那人的脸庞,竟觉得恪手的很,
“白炎,你瘦了……”咽去喉咙间传来的阵阵酸涩,低声道:
“是瘦了,你昏迷了两天,都未曾醒来过,我怕你醒来不见人在会害怕,便一直守着,所以便也来不及回到小山林中去,在小镇的客栈里,寻了言老来给你看,现下可还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去叫言老……”话落,欲站起身朝外走去,却被叶浮清拉住,朝着他摇摇头,
“无事,我现下感觉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你不用去叫,你……”话未完,恰巧这时言老从外头直接推门而入,郎声道:
“可是醒了?老夫来看看……”闻言,白炎站起身迎去,
“是醒了,请先生来替清儿来把把脉,看看……”言老笑道:
“早就算着你今日会醒来,这不来了吗?哈哈,看你这样子,还有那一国储君的样子吗?”顿了顿,又继续道:
“昏睡了两天,她现在醒来会饿,也不便吃些太补的东西,你下去楼下让店家小二煮些粥上来吧……”白炎点了点头,看着叶浮清依旧一脸担忧的样子,那般不舍,却让言老笑弯了眼,
“怎么,怕老夫下药啊……”话一落,顿时让叶浮清红了脸,转身朝外走去,白炎一离去,客房内的气氛一下子就沉寂了下来,言老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沉声道:
“姑娘……”
“先生不用姑娘姑娘的叫,若是不嫌弃可唤浮清的名字……”还未说完的话已被叶浮清打断,听叶浮清这般说,言老也不再拘束,心里也对叶浮清越发喜欢,
“浮清,浮清,浮云万般,一生清卷,确实是好名字,那老夫也就不客套了,我原以为你还能多撑些时日的,只是……”
“先生有话便直接说好了,浮清还有多长时间?”
“唉,丫头,天启蛊虫历来本就阴狠,再加之是有剧毒的蛊虫,性质便不一样了,你经脉皆毁,已伤之根本,这几月的沉睡,纵使恢复一些,之后调理会好些,可是也……接下来你还有多少时间便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话到这里,其他的也就已经不用明说,她足够明白了,千折腾,万折腾,还是抵不过这白云苍狗的变化,白炎,一次又一次说相见无期,你我到头了,现在想来,怕是真的已经到头了,
“先生,可否多为浮清来些药,多苦都没关系的……”
“丫头你……”
“先生,你不懂,我多一些时间便可以为白炎多做些事,也可多陪他一些时间,有些痛可能只是当时很痛,谁都比不过时间,若是将来我真的走了,白炎他在那个位置也能有个念想,不至于孤单一个人……”
“你决定了?当真要放弃?”抬起头,无声的看着那不知是何处,不知摆放着何物的地方,语气也在顷刻间变得有些伤感,
“嗯,是要放弃,就算先生不说,浮清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也自知时日无多,可是白炎不一样,他有大好年华,一身才情也不可随我一同淹没,他生来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从小的抱负也是这个,所以不该为了我而放弃,所以我便陪着他,倾尽全力助他,便足矣……”片刻的沉寂,叶浮清回过头来,看着言老,低声道:
“南洲如今已乱,除却西江不明态度,余下的两国和外族都想吞并南洲,有些事,浮清这个死人已经不能够去做,还有望先生代劳……”言老点了点头,也应承了叶浮清的话,
“丫头,你尽管交待便好……”
白炎端着小粥进来时,看着言老和叶浮清两人之间逃的甚为欢快,也不禁笑开了眉眼,只要叶浮清在的地方,他笑的也越发的多了,看着白炎进来,言老也不好打扰这小两口,
“老夫这就走了,多多注意自己的身子,抓好药你来取便是……”寻了为叶浮清抓药的方子,便出去了,白炎端着白粥走到了叶浮清的床榻前,
“小二店家有些忙,便借了他们的小厨房,这是我亲自熬的,你尝尝。”边说话边将小粥吹冷,用小勺递到叶浮清的嘴唇边,叶浮清惊奇,那十年和这丫的在一起,可没见过人家下厨的好么?都是承远那个蠢货做的菜好吗?今日是有口福了,
“你做的?这可得尝尝……”毫不扭捏的吃了一大口,入口的小粥柔软的紧,几乎是已经吃不过那种白米饭的味道,入口即咽,如水一般,清淡的很,平淡无味的感觉却让叶浮清几乎难以下咽,喉咙发紧,鼻间也开始酸涩起来,这人从来都未曾干过这样的事啊,低头一口口的吃着白炎那喂来的粥,不一会儿就已经见底,
“胃口好,便再吃点,好不好?”站起身端着碗欲再去盛一碗,却被叶浮清猛然拉住衣角,哑声道:
“我困了,不想吃了,你陪我睡会儿,好不好?就这里……”说着还从里面挪了挪位置,拍着自己的身旁,一双桃花眼里尽是无助,白炎心下一酸,也明白过来叶浮清的用意,轻轻的拍了拍她的手背柔声道:
“好……”将手中的碗放于一旁的桌上,走到床榻边就和衣躺在叶浮清的身侧,随势也将叶浮清拉了下来,拥入自己的怀中,紧紧的抱住,鼻间传来的若有若无的梨花香也在这几月中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尽是药味,就是如此,他亦觉得未有半分不适,那怀中的人瘦的心惊,那从前一身的光芒,行走于黑暗之中,夹缝生存于天启皇宫,一次又一次暗杀来袭,那人都一脸的不在意,一双桃花眼中满是算计的光芒,手中的银针顷刻而出,那人必死无疑,而现在的她,犹如一个废人,没有引以为傲,杀人从不失手的银针,废了右手,废了武功,废了双眼,就这样在这里,挣扎着,日日喝着那一碗碗苦涩的黑汁,若说叶浮清是骄傲的,白炎又何尝不是,背对着白炎侧身躺在那人怀中,一双眼睛睁的老大,想要努力看清楚,却终究是一片黑暗的无力感顿时袭遍全身,
“满头华发,苍老容颜……”那无情的几个字,一遍又一遍的回响在脑海里,眼泪也禁不住说眼角而下,落进那枕头之上,瞬间隐下,再不见踪影,耳畔传来那人轻浅的呼吸声,怕是已经累极了吧,她的白炎,从前那时总是一席白衣着身,俊朗的容颜,英气挺拔的眉宇,一头就是她也羡慕的黑色长发,那些与他相伴的岁月里,那人时而从站于窗边负手而立,看着窗外那点点的梨花飘散而下,那样子犹如邻家的少年郎,在眺望着不知从哪儿而来的姑娘,时而眉间紧皱,日夜燃着书房中的烛火,为那边疆被外族侵犯的百姓,担忧着,一次又一次,在她遭遇暗杀时,总是恰巧经过,又恰巧救了他,那时他知,她亦知,他天涯海角,战场之上,马革裹尸,她亦想尽一切办法从皇宫中脱身追随,他懂,她亦懂,那曾经坐在高堂之上,便能翻云覆雨,运筹帷幄的帝王储君,怎地今日就为了她,变成了这样……
恍惚间,竟在梦里清晰的看见那气大殿之中的情景,白炎一席白衣都已被她的鲜血染红,带着她,一步步从皇宫之中出来,走到那帝京中的医馆,一间间的去,却又被人一个个的赶了出来,那时的她,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皇宫之中,帝王不下令,所有的太医皆不敢为她诊断,甚至为她探探脉,出了皇宫的大门,她一身是血的样子,惊骇的众人,仍旧不愿为她诊断,就算进去了,探了叹脉搏,也终究是对着白炎摇摇头,那身为一代储君的样子和形象在顷刻间全部崩塌,梦里的一切一切,她都看的甚为清楚,
“白炎,白炎,你别去了,别去了,没用了,没用了,你别这样好不好?”一声声的唤着那人,那人却根本未曾听见,仍旧不顾一切的抱着她,到处去找大夫,白炎是人,不是神,抱着叶浮清走了那么多的路,也有耗尽的时候,终于体力不支,白炎抱着叶浮清站在最后一家医馆时,腿已经在颤抖,
“你们救救她好不好?她没有死,没有死,真的,我有感觉,我有感觉,她真的没有死,求求你们了,只要救她,什么我都允你们,求求你们了……”看到这一幕,心瞬间被拉紧,
“白炎,你不要求他们,不要啊,你是一国储君,怎么可以这般,你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啊……”就是再无力的喊,那人也听不见……
出来的是一位老伯,年纪已经很大,看着眼前的两人,猛的一惊,原以为这位老伯也同之前的那些个人一般,不愿为她救治,却不想那老伯连忙让开路,
“快,快,快将这位姑娘抱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