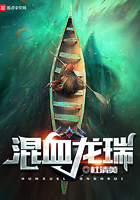啪!
突然的一声脆响,惊得夕照心中一震。只见崇祯将奏折往桌上一摔,倚着椅背,一脸烦躁难抑。
“皇上……?”夕照小心询问道。
“这些文官就没别的事可奏了吗?成日价都是为郑鄤求情,说什么忠良难觅,从轻惩处,难道他们一个个都收了郑家的银子!”崇祯忿忿说道,脸色就像暴雨将至的天空。
“皇上息怒。”夕照好言安慰道,“官员们也是好意,万一这郑鄤的罪行不实,他们也不愿见皇上误罚了好人。”
“好意?哼!这郑鄤……”
崇祯话没说完,只听门外太监报:
“司礼监王公公求见。”
“传。”崇祯话语一断,便没再说下去。
不一会,王承恩抱着一叠奏折进了暖阁。崇祯示意他放在案上,拿起第一本翻开大致一读,又啪的合起扔了出去。
“皇上……”王承恩眉毛一颤,也吃了一惊。
“以后这保郑鄤的折子少送来给朕,朕不爱看。”崇祯闷声说。
“是……”王承恩小心翼翼的捡起地上的折子,惶惶然揣在怀里,不敢再上。停顿片刻,只听崇祯又道:
“郑鄤的案子,刑部审得如何了?”
“回皇上,刑部称目前证据不足,尚还无法将郑鄤定罪……”
“证据不足?”崇祯眼眉一立,“有郑鄤族舅吴宗达作证,还有什么证据不足!”
“是……奴婢也如此说,已替皇上催下去了,约莫过上几日,便可结案了。”王承恩谨慎说道。
“嗯。好。”崇祯点点头,神色稍稍舒展,“传朕口谕给刑部,无论舆论如何,定要秉公查办,不可姑息。”
皇上自从凤阳归来后,不知为何忽然换了副暴躁的性子,以至于为了一个无官无爵的小人物的罪行,竟然动怒至此。是杖母一事触动了皇上的孝子之心,还是贿赂求官撩起了皇上的憎恶之情,又或者这些都不重要,只是凤阳之祸以来的自责与抑郁,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夕照左思右想,也没想出答案;包括朝廷上下的内官朝臣们,也是满腹问号,摸不着头脑,只有感叹着圣意难测,各自唏嘘。
“不过无名小卒而已。皇上若想杀了高兴,那便杀了好了。”
司礼监中,王承恩把玩着新入手的翠玉把件,表情漠然。
“……公公这话说的,还真是事不关己。”李全抿了口茶,笑道。
“嗨,无关痛痒的案子,自然是事不关己。”王承恩说道,“满朝上下,这种文震孟似的石头脑袋还嫌不够多么,此次轮到这个时运不济,惹上了皇上,正好也少了干净。”
“瞧皇上的意思,郑鄤确是非死不可了。”李全一副气定神闲,脸上依然浮着那丝若有若无的笑。王承恩自是事不关己,而李全自己,看起来也并没为此案如何痛心疾首过。
王承恩冷笑一声,举起那翠玉把件对着光,细细审看。这玉略呈椭圆,上浓翠,下淡青,质地通透无比,一幅山石盘松也雕得精巧细腻,宛若天工。“其实这郑鄤……本也不是非死不可的,首辅大人那边不过也只是要绝了他入朝做官的路而已。这事啊,要坏,就坏在这帮心怀鬼胎的文官身上。”
“哦?这话怎么说?”李全问道。
“怎么说?这还不简单。”王承恩一挑眼,“你想这郑鄤是谁告的?”
秋风卷着枯叶的残骸挑起门帘,偷偷放进来一丝寒意。李全愣了一愣,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
“首辅大人也混得一日不如一日了,想整治个人,竟招来这么些人力保。”王承恩放下玉,慢声细气接着说道,“要说这里边,真正关心郑鄤生死的亲友旧识也不是没有,但大多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看准了法不责众,有利无险,一来显显自己的正直忠良,二来想保下了郑鄤,灭一灭那厢的威风。只不过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怒,这些石头脑袋们这么个谏法,惹得皇上较起劲来……嗨,怕是反倒要害了人家的性命。”
“嗯……皇上此番也奇,怎地就和这平头小民认上了真。难道真如众人所言,是继母二字犯了忌?”
“皇上的心思,谁猜得出来呢。”王承恩随口应道,也不甚在心,话音未落,又仔细审看起这翠玉来。
李全见状,笑笑道:“要说温大人还真是会投人所好。知道我们公公喜欢这玉石玩意,最近隔三差五的老给公公送些腰坠把件,莫不是有求于您?”
“哼,管他那许多。有求也好,无求也罢,送来,杂家就收。”
远远有小太监走来,将门关严,又将门帘摆正。王承恩眼不离玉,却嘴角一撇,露出一丝轻蔑的笑。
几日后,刑部送来奏章:郑鄤罪行尽皆属实,但此案影响重大,贬谪太轻,充军太重,实不敢妄断,惟请圣裁。
“既是事实,又有何‘不敢妄断’。”读了奏折,崇祯眯起眼睛。
“是……”王承恩欠身一应,眼中偷偷窥探着崇祯的表情。只见崇祯手执朱笔,在砚台边抿了抿,竟不作任何迟疑的,挥笔在折上写下了四个令人心头发颤的大字——其罪当诛。
其罪当诛,其罪当诛。这四字圣裁一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是曾上疏力保郑鄤的文官们,就连未曾参与过此事的人们私下里也是议论纷纷,深感不公。且莫说那杖母蒸妾的罪行是否真的属实,就算件件属实,大不了流放充军则已,何必要重罚至此。不过,即便是议论骤起,为郑鄤求情的折子倒是一下子少去了许多。圣意已决,大势已去,那些投机的折子一撤,只有黄道周等郑鄤的同道之人,还在坚持不懈的上疏请愿,千方百计的要留住郑鄤的性命。
尽管这一切,早已走进了死胡同。
“勿因一时之气,污万世之名……”窗外寒风瑟瑟,窗内的崇祯面若冰霜,冷冷的合上折子,“出言不逊至此,这黄道周是想随郑鄤而去吗。”
“皇上息怒……”这一阵子,夕照不知说过多少次皇上息怒了。看着日显暴戾的皇上,夕照不解之余,心中也很是惆怅。毕竟在他心中,郑鄤之事也并不是一件值得激愤至此的事,而这些年来,温和隐忍的皇上也并不是这样一个怨怒频频的人。这究竟是……
“事不顺心,要如何息怒。”崇祯拉着脸,声音低沉,“忤逆乱伦,贿赂求官,朕不过是要处置这样一个人,竟跳出这么多人拼命阻挠,难道朕身为国君,连惩罚一个不忠不孝的人也不能了吗?”
“这又岂会不能。”夕照收回思绪,顿了顿,笑笑道,“只是皇上此次的对郑鄤的责罚的确……令人颇感意外,黄大人他们也只是……”
“连你也觉得朕处罚过重?”未等夕照说完,崇祯斜斜一睨,竟直接将话挑明。
“不不……”夕照见崇祯眼中含怒,连忙辩解,“皇上莫怪,小人只是觉得……”夕照话说一半,忽然没了下文。
“觉得什么。”崇祯压着声音问道。
“没……没什么……”夕照口中欲言又止,心里片刻间转了几个来回。到底该说不该说……?说了,皇上定然不悦,不知会不会迁怒责罚于自己。但皇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信任自己,为着皇上的信任,夕照又觉得似乎有那么几分直言的义务。但到底……还是算了。退一步讲,那郑鄤的死活,与自己又有何干,对皇上以诚相待,不过也只是希望皇上能顺心顺意而已,这政事本身,又岂是我辨得明,管得了的,不如……便姑且顺着皇上的心意好了。想到这,夕照闭了口,咽咽口水,生将剩下的一半话囫囵吞下了肚。
可崇祯却不愿只听一半。“觉得什么?但说无妨。”他又问了一遍,声音渐高,却又忽然柔和下来。
宫女轻轻走进屋来,将崇祯手边半凉的茶水端下,又换上了一杯新泡的热茶。夕照低着头,目光无意识间随着宫女波动的裙摆移出房外,一个晃神,又慌忙收了回来。不能不答了么……皇上已然追问,若是推脱不答,岂非是欺君之罪。何况皇上亲口说了但说无妨……夕照偷偷瞄了瞄崇祯的侧脸,虽不晴朗,似也并不阴沉。夕照深吸口气,壮起胆子,但开了口,声音却仍虚虚的没有底气:“小人只是觉得……郑鄤的罪状多是深宅大院中的闺门秘事,旁人难以亲见,只凭风言风语,所述难免有些夸张不实。郑鄤固然是有罪……但应是罪不至死,皇上还是三思而后行……”
“够了!”一声闷喝突然截断夕照的话语,崇祯脸上风云骤变,抬手猛然一拍桌子,吓得夕照慌忙跪在地上。只见崇祯满脸愠色的瞪着夕照,薄唇微动,好似有话要说,却最终强忍不发,只是一甩袖子,留下伏在地上不敢起身的夕照,大步离开了暖阁。
这之后的几日,夕照心中战战兢兢,却也还是照常来暖阁侍奉崇祯,但二人同处一室,却没再多说一句话。夕照自然是很想寻个机会与皇上重归于好的,只是一见到崇祯眉头紧锁的烦闷样子,便犹犹豫豫的不知如何起这个话端。尽管答应过皇上要说真话,但明知皇上心情不佳,还拂逆皇上心意,也的确是鲁莽了些。不过夕照内心深处仍是相信,一向英明的皇上并不是有意拒听真话,就算一时胸中不畅,总归还是不会真心气恼自己。想到这,夕照算是大抵能够安心。不过今后,这些无甚意义的真话,还是少说为妙吧。又是一日值事毕,回房的路上,夕照暗自想道。自己毕竟也不是言官朝臣,说这种话落不着好,还平白的招惹皇上生气,何苦来哉。
就这样,一日日间瞬息而过。而之后这天发生的事,夕照却是如何也预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