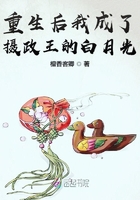建州,百姓堵在朱府门前,叫嚷着要见朱豪,一身形高大的壮士跳起来将门上的白灯笼扯下来,狠狠往地上一摔:“王爷不可能死,朱府不该挂这灯笼!”
“王爷死在朱府,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蹊跷,让知府大人出来,他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王爷有神明保佑,不可能死的,肯定是遭人陷害,知府大人为什么还不出面给我们一个交代。”
“王爷死了,留下我们怎么办,还有谁能和皇上抗衡?”
池靖卿死讯传开,百姓人心惶惶,义愤填膺,从早上便堵在朱府门口,现下到了晌午,人数不减反增,使朱府之人出不来,外人的人也进不去。
朱府不远开着一家茶楼,二楼一男子站在窗口,倚着栏杆,看着下面的百姓,唇角笑意玩味:“二王爷,你将自己的死讯传出来,将朱豪堵在家里,可有何收获?”
朱豪被堵在家中哪儿也去不了,那些个勾当自然做不了了,其中受益最大的人就是他了。
池靖卿也不否认,转着小巧精致的茶杯,漆黑眼眸深邃如渊,目光落在远处,道:“朱豪运往漠北的货出了问题,他定要为此奔走,若他无法出面,下面的流程无法进行,他本就因为那批货使得漠北二王子对他有所不满,如今再失了信誉,之后的合作他定会遭到提防,久而久之,两人相互怀疑,合作自然瓦解。”
裴无忌离开窗口,歪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毫不客气的翘起二郎腿,唇角轻佻:“朱豪能将生铁走私的神不知鬼不觉,也能悄无声息的离开朱府,倘若他出去了,继续行走私之事,王爷岂不白白弄出这么大的声势了。”
他可不认为这法子真的能够困住朱豪。
“无妨,”池靖卿道,“百姓过来闹了便足够,朱豪再行事亦会谨慎些,且他出了朱府,本王也有应对之策。”
边说边起了身:“小王爷,朱府便麻烦你继续盯着,本王到时间该会会漠北二王子了。”说话之时,已变了神色。
裴无忌偏着头支着下巴,但笑着,也未应下来,池靖卿却仍安心的走了,笃定了他不会走开似的。
漠北二王子乃王位候补人之一,性格相较刚愎自用的澹台月华,多了份商人的狡诈,能力与其不相上下,却错失太子之位,这让他一直心怀怨念,此次与朱豪合作,也是想借此证明自己能力不比他差,却在合作的过程中,得知了澹台月华的死讯。
并且从朱豪手中购买的生铁纯度高,且价格公道,拿来制作兵器再好不过,是故澹台月华死后,他也未停止购买。
池靖卿边在澹台月明的房间的屋顶停下,脑海中将他的动机过了一遍,侧耳细听着房中动静,屏住呼吸,将气息隐匿。
澹台月明负着手站在窗边,红衣魅惑,容颜也无漠北之人的粗犷,微皱着眉,道:“朱豪的货近来频频出现问题,是时候找下一家了。”
他身后不远处站着一玄衣男子,稍作思量:“从前朱豪手中的货从未出过问题,这次恐怕并不简单,若不是朱豪的疏忽,便是有人作祟,我们与朱豪中断合作,岂不中了那人的计了。”
“正因事出突然,我们才不能继续与他合作下去。”澹台月明目光变得锐利起来,“若是他的疏忽还好说,怕只怕当真有人作祟,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并了如指掌,届时我们便被动了。”
走私生铁算不上什么光荣的事儿,趁没有被调查出来前撇清关系,乃明智之举。
玄衣男子稍作沉吟:“二王子的意思是池靖卿的手下在继续他生前未完成的事?”
按理来讲,池靖卿死了,反叛军没了首领,也即将瓦解,此处天高皇帝远,仔细想来再无人会调查此事,但朱豪的货近几次频频出问题,若说有人作祟,也只剩池靖卿的余孽了。
澹台月明唇角溢出冷笑,高深莫测:“倘若池靖卿没死,这一切便都合理了。”
玄衣男子眼中略有愕然:“可池靖卿的葬礼不是已经办完了,他怎么可能没死。”
澹台月明适才还只是猜测,稍作思量,愈发确信:“池靖卿若活着,朱豪必定会畏头畏尾,难以放开全力做事,只有他死了,朱豪才敢放肆的倒卖生铁,才有可能露出马脚。
且即便他真的死了,也极有可能布置了什么,他的心腹和女人没有在他死后立即离开朱府,便是再好不过的证明,他手下之人皆不简单,谨慎些总归错不了。”
澹台月华的死给他提了个醒,兵不厌诈,更何况是面对池靖卿这等诡计多端之人,更不可掉以轻心。
玄衣男子走到他身边,做了个割喉的手势:“二王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如我们……”
澹台月明余光瞥见他的动作,眸子深了深。
池靖卿听到此,眼底掠过一抹狠厉,从袖中掏出一封信笺,掀开一叶瓦盖,扔下信笺。
信笺落地之声轻微,却未逃过两人之耳,玄衣男子未去捡信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房间,腾空而起,落在对面房檐上,警惕的四下看去,但见四周除树木摇晃,再无其他。
回到房间,但见澹台月明已拿起了信笺,走上前去:“二王子,外面没人。”
澹台月明无半点意外,道:“那人能将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上了屋檐,将信笺扔下,必定身手极高,若你能追上,反而奇怪。”
似乎笃定了他身手不如那人。
玄衣男子双手握紧又松开,问道:“二王子,信笺是什么人留下的?”连面都未见便被比了下去,他岂止是不甘。
澹台月明收起信笺,声音已然冷了下来,语气亦与适才不同:“是何人留下的不重要,让朱豪来见我。”
朱豪府邸虽被围得水泄不通,出门却不难,半个时辰后,他身影出现在先前的茶楼。进了雅间便察觉气氛不对,且往常只有他与澹台月明两人,今日后者身后却多出一玄衣男子。
他心下狐疑,未表露出有何不解,照常入座,只还未坐下,澹台月明便将一封信笺仍甩到了桌上,虽身无戾气,却仍扔得他心中一突。
坐下的动作顿了顿,看了眼信笺便看向了他,缓慢坐下后,问道:“这是……”虽有疑惑,却并未伸手去拿。
澹台月明仍一身红衣,鲜红之色映衬得他面孔更为妖冶,唇角凉薄:“朱大人既找好了下家,何故再与我漠北合作,价钱不公道岂不委屈了你。”
朱豪面色大惊,拿起信笺粗略扫过,恼怒地将信笺拍在桌子上:“这是污蔑,二王子,这绝对是假造的,我与漠北合作这几个月,货物从未出过问题,只多不少,这点您是知道的,我怎么再与明召合作,这不明摆着是挑拨离间,二王子您要明察!”
那信笺上竟是“他”与明召王爷的往来记录,点明了他嫌弃漠北给出的价格迟迟不涨,有弃暗投明之意。
商人重利益,这本没什么,偏生让澹台月明有所察觉,无论真假,皆会破坏他们的关系。
澹台月明面带愠色,唇角冷意更甚:“若那一封是伪造也便罢了,难道其他也皆是伪造?”说话间,打了个手势,身后玄衣男子不知从何处弄来厚厚一沓信笺,放到了他面前。
朱豪一封一封的看着,脸色愈发紧绷:“这……”
澹台月明没有给他丝毫解释的机会,略带嘲讽:“良禽择木而栖,此乃人之常情,只是朱大人既然择了良木,也便没有必要再与漠北合作,大可直言,何必在货物上弄出差错,平白失了信誉。”
换言之,他信了这些信笺便是朱豪与明召往来的证据。
朱豪心中大喊冤枉,面色凝重且带怒意:“二王子,明召与大越都来往甚少,就更别提我这无名之辈,怎能入得了明召皇室之人的眼,您怎能相信这些片面之言,你相信我,这绝对是有人恶意陷害!”
澹台月明比澹台月华聪明得多,现下却宁愿相信这些信笺,也不愿意相信他这大活人的话,显然,与他中断合作的念头原本便有了,但朱豪却想不到这点,只当澹台月华被着信笺上的说辞蒙蔽了双眼。
朱豪迟迟未听见他的回应,心中愈发忐忑,刚要继续辩解,澹台月明便道:“若本王子没有看错,与你通信之人乃明召小王爷,据本太子所知,明召小王爷便是前几日与池靖卿一同入住你府上的人之一,而这些信笺也是在你房间床下发下,你不会要说这不过只是个巧合罢了,一切皆是本王子多疑。”
他语气咄咄逼人,空气随之凝固,朱豪深感压迫之力,却被心中愤怒支撑着,此时连彼此身份也顾不上,蹭地站起身来:“二王子,我定要查出是何人所为,我的信誉更不能被人白白玷污!”说罢,大步朝门走去。
“不必了。”澹台月明道,“朱大人在信誉上着实有欠缺,本王子觉得有必要中断合作。”
朱豪脚步一顿,双手紧握成拳,手背青筋暴起,恼火地离开。
玄衣男子在人走之人,才问道:“二王子,这些信笺也并不一定是真,且除了朱豪,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合作之人,我们是不是太过武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