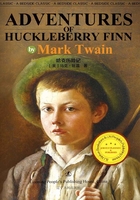临走之前,她去了趟艺术学校,假期还有两个老师在办班。看门的大爷把门打开,詹雨桐掺在一群孩子里涌向楼梯口。艺术学校的教室在三楼,詹雨桐踩着楼道的棕色瓷砖进了教室,孩子们正在画画。笔和纸都是画室提供的,孩子们在学画前先要学一段时间的花鸟画,花鸟画有时在写生生态室里画,生态画室里有很多花,除了花以外,还有各种动物的模型,其中一只老虎和一只脖子上带着铁链子的狼尤为醒目。模型架上摆着各种瓷瓶和瓦罐,还挂着一只羊的羊角,一个缺了半边脑壳的人像模具。走廊尽头有一个小卫生间,卫生间没有通风口,尿臊味不时从里面散发出来。出了卫生间,房顶上吊着一个康佳牌21英寸电视机,电视是供接孩子的家长们观看的。每次上卫生间洗画笔,孩子们都担心电视机会掉下来砸着他们的头。来接孩子的家长坐在椅子上等孩子下课,她们手里拿着未织完的毛衣,还有看了不知多少遍的皱巴巴的时装杂志。走廊的墙上贴着孩子们画画的获奖作品,还有报道艺校校长的板报,一个整版都是校长这几年的业绩,板报上的字小,走廊里的灯又暗,所以几乎看不清楚写的啥。来接孙子的那位爷爷头发全白了,仍穿着好几年前的灰裤子灰衣服和圆口黑布鞋。一个孩子的母亲穿着长裙,坐在椅子上玩着手机游戏,穿着一双凉拖,脚趾甲涂了红色甲油,走廊里的人不看她的人,总是盯着她的脚看。每间教室都安装了玻璃门,铝合金的拉手,家长们隔着玻璃门可以看到孩子们在画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地做画。另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坐在凳子上,一边抽烟,一边与一个男人闲聊,看她的手被烟熏的程度,可以断定她是常抽烟的那种女人,她可能是女企业家、女老板或者女干部。女人的长发如瀑,黑色牛皮凉鞋,肉色短袜,看上去很苗条很飘逸。
这几天,她一直想对康天龙实施报复,真正挪用公款的是康天龙,她丈夫不过是给康天龙当了替罪羊。她了解她的丈夫就像对一本书那样熟悉,她知道他是个正直无私的人。康天龙把他安排在科长的位子上,就是看他为人忠厚老实,欣赏他的唯命是从,他对詹雨桐同样是唯命是从。只要康天龙吩咐给他的任何一项开支他都照办,从不拖泥带水,不该列支的款项被他列支了。
丈夫进了监狱后,她教学生画画再也没有先前那种耐性了,她的脾气开始变得烦躁不安,动辄就摔东西,还砸碎了几个花瓶,连花瓶里的假花也用高跟鞋踩碎。
一天,他还去了丈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保洁员坐在椅子上打瞌睡,桌子上放着未读完的圣经,一脸皱纹的老女人还穿着花衣裳,像极了民国时期的地主婆。她准是拖地板拖累了,才趴在桌子上睡着的。卫生间的灯坏了,许是灯管的镇流器坏了,上厕所的人也不能把门全关上,要留个缝儿,哪怕进来一点光也行。站在窗户前往外看,街上穿梭着来来往往的车辆,一对情侣揉着睡眼,挽着胳膊从楼道里走了出来。马路对面未拆完的废墟里还住着一位孤寡老人,她独自生了火,烟筒从一块残缺的玻璃洞里伸了出去冒着烟,天这么热,屋里还架着炉子,烧的是一元钱十块的蜂窝煤。她女儿偶尔来看看她,劝她快点搬出去,她执意不搬,誓与房子共存亡,嘴里咕哝着:“就是楼塌了,压死我,我也不会搬!”
回到家,詹雨桐从公寓里拿了一些私人用品,还有那块手表一买了好几个月了一是她给儿子准备的生日礼物。临走时,她把那幅《阿拉斯加少女》卷起来装在包里,她要把它带到乡下去,带给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