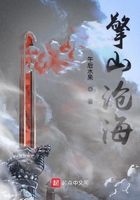营盘望楼上,张七郎的右眼不住地跳动,多次与极北妖兽血战的经历,让他对自己右眼对危险的预警准确性寄予了足够的信任。他几乎马上就挂上弓弦,拈起裹了毡布的火箭点着,张开了寻常军士半弓也开不了的四石强弓。
火箭飞掠,一百二十步,那层扎营时就铺下的干草被点着。
远处无数杂乱脚步声已然清晣可闻,一百二十步外的熊熊火光仍不能照亮的黑暗处,无数的身影耸动,向朔方的大营蜂涌而来。张七郎的面上没有一丝慌张,作为朔方仅存的三千骑军之一,从十年前就开始跟随古虎餐——对于他而言,漠视生死渴望战斗已不需要勇气和热血,只是习惯。
但当他伤痕累累的手握紧了示警的铃绳时,他愣住了。
那是天督军!天子亲军天督军!那些奔跑过来的人们,终于冲入了一百二十步外火光所能照亮的区域,尽管他们已然面黄肌瘦,但那残破的衣甲和一缕缕挂在衣上的战袍,倒拖在地上的战旗,都明白无疑地宣告,他们是天督军,号称东陵第一强军的天督军!
张七郎奋力扯动了铃绳,放声高呼:“绕营!绕营而走!”望楼上那几个无甲白袍少年才醒觉过来,连忙画出五角星芒,这是一个风系扩音魔法。风于五行在木,故之将心神沉入东方木位;风从四方隅而来,故谓之角,使魔法者口中咒语亦作角音之韵。五芒星辉骤成,顿时狂风大作,远远将百二步外的焰火逼得向外吐出数尺长的火舌,张七郎的声音也在风中远远传开了出去。
此时那些衣甲狼狈的天督军残部已纷纷绕营而走,两三迷糊的,未奔入营盘五十步内,便被弓箭射倒了,只是百二步外那黑暗里,无数绿莹莹的眼珠子,万马齐奔也似的蹄声,冲入火光照亮的范围里,竟是漫山遍野的三头犬。
营盘内战鼓如雷,近千无甲白袍少年列阵奔向营盘木墙,这五六年之间古虎餐使良师教他们修文习武,自己更是苦心教授他们魔法,却从不使他们参与极北妖兽的征战。少年人总是好强,尤其是身怀绝技未曾一试的少年,是以尽管大多数人双股战战,仍是随着军令,划出那练习了千万次的五芒星,把心神探入南方离火之中,一时间,近千五芒星骤然放亮,星芒一涨,几使人疑银河群星坠于人间!
五芒星消逝,近千火球便静静地浮现出来,只随那发号的白袍少年一声令下,呼啸着的火球便借着风力,如流星雨一样灿烂绚丽,淹没了那些带着硫磺气味的地狱三头犬,连接的爆炸声在火光里响起,不时有三头犬被轰得支离破碎地飞起。
如果修真者关于大罗金仙的传说是真的,似乎神仙已经开始眷顾东陵?
明月不知何时躲进乌云,也许大罗金仙只是美好的传说,或者他们根本不曾留意东陵的苦难。朔方军,东陵土地上成建制存在、战力最强的军队,在这夜,崩溃了。
说时迟,那时快,从张七郎引弓到近千白袍少年发出火球,前后不到半刻钟的工夫,其间有天督军残兵惊恐的呼叫,有三头犬的低声咆哮,有风系魔法的狂风,有流星雨一般的火球,以至火球引起的连环爆炸。
数万朔方军,大部分都是被征召的平民,而长途的行军已经让他们的神经比最柔弱的蚕线还要可怜,这突然而来的无数声响让他们惊恐万状,营盘里发生了军旅中最为可怕的事:营啸。
紧接着西面的营盘被天督军的残卒涌入,跟着涌入的还有无数的三头犬,悲泣与号叫,在夜空里,如瘟疫一般传染了这支长途跋涉而来的军队。
营盘外,那株被雷殛得只剩半截的枯树,几片可怜的残叶,颤颤地发抖。
营啸是军队最无奈的失败,连古虎餐和陆相爷也被裹在其间,溃军下意识地向北方狂奔,古虎餐站在马车上,望着那仍在苦苦支撑、离他愈来愈远的白袍少年,苦笑地自语:“要是知道终究得为你们生命负责,也许,之前应该让你们去参加与妖兽的征战。”
陆天波带着十来个军中兄弟,挥枪驱逐着身边的溃卒,以防他们把古虎餐和陆相爷的马车也掀翻了。也许为了安慰自己,也许为了安慰古虎餐,陆老相爷悠悠地对陆天波道:“不要太在意,意料之中的损失罢了……”
古虎餐只是无奈地笑着。或者别人会指责陆老相爷——这所谓的损失,都是活生生的人命,但对于古虎餐来说,冲龄整村人被屠杀,接着养育他的师父又死了,荣华富贵也享受过,纨绔子弟也做过,天牢也呆过,西陵入侵时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也干过了,然后三十来岁的灵魂困在只有十岁小孩的躯体里的事情,也在他身上发生——只要不是因他死,其他人的生死,他实在很难激动起来。
也许唯一让他牵挂的,只是那远远的、仍在奋战的白衣少年们,但古虎餐知道,他十岁的身躯委实不足以在这疯狂的时刻,给予败兵溃卒们信心和坚定,如果他跳下马车企图去与那些白袍少年会合,唯一的结果,就是被无数大脚踩倒在地……所以,他能做的,也唯有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