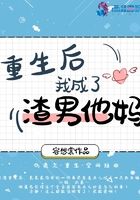(1)
萨特对另外一个女人产生激情之后,唤醒了波伏瓦对女人的兴趣,进入了双性恋时期。波伏瓦对自己的双性恋本性也曾迷惑不解:“在哪个方面我是一个女人,在哪种程度上我又不是?”
姑娘们迷恋她,因为她是女人,但她很多时候更像男人。
波伏瓦不厌其烦地对自我真相进行探讨,想了解自己的愿望使她显得近乎自恋。她曾玩笑般地对萨特谈到,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到她60岁的时候,姑娘们就会在教室里自杀。
那个英俊的博斯特曾对她说:“啊!你!你真像个男人!”
在她和萨特的关系中,有研究者说,波伏瓦是那对情侣中的男人,而萨特则是女人。波伏瓦的一位女性崇拜者曾说,她曾经那样充满激情地爱过波伏瓦,就好像波伏瓦是一个男人那样。
由于自己的“磁性”,波伏瓦没有主动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这些女性的爱慕之情。所有这些年轻女性都需要她生动的个性,她的超然态度,她的处世不惊和大智若愚,这就是她呈现给那些仰慕者的样子。
波伏瓦的一位女情人纳萨里·索克林曾下尽工夫去赢得波伏瓦的兴趣:在她早上离开旅馆去学校时等她,在她上完课时等她,在夜里拒绝离开她的房间,有规律地送给波伏瓦小礼物。她嫉妒波伏瓦的女性朋友,并且尤其嫉妒萨特。
对于自己的双性气质,波伏瓦一生中曾多次予以公开有趣的否认。波伏瓦拒绝公开女同性恋者身份的原因,是她担心这样一种身份对她的养女西尔韦·勒邦或许会有危险。如果勒邦的同性恋者的身份被人知道,勒邦就会遭到波伏瓦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种种难堪。
(2)
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如此褒奖同性之爱:女人之间的爱是沉思冥想的;爱抚的目的与其说是占有对方,不如说是渐渐通过她再造自我;分手被废止了,没有斗争,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在真正的互惠意义上,每一方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君主又是奴隶;二元性变成了相互性。女作家陈染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即在女性之间建立一种乌托邦,摒弃肉体之爱,建立起精神世界的共鸣。
(3)
但是,在波伏瓦的多次同性恋事件中,不仅没有实现这种同性之爱的乌托邦境界,反而伴随着许多的伤心落寞。
如前文所述,正当波伏瓦与奥尔加的恋爱进入甜蜜时期时,萨特毫不犹豫地插足进来,奥尔加再也不是波伏瓦一个人的了,波伏瓦只好伤心地选择了退出,开始寻找新的情感寄托,博斯特只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备受磨难的比安卡。
比安卡是波伏瓦在巴黎莫里哀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她是犹太人,长得非常漂亮,笑容甜美,高三时认识了波伏瓦。她很快喜欢上了这个从不备课、讲课却激情澎湃的女老师,波伏瓦也注意到了这个对哲学感兴趣的女生,两人很快无话不谈。波伏瓦把自己的经历,包括扎扎、萨特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协议,与奥尔加的三重奏等等都告诉了比安卡,比安卡为之着迷。
在波伏瓦的影响下,比安卡的某些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她不再相信贞洁的重要性,也不再认为姑娘在结婚之前应该保持童贞,还放弃了对同性恋的成见。比安卡觉得她和波伏瓦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波伏瓦在吸引她,使她放弃了从小父母给她灌输的观念;另一方面,在迷惑中她还不愿意走得太远。
比安卡发自内心地崇拜波伏瓦,并逐渐演变成一种狂热的激情。毕业会考后,两人一起去旅行,在一个简陋的旅馆里,她们发生了肉体关系,在回程的客车上她们已经像一对情侣那样亲密无间了。
1938年秋天,萨特认识了比安卡,立即被她的美貌打动了,34岁的萨特对18岁的比安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写了很多炙热的情书给比安卡,比安卡完全沉醉在萨特的甜言蜜语中,以为这就是爱情的全部。但很快,萨特就要求比安卡和他上床,在萨特看来,只有和她上床才算真正征服了一个女人,就好比吃东西,含在嘴里不算,只有咽到肚里才算数。
这次性经历让比安卡非常不快,反而觉得波伏瓦在肉体上能给她更多的满足,萨特也觉得她索然无味,开始觉得和波伏瓦分享同一个女人并不有趣。1939年9月,萨特就给比安卡写了绝交信,这大大伤害了比安卡,她一生都没有原谅萨特给她造成的伤害。
在比安卡遭受萨特的伤害后,波伏瓦经常来安慰比安卡。
1940年6月,巴黎失守后,波伏瓦开始逐渐疏远比安卡。比安卡认为,这也许因为自己是犹太人,波伏瓦才和自己划清界限。不久,波伏瓦突然提出和比安卡分手,说自己其实更喜欢男人,这让比安卡再次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她对波伏瓦的感情比对萨特的还要深。虽然后来比安卡嫁给了挚爱自己的丈夫,但伤心的往事总是挥之不去,久而久之,她得了抑郁症。波伏瓦得知自己把比安卡伤害成这样后悔不迭,1945年,她主动联系比安卡,建立了一种新的友谊。后来,波伏瓦名声大振,还一直保持着与比安卡的友谊。
1980年萨特去世后,波伏瓦出版了萨特的书信集。其中《致海狸与其他人的信》于1983年出版,书中收录了13封萨特写给比安卡的情书,该书导致了比安卡与波伏瓦之间再次发生了一次大的冲突。虽然此前,经波伏瓦请求,善良的比安卡答应了波伏瓦同意出版,但她要求不要暴露她的真实姓名,并删去和她身份有关的内容。波伏瓦信誓旦旦地保证,信件用完后一定物归原主,但书出版后,波伏瓦没有按照约定归还信件,并推三推四,一拖就是三年。直到波伏瓦去世,她也没有归还信件。
1990年,《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出版,再次侵扰了比安卡的生活。《致萨特的信》和《战争日记》是1939年至1941年间波伏瓦的日记和给萨特的信,书中记载了在那段时间里,波伏瓦同时和博斯特、丽丝、比安卡保持着性关系。在比安卡看来,该书以“极其庸俗”的方式泄露了她的全部私生活,波伏瓦在揭露别人隐私的时候,什么都敢说。
愤怒至极的比安卡决定进行反击,她写了《被勾引的姑娘》,在书中总结波伏瓦时这样写道,“我在发现我终身热爱的女人的真正人格时感到一阵恶心”,“西蒙娜把她班里的姑娘当成一块鲜肉,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然后将她们献到萨特手里。不过总而言之,我相信他们未发表的条约、他们的‘偶然爱情’,实际上只是一种‘诀窍’,是萨特为了满足征服的需要而发明的、西蒙娜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讹诈”。
波伏瓦在自传中说:“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稍稍脱离原有轨迹时,也就是文学诞生之时。当生活乱了套时,文学就出现了。”她不能制造国家的不混乱,但是她可以制造自己生活的不幸或者混乱。她所制造的“非正常生活”一次次激发了她的文学灵感。
(4)
在波伏瓦众多的女情人中,唯一没有被萨特染指的只有丽丝。
丽丝是移居法国的俄国人,她也是波伏瓦在莫里哀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丽丝与波伏瓦相识时,萨特正在服兵役,波伏瓦一个人在巴黎过着孤独的日子,是丽丝填补了她生活的空白。有时,波伏瓦想念萨特,丽丝就妒火中烧,她常常对波伏瓦说:“我恨不得他死了才好。”丽丝性格顽固,脾气暴躁,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在波伏瓦与丽丝的关系中,波伏瓦始终是被动的,丽丝对波伏瓦非常依恋,她经常赖在波伏瓦的公寓里不肯回家,一定要和波伏瓦睡在一起。
本着不欺骗不隐瞒的原则,波伏瓦将这一切也都写信告诉了萨特,萨特没有表示支持,也未对她搞同性恋大惊小怪,更没有愤怒与嫉妒,这正符合他的爱情理想。
因为丽丝的母亲举报波伏瓦勾引女学生,波伏瓦被学校开除了公职,失去了教师工作。1944年巴黎解放后,莫里哀学校才决定恢复波伏瓦的名誉,但此时的波伏瓦已对重执教鞭失去了兴趣,恰逢《女宾客》出版后大获好评,这促使波伏瓦决定从事专业写作。
二战后,萨特从集中营归来,丽丝嫉妒波伏瓦和萨特频频约会,她从中百般阻挠,随着时间的流逝,丽丝渐渐对萨特消除了敌意,但却不愿与他建立情人关系,她给予萨特的只是友谊。中年后的丽丝精神出现问题,变得神经质,1968年死于流感。在她死后一个月,波伏瓦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写着丽丝的名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只水果蛋糕,是丽丝临死前两天给波伏瓦订做的,这让她大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