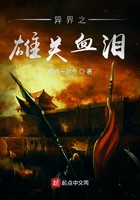在我们指向的枪口下,只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这老太婆身子佝偻,眼睛已接近瞎的程度。
我想,我还是该尊敬地称她为老人家,尽管她是杀人犯的母亲。
我们包围在她的面前时,她正勾着腰身,手夹着筷子在一个鼎罐里搅拌,搅拌出来的味道香飘房间。我闻着它判断这又是萝卜炖野味,而且除了萝卜可能还有黑豆子,都是吃着香甜、诱人食欲的好东西。
鼎罐是用一根铁钩挂在房梁上的,鼎罐下就是燃烧的木块,干木柴发射出的火苗则像一个谄媚的县乡干部在拼命地全方位地舔着鼎罐这个省市领导的屁股。
老人身子站起来的时候,脊骨碰上了洪耀的枪口,老人便歪开头,伸出手抓着洪耀的枪口,用她那双快瞎去的眼睛瞄了半天,然后才丢开手,也不说话,坐在了凳子上,继续用筷子搅拌鼎罐内炖着的肉块。
毛峰给洪耀使个眼色,带着洪耀开始屋前屋后地搜查。我和周彪悍便看守着老人。我用昌水本地话问:“老人家,您好啊!您一个人在家吗?”
老人哦了一声,说:“你们坐啊!”抬起头,看着我,看着我手里的枪,然后指着我手里的枪笑着说:“孩子,你都这么高啦,这么大啦,还玩驳壳枪!”老人说的时候,还做了个很高的手势。她嘲笑我们大孩子玩玩具枪。
在乡下,农民喜欢用木料给孩子们做玩具枪,一到过年就作为礼物送给孩子。当然,这孩子一般是男孩子,只有男孩子才喜欢玩这个。而驳壳枪是乡下人仿照电影里的做法。显然,老人把我们手里的枪当作了家长赠送的玩具枪。
我看出老人不但眼睛不好使,而且耳朵也背,我便蹲下半个身子,几乎附着老人的耳朵喊道:“您一个人在家吗?您崽老倌呢?”我说崽老倌,就是指他儿子。在昌水周边几个县,都有把儿子叫崽老倌,把母亲叫娘老子、父亲叫爷老子的习惯。
老人听清我的话了,摆手道:“莫讲,莫讲,他冇回来。”老人叹了口气后又说:“过年也冇回来,真冇用!”
当老人的筷子在鼎罐里搅拌时,我瞥见了鼎罐内的不少东西,心说这不是一个老人在三两天内可以吃完的。而且,我和大家都注意到,这鼎罐,是乡下人用来炖煮东西用的最大的鼎罐。
我判断老人不是真的糊涂或者耳聋了,甚至,她将我们每人手里的枪当作玩具都是故意装的。她两个儿子一个是当兵,一个是护林员,而护林员也是玩猎枪或玩鸟铳的,因此,她不可能对我们手中黑黑的、乌亮的家伙会看不出来。
而且,她的那种从容,对闯进他家的人所表现的那种不闻不问,更显现她的老成和精明以及心中所想。有人说过,眼睛不好使或耳朵不好使的,会比一般人都心灵亮堂、精明睿智些。这个老人或许就是。
“你们找我崽老倌?找哪个?大的还是小的?”老人这时突然主动问我。问我的时候,还抬起头好像去看大家,但显然,她只是做个样子,她看不清大家。如果说我对他耳背有点怀疑的话,那么对她的眼睛不好使是相信的。
我问话的意思是我们找她哪个崽。我便老实地答道:“两个都找。”
老人摇头,说:“大崽在城里,细崽在山里。”在城里我们明白,但说细崽在山里,我们就有点不明白了,因为这就是山里。不过,仔细想想,也许是指林场吧,作为护林员,工作单位肯定就是林场了。另外,或许他们山里人看来,山有更大的山,也有更深的山,作为护林员,应该有更深的山林要保护。
我站起身来,大声喊了一句:“老人家,打扰了!”,便给周彪悍和另外几个撇了撇嘴。
遵照我的撇嘴约定,我们都来到了门外。毛峰在周围每一个角落搜查了好几遍后,见到我和周彪悍就摇头。我和周彪悍会意,我说:“大家注意到没有,老人鼎罐内炖的肉可不是一个人吃的。”
周彪悍也点头说:“房间内看起来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但我想他们应该是躲起来了。”
毛峰说:“我们可以守株待兔,这小子晚上肯定回来。”
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两个杀人犯崽老倌不可能丢下娘老子一个人,中午不过年,晚上一定会回来。”
周彪悍于是小声对大家说:“这样,我们现在装作撤退,找个林子深一点的地方藏起来,晚上再来逮个正着。”
我同意,毛峰同意,李光前、洪耀、向李弘自然也都同意。于是,我们回转去跟老人家装模作样打了个招呼,我和周彪悍并跟他提早拜个年,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小道下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