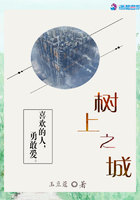下到仙姑岩,我知道有的是时间,便伫立在仙姑岩前观起其景来,李光前说,我们不如躲到那伞下去午餐。我和周彪悍都觉得主意不错,毛峰也没有提出异议。
李光前说的伞,就是仙姑岩岩层凹进去的那个空间。而他说的午餐,其实就是吃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当然也有军用罐头。
一打开饼干,撬开罐头,大家都像约好了似的,全都禁了声,并不是看着饼干难以下咽,而是一个个心思重重。
我知道,大家都是一个肉体,谁也没有高尚到成仙,此时都和我一样,想到了今天是除夕,想到了半山腰那老人家炖烂的香喷喷的肉块,想到往年的这个中午和家人的那桌丰盛的团圆饭,以及即便不和家人在一起,在部队,除了必要的值班,也同样有菜有肉……
可现在,我们几乎和指导员讲述的在云南前线躲在猫耳洞内的景致无二。
好在我们不是婆婆妈妈的小孩、老人、女人,我们既然都是想念吃肉的一大群体,那么我们就有狼一样的意志。在短时间的思念和留恋后,马上恢复到了常态,一个个很有程序的吃喝:一块饼干,一块罐头肉;一口罐头肉,一块饼干。
向李弘首先打破沉寂,开口问我说:“霖哥,你还记得那只黄鼠狼吧?我去把它取来,烧着吃。”
我正嚼着罐头肉,还没来得及回答,洪耀那小子像听到了他妈妈的呼喊一般,大声问:“哪里有黄鼠狼?去去!我跟你一起去!”
周彪悍没有忘记他的组长身份,吼道:“去去去,去什么呀?不能乱走!”
向李弘和洪耀被噤声了,不说话了。我看看他们两位,怪可怜的,便在吞下最后一口肉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也不想想,黄鼠狼的屁那么臭,那肉能吃吗?你们几位没闻过,向李弘是领教了的。”
向李弘皱着眉摇着头说:“这样想起来,我不敢去取那家伙了,没有食欲了。”又将我和他在路上碰到的那只入了笼子的黄鼠狼的情况细细地讲了一遍。
李光前说:“既然它的肉吃不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设机关捉它呢?”
坐得稍远一点的毛峰嗤了一声,嘲笑大家说:“你们真是嫩,问出幼稚的话。捉黄鼠狼是靠它的皮卖钱,那皮值钱呀!我没听说过吃黄鼠狼的肉的。告诉你,凡是带鼠字的动物,肉都吃不得。李霖,你说是不?”
我点头又摇头说:“一般人不吃,但也有胆子大的,吃了,还说味道好。我们老家的人是不吃黄鼠狼肉的。小时候,青蛙、麻雀、蛇、野猪、兔子、斑鸠、野鸡等等,都吃过不少。”
我正数着,谁知洪耀这个二百五又喊起来:“李班长,你别数了,你一数,我就恨不得把毛警官打的那只野猪拖了来,宰了吃。哎,那个香啊!”他还仰着头眯着眼,做了个迷醉的样子,逗得我们一个个呵呵笑,但都不敢大声笑。
毛峰没有笑,他赶紧做了个打住的手势,周彪悍也跟着做手势。
大家静止了后,周彪悍对毛峰说:“我说毛头,你有什么办法没有?大过年的,晚饭改善下伙食,或者又来回走个十来里山路,到支书家里去吃?”我知道周彪悍是心慈,刚才吼了洪耀和向李弘,现在想办法挽救,用以安慰战士们。
毛峰摇摇头,但又点头,然后笑着说:“晚饭有办法解决。我带你们去个地方。”不过,话刚说完,马上又摇起头来,并自言自语:“不行啊……”
我不是自作聪明,周彪悍一提出来时,我心里就想,解决晚饭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是邓天虎老娘的那个鼎罐,而离开这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将不是地方,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要守株待兔守邓天虎兄弟!
我也学着刚才毛峰嗤笑的样子嗤了一声,对毛峰说:“毛警官,你该不会是想带我们去某个藏粮食的山洞吧?”
我这样说,并不是胡说八道,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山里人尤其是打猎的,都有暗中藏粮食的山洞。十二岁那年的寒假,父亲就带我去过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表叔家。表叔带我和父亲去看过他的狡兔三窟之地。当然,我说的狡兔三窟之地,并不就是表叔的三个房子,而是表叔打猎时,有时候为了守野兽,晚上都不回去,不回去住哪里呢?就是山洞。因此,山洞会放有野兽轻易弄不走的粮食。这粮食一般就有风干的野味和保鲜的红薯、玉米球之类。
毛峰说:“什么都瞒不住你小子。”
我说:“去山洞都不现实。我看,我们晚饭就守着老人家的那个鼎罐。等把两兄弟捉拿住了,我和彪悍出几块钱给那老人,买下她鼎罐里的肉,请大家吃!”我本来是想单个请大家吃,但想想周彪悍家庭条件比我好得多,便说两人合伙,再说,周彪悍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应该负起让兄弟们吃好点的责任。而毛峰,是五比一中的一个,我们把他当客人对待都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