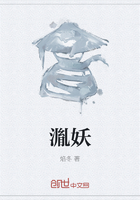我等着青菱姐和姐夫的到来。
我信心满满,我认为陈江雄哭都会将他的姐夫哭来的。我毫不怀疑。
但当天下午,青菱姐没有来,青菱姐的夫君也没有来。我虽然有失望之感,但细想,自己也太急了,没那么快的。再等等吧,明天一定会来的。
可谁知,第二天,陈江雄的那位姐夫仍然没有来,倒是监督李毅死刑执行的检察官一早上就来到了我的禁闭室。
一同来的还有指导员。
指导员在被我殴打过后,是第一次见我。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突然见面,搞得我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但指导员像没事似的,不冷不热地问我道:反省得怎么样?检讨书写好了吗?看到我本子上一页纸都没有写完,又说:不急,过几天写不碍事,你有的是时间。
而我,怎能不深深的自责?甚至连和指导员双目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但我既跑不掉,也走不开,更做不了土行孙遁地。我唯一的,只能低下头小声地说:“指导员,对不起!”
指导员手一扬,将我还要说的话打断,或者,是怕我还有什么话要说,快速地制止。
我当然得止步。但我还以为指导员会和我说说其他的话,或者跟张扬攀谈攀谈。但他都没有。他对检察官说:“有什么需要吗?同志!”然后又关切加商量的口气问检察官:看是不是将我带到办公室去,这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检察官也像指导员刚才那样,扬扬手说:不必。这里可以。
这样,指导员就关上门出去了。我想,他可能在外面等。他既然极力帮助我和我的兄弟,自然对检察官会礼节到位,何况,我们的方进同志,平时本就是非常注意礼节的。
检察官拿出一封信递给我,并不说话,仅是眨下眼,示意我阅看。
我一看,是青菱姐的落款。我一惊,抬头看了检察官一眼。
青菱姐说,江雄跟他说了李毅的事,很震惊。她还说,李毅的娘是她同学的姐姐,她只要做得到,一定会帮,况且,李毅是她在大队小学代课的时候教过的学生,她知道李毅是个优秀的孩子。最后她说,这个带信给你的人,就是你们的姐夫,叫姜汤,他是个正直的人,他会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帮助李毅的。
我看到信的最后,心开始砰砰直跳。信纸捏在手里,手微微发颤,我不是害怕,而是激动。我看着这个大哥好一会儿后,才嗫嚅着说:“原来......你就是......是江雄的姐夫。那我也叫该......该叫你姐......姐夫。”
我太激动了,这江雄姐夫的突然出现,竟然让我也快成向结巴了。
青菱姐夫摆摆手,咧咧嘴道:“李毅的死刑暂缓了,这个你也知道了。公安那边与你们武警派出的同志昨天也都去昌水调查了。不久就会有结果的。年前,可以的话,我也找个时间去去昌水,正好还有其他的案子要办。”
青菱姐夫平淡地说,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难怪陈江雄说,怕他。我此时本想热情地认他这个姐夫,可他就不给我机会,除了刚才咧咧嘴,像阴冷的天要开天窗似的,但还是始终没有开脸,继续维护他那铁树开花一般的难度。
不过我还是说:“谢谢姐夫!”
青菱姐夫扬起手,摆了摆说:“还是别。叫我老姜吧,我姓姜,叫姜汤,叫姜检察官也行。”
我虽然不情愿,但想想这也不无道理。在部队呆了这几年,也是开始政治性地觉悟到,这个办案的事,是要避让亲戚关系的,以公事公办的形式出面才好些,而事实上,在不认识姜姐夫前,他也在操心这个案件,并没有敷衍塞责,更没有草菅人命。通过他和大家的努力,已经将李毅的死刑暂缓执行了,在严打期间,让一个流氓案件暂缓死刑执行,原本就是如登天一般艰难的事。
我于是说:“姜检察官,非常感谢您!您是好人!”
姜检察官这时作凝思状说:“我问你,你说入伍前,也就是1983年的5月5日晚间,你们去邻村看电影,你承认是你强行吻了袁绵绵,李毅也指正是你。那么,你现在跟我说实话,到底是李毅,还是你为了救李毅,自己揽上的?”
我想说,但意识到他人的话比我说更有用,于是抖开手中的信给青菱姐夫看,并说:“青菱姐的信中都说了,李毅是他教过的优秀学生,她也不相信李毅能做出坏事来。另外,您回去还可以问江雄,他也是最了解李毅的。而我,入伍前是个调皮鬼,我爸叫我‘翻天印’,村里的人都晓得。”
青菱姐夫点点头。
“那你为了救李毅,就不怕自己坐牢吗?过去的事,很多人唯恐捂不住,你倒还满世界喊,拼命往自己身上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很简单,他是我兄弟!同年哥哥!我要救他!”
见青菱姐夫眼角溜了我一眼,我又补充说:“就是李毅没有帮我去顶替参加违法违纪人员学习班,我也会想法子救他!而且必须救!当然,前提是,他不可能做坏事,更不可能是一个流氓!他如果是流氓,那么,满世界的人都可能是流氓!”
我说得有点激动。
青菱姐夫又点点头。
然后,他站起来,应该是想离开。但他在又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后,说:“讲句实话,你小小年纪,很有勇气,也坦率,我有点佩服你!等你自己的事结束了,出来后,到我家里去跟你青菱姐聊天吧!”
说着,拍拍我的肩,出去了。
我感激加失落地盯着他的背影。但突然,我身子一热,像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温热。尽管在这温热产生前,我有过因他的冷淡而出现了从激动到冷却的过程。
青菱姐夫走远后,我对着窗外哈哈大笑。当张扬那小子在外面敲门问霖哥霖哥有什么事时,我喊道:张扬,让炊事班吉霸子帮我炒个菜,还带一碗谷酒来。
炊事班的班副吉霸子,叫王吉庆,是我在机动中队唯一一个同县同乡同年入伍的战友。因此我们的关系是两个哑巴睡一头,好得没话说的,我要他加菜、送酒,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被发现或被调离炊事班,是完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