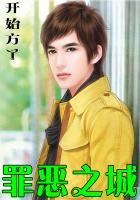玄烨回到宫里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的十九日了,再过一天就是霁兰薨殂一个月的日子,这天是四七的第二天。
太后看着给自个儿来请宫的玄烨,心里莫名地有点虚,身子往后靠了靠,琢磨着怎么提霁兰的事。虽说霁兰是重病不治,可若不是这些年来孝庄文皇后和太后的冷淡与鄙视压制,霁兰说不准不会这么早走了。
太后盯着玄烨请安跪那的身子,也老了,心里动了些怜悯,可转而又在想,霁兰到底也老了,后宫里不乏年轻貌美的年轻女子,玄烨不久就会忘了。
死个妃子也不算什么了,葬礼都这个样子了,看看都要赶上前面没的三个皇后了,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太后的心又定了,也不觉得亏欠霁兰和玄烨什么了。
玄烨请了安,又陪着太后说了两句话,就出了宁寿宫,先回了乾清宫换过了衣裳。虽说衣裳一直穿得是素服的颜色,却是石青色,玄烨不满意换上了月白色,一身孝的出了乾清宫、东华门。
东华门外的銮驾仪卫,都没有散去,静静地等着玄烨的到来,一路这么着去了朝阳门外的孙文善花园。
霁兰的灵棚搭在孙文善花园,金棺静静地停在灵棚里,在京的年长阿哥、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民公侯伯以下四品官以上,全穿着孝服,跪在这里。
玄烨下了銮舆,望着眼前白色的一片,飘着的灵幡,眼泪就要流了出来,却忍住了。他是君王,天下的表率,可以哭妻,却不能哭妾,这是儒家的规矩。玄烨恨这规矩,却无力打破。
走到了神牌前,看着黑漆上的几个白字,心里冰凉凉的,不能相信霁兰已经这么去了。
梁九功端着托盘跪了下来,双手高举着。玄烨却没有去拿托盘上的酒,不确认霁兰真的不在了,这酒绝不能祭。
玄烨迈步往后走去,停住了步,望着金丝楠木的棺椁。棺椁上漆着厚厚的漆,漆上浅雕卍不到头纹饰图案,卍不到头纹饰图案上面再雕刻藏文经咒。这副棺椁是玄烨早为霁兰准备的,那时说的是图个吉利,避一下邪,没想到却用上了。
走了过去,玄烨摸着棺椁,这副棺椁跟给自个儿准备的一样,想得是生同衾死同穴,如今自个儿好好地站在这,霁兰却已经不见了。
“打开!”玄烨的眼睛不肯离开金棺一眼,虽说冰冷的可怕,可还是要探究里面是不是真躺着霁兰,只要里面没有霁兰,那就是他们把霁兰藏了起来,不许霁兰跟自个儿见面。
或许这是霁兰想要吓自个儿了一下,嫌自个儿撇下她一个人去谒陵了。霁兰一下大方,可是这回也许真得舍不得自个儿这么着去,所以才会这样的。
玄烨想着,眼睛更一眨不眨盯着梁九攻领着太监小心地搬开了金棺上的棺材盖,一点点露了出来,看到了修陀罗经被下的霁兰头上戴着吉祥帽,帽下的脸那么小,好像不到一个巴掌大了,可是神态安详,像是正在熟睡。
玄烨伸出了手,摸向了霁兰,想唤醒霁兰。手指尖才碰到霁兰的脸,没有人气的冷把玄烨的心冻住了。霁兰的脸永远是温热的,再冷的天,摸上去是冰凉,却也不是这种感觉。
眼泪滚了出来,滴在了修陀罗经被上。玄烨的手抖着,揭开了修陀罗经被,看着穿着鹅黄宁稠绣五彩龙云龙袍蟒袍,戴着一串朝珠。这一身的吉服,霁兰是要去做什么呢?玄烨迷惑着,似乎又忘了霁兰已经在不了。
玄烨手的手在霁兰的身上移动,冰冷僵硬的锦缎提醒着一件事,霁兰真是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玄烨的手去握住了霁兰交叉的双手,像握着玉,却是永远也握不暖了。
浑浊的泪水,硬憋着的哭声,玄烨不知道能给霁兰带走什么,留点什么,垂着的花白辫梢提醒着玄烨“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弯下腰来,从靴筒里拿出了把银刀来,抓起辫梢,微用了下力,就割了下来。
梁九功吓得用手捂住了嘴,没让那声惊呼出了嘴。主子居然违反了大清朝的祖宗礼法,后丧皇帝例不割辫。这是祖制呀,前面死的三个皇后,主子没有一个割辫的,就是孝庄文皇后薨殂的时候,主子才割了辫。
可孝庄文皇后,那是什么人,那是主子的祖母,是一手扶持主子当上这个皇帝的,是连主子都说:“太皇太后祭物,俱照世祖皇帝往例。”。这就是告诉天下人,孝庄皇后虽是太皇太后,可实际上就是皇帝。
良妃怎么能跟前面的三个皇后比,跟孝庄皇后比,主子却就这么割了辫。
梁九功左右看了看,幸好这只有自个儿一个,千万别给人知道了,尤其是那些大臣,不然又不知道要兴出什么事来,那些御史还不得死命地参奏主子。唉,主子也苦呀,心爱的人死了,连个哭都要给人说。
玄烨把截下来的发辫细细地缠好,又从腰带上摘下了个月白色的荷包,那上面的连理枝,还是霁兰绣的。这荷包还是裕王没了的时候,霁兰给连夜绣的,那时怎么就绣了连理枝呢?
“物在人亡无见期,闲庭系马不胜悲。……忆君泪落东流水,岁岁花开知为谁”,玄烨瞧着手里的荷包,想不明白,难道那时霁兰就知道今儿个会用上?玄烨趴在了金棺的帮沿上,闭上了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滚。
滚久了,眼睛涩了,玄烨直起了身,把截下来的发辫卷卷塞进了荷包里,又小心地把霁兰身上的修陀罗经被揭开了,再解开了鹅黄宁稠绣五彩龙云龙袍蟒袍颈下的纽襻,握着荷包的手伸了进去,一直伸到了最里层。
曾经温热柔软细腻的地方,现在只有冰冷僵硬如玉石了,一点点摸着,最熟悉的地方成了最陌生的地方,不敢触碰,却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如此了。
哪怕是僵硬的玉石,玄烨也是如此地贪婪,想把这冰冷留在心里,停留在那里。玄烨把荷包放在了霁兰的心口上,喃喃着:“等我,等我……”
再去看霁兰,那唇角好像有了笑意,知道玄烨的心思,把那截发辫留在胸口,就是陪着她走过黄泉路。
玄烨想要惊喜,难道霁兰又活了过来,再细细地看着,霁兰的脸依旧是那样地端庄慈祥,却又是那样的遥远……
把霁兰的鹅黄宁稠绣五彩龙云龙袍蟒袍上纽襻扣好,再盖好了修陀罗经被,玄烨说不出“盖上”那两个字,倒退着往外走,走了四五步才回到了外面的灵堂。
不去看跪着的儿子和宗室王亲、民公们,玄烨再次站在了霁兰的神牌前,从跪着的梁九功高举着的托盘里取过酒卮,微微一斜,酒淌了出来,就像玄烨心头的血眼里的泪落在了地毡上……
玄烨祭完了酒,走出了灵堂:“让起居注官把给良妃奠酒的事记在起居注上。”
梁九功“嗻”了声,看看跟着来的大臣、侍卫,这不都穿着一身的丧服给良主子行礼了,那起居注居跪着不也得记。可主子还要这么吩咐,就是怕起居注官不记。
唉,主子就是怕人看低了良主子呀。想想也就三个皇后才有这待遇了呀,梁九功的心里酸酸的,谁能体会主子的心呀。
碍着太后,宫里不好太办霁兰的丧事,玄烨让胤禩在禩贝勒府大办:恩准胤禩素服三年,在禩贝勒府供奉霁兰的像。
胤禩更是得了玄烨的特许,予定例外,加行祭礼,每祭焚化珍珠金银器皿等物,大设筵席,自初丧以至百日,日用羊豕二三十口,备极肴品。
胤禟、胤?、胤祯这些阿哥们约着给胤禩馈粥。满洲丧葬之事有个习俗,因丧家笃于居丧,以至饮食一道也就荒废了。亲友恐其伤生。特馈粥糜,劝令少进。
现在有了玄烨的意思,胤禟、胤?、胤祯这些阿哥们,馈粥就成了用羊、猪这些来送了。
胤禛瞧弟弟们这样,也想去送了,自个儿这回想把良妃额涅移至五龙亭的要是给罕阿玛知道了,那不是前功尽弃了。
胤禛想想,也让人备好了几十口的羊和猪,往禩贝勒府抬了。
按着胤禛想的,胤禩素来和软,不会不顾忌别人的,这羊和猪一抬过去了,胤禩总不能打笑脸人吧。好歹,自个儿也是胤禩的四阿哥呢。
胤禛这么想着,骑着匹马,后面让侍卫抬了这几十口的羊和猪,浩浩荡荡往禩贝勒府去了。
到了禩贝勒府门口,来接的是禩贝勒府的长史,跪了下来:“奴才给四阿哥请安。”
胤禛骑在马上,就要下马来:“你们主子呢?”
“我们主子……”长史低了下头,“因着连着这些日子守灵,哀痛过度,我们主子病了。”
“哦……”胤禛把收养挑了挑,“那我去看看八弟,这些羊和猪,你就收进去吧。”
长史看了看给拴着四条腿挂在木棍上的羊和猪正那不停地叫呢,再看看那些听到羊、猪叫声来看热闹的人正跟在这队列的后面,想着四阿哥不知道羊和猪杀了送?这活得送过来,真是造声势,举国喧传,都知道四阿哥雍亲王胤禛给八贝勒来馈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