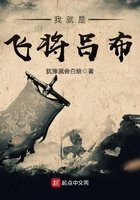离开尉迟恭家,天色已黑,三人只得投宿客栈,一路上窦虎郎都神情愉悦,竟轻哼起了小调。
“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
孙安祖好奇道:“虎郎,你哼的是甚么调子,俺却是从没听过。”
刘黑闼也有些好奇,扭头询问窦虎郎。
窦虎郎不知怎么解释,只能含糊道:“自打上次醒来,莫名其妙的就会了,我也不知是咋回事。”
“要俺说,你八成是狐仙附体,要么怎么会这么多东西。”
窦虎郎顿时无语,这是刘黑闼开口:“虎郎,我看你今日之举,可是想拉那尉迟恭入伙?”
“三叔,非是侄子妄言,侄子料定,那尉迟恭乃是能成大器的人物,若能得他相助,我等如虎添翼啊!”
刘黑闼闷了下,说道:“只是你今日这手段却有些不甚光彩,我却担心那尉迟恭心中存有恼怒,就算他日后上了寨子,也不肯真心效力。”
“三叔,那尉迟恭也是个磊落的汉子,小侄这是摆的阳谋,若是他心中情愿,以后自会安心做事;若要反悔,小侄也不会强求于他,恭送他老母回家便是,以后也好想见。再说了,莫非三叔还不相信小侄的手段?”
刘黑闼点头道:“这倒也是,我们要做事,便不能太拘泥于手段了。”
孙安祖却没那么多心思,言道:“那尉迟恭一身武艺很是了得,怕是三弟也不是他的对手,他要是敢不答应上咱寨子,俺老孙就绑了他来!”
三人一边闲聊一边进了客栈,要了房间各自安歇了。
且说三人离开后,尉迟恭闷声道:“娘,那窦小郎君明显不怀好意,您怎的还答应他到那寨子里住着,这样,叫孩儿如何是好。”
老妇人笑道:“娘这双招子又没瞎,怎能看不出那小郎君的心思,跟老身斗,他还嫩了点。”
尉迟恭更加不解:“既然娘已经看出,为何不回绝了他,这样孩儿也不难做。”
“为娘为何要回绝?到他寨子里吃他的喝他的岂不乐哉?”
尉迟恭大急:“娘……”
“傻孩儿,那孙安祖是个没心眼儿的,但那小郎君,娘却看得出,花花肠子不少,有个词怎么说来着?是了,狼视鹰顾!这小郎君啊,心思大的很呐!
一个小小寨子的少当家,可满足不了这位小郎君的胃口!为娘知道,他是看重于你,才会讨好为娘。话又说回来,人家做的还算磊落,换作旁人,直接一根绳子把为娘绑了去,胁你做事,你又能如何?”
尉迟恭怒声道:“他敢!”
老妇人又道:“我儿啊,你少幼习武,尽得了尉迟家传,如今这一身本事莫不是要荒废了不成?”老妇人声调越来越高。
尉迟恭道:“孩儿何尝不想马上求取功名?只是您老也知晓,孩儿上次去投那刘武周,此人嫉妒孩儿本事,只让孩儿做些看门打杂的活计,却不给孩儿上阵杀敌的机会。”
“那不就是了,如今既然有人看重于你,你不抓住良机,日后岂不后悔?”
“这算什么良机?他一个小小的寨子,怎能容得下孩儿?俺要是投了他们,岂不是好马配了坏鞍?”
老妇人大怒道:“竖子!你给老身跪下!”
尉迟恭不敢忤逆,俯身跪了下去。
老妇人随手抄起一根笤帚,朝着尉迟恭劈头盖脸抽了下去,只抽了几下,便急剧咳嗽了起来。
尉迟恭哽咽道:“娘,孩儿不孝,惹您老生气,您莫要气坏了身子。”
老妇人喘息了几口,道:“你嫌人家庙小,容不下你这大佛。为娘问你,你这佛就是整日间打铁赚几个肉好再与那些闲汉耍钱厮混不成?!”
尉迟恭羞红了脸,嗫嚅不言。
老妇人又道:“想你先祖尉迟武公,当年不过一界家奴耳,后来征战沙场,才博了功名爵位,那是何等的英雄人物。
你爹时运不济,尚未袭爵,这北齐说亡就亡了,他又不肯侍奉大隋,便回返老家务农为生,这才有了你。怎的到了你这,一辈不如一辈,先祖武公在天之灵,怎能安息?!你配得上‘尉迟’这姓氏么!”
尉迟恭连连叩首,泣声道:“孩儿无能,让祖父蒙羞。”
“那你就做给先祖看看,让他知道,尉迟家的儿郎,没有一个孬种!把尉迟家的威名给老身重新拾起来!”
“可是娘,他们高鸡泊如今可是贼人,俺清白人家,怎能屈身为贼?”
老妇人呸了一口,不屑道:“贼?谁是贼?你看看,如今这官府做的都是甚么勾当!他们喝人血吃人肉,比贼还狠呐!这样的朝廷,便是反了他又能怎地?
再说了,他先帝就不是贼么?抢了自己亲外甥的皇位,好不要脸!他才是大贼!当今这个天子更是比他爹还不要脸,杀兄弑父,这是畜类都干不出来的龌龊勾当!他更是大贼!
那个叫窦建德的,老身也听人说过,当年他老父故去,上千人给他披麻戴孝、扶棺送灵,这样的仁义之人,还不值得你去投奔么?还有那窦小郎君,娘这招子看不错人,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思,怕是要青出于蓝的,也不值得你去投奔么?”
尉迟恭再次磕头应道:“如此,孩儿便听娘的,这次孩儿便去相助他们往塞外买马,孩儿再观察于那窦小郎君,若他真有才干,孩儿就带着娘一起投了他们寨子。”
老妇人点了点头:“你且起来说话吧。”
尉迟恭应声而起,垂手躬立。又听老妇人道:“我儿,你生性憨厚耿直,为娘教你一句,你且听好。
眼下这大隋,让为娘说,马屎面上光,里面是一团糠啊。这天下,怕是安生不了几年了,他窦家父子要真是能成事的名主,我儿就好好辅佐于他,以后未必不能封侯拜相。
若是他父子都是不成器的阿斗,我儿要么就另投明主,要么就直接并了他的寨子,你来做这龙头当家的!为娘的话,你记下了么!”
“娘放心,您的话孩儿都记下了,不敢忘掉一个字。”
次日,尉迟恭到客栈寻了窦虎郎三人,答应助他们前往塞外,并将老母托在寨中照看。
窦虎郎三人俱是喜悦难当,四人商量了下,决定当天就动身。
尉迟恭老母身体感恙,耐不住跋涉,四人便一起前往车马行,打算雇辆马上载着老妇人。
刚到车马行门口,从中走出几个人来。为首一个身穿青色从八品官服,年约二十八九,面容清癯俊朗,风流而不威严。旁边车马行掌柜落后一步恭敬道:“请县尉老爷放心,小人一定安份做事,不收那来历不明之人做工。”
窦虎郎见对方是个县尉,赶忙侧身让开道路,让他先行。
那县尉走到窦虎郎身边,轻咦了一声,朝尉迟恭问道:“你这汉子,有些眼熟,可是那西城的铁匠?”
“回县尉老爷,小人正是铁匠尉迟恭。”
县尉追问道:“尉迟?北齐时曾有尉迟讳武的将军是你何人?”
尉迟恭肃然道:“正是小人家祖。”
县尉叹道:“令族当年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将,却不料你如今做了铁匠。眼下朝廷东征高句丽,圣上亦许良家子弟从军报国,你既是名门之后,想必身上是有武艺的,何不前往诼郡从军,为圣上效力?或许也能建功立业,重现祖上荣光?”
“小人家中尚有多病老母难舍,小人想要先侍奉老母。”
县尉也不强求,说道:“罢了,既是如此,本尉也不再多言,若是他日你想投军,可来县衙找我,我在军中也有几个相识长辈,可修书一封给你以作鉴身之用。”
窦虎郎心中破口大骂,哪来这么一个二愣子,老子好不容易说服了尉迟恭,你来横插一杠,这不是虎口里夺食么?
窦虎郎心中忐忑,生怕尉迟恭反悔,又不好多言什么。
尉迟恭道:“多谢县尉老爷赏识,日后小人若有投军之念,自当来烦扰老爷。”
县尉点了点头,这才打量到窦虎郎,脱口赞了声:“好一个少年郎君,也是长乐人士么?”
窦虎郎无奈,硬头皮回道:“启禀县尉老爷,小人乃漳南人士,因家中长辈与尉迟叔父相识,今日便来长乐一聚。”
县尉轻哦了声,带着几个衙役转身离去。
他娘的,这二愣子总算走了。
一旁车马行掌柜向尉迟恭抱拳贺道:“老弟今日被房县尉赏识,他日必有出人头地之日,鄙人在此提前祝贺了。”
听及此言,窦虎郎问道:“掌柜的,你说他姓房?”
掌柜的答道:“正是年前刚来本县的房乔房县尉。”
窦虎郎心中狂呼,娘的,这次来长乐县真是来对了,这二愣子竟然就是“房谋杜断”里的房玄龄!
窦虎郎恍恍惚惚跟着掌柜的进了车马行,全然没听进去他们说了什么,心中只是在不断回忆着前世《水浒》里的桥段,合计着怎么把这个房玄龄也赚上山来。
我真是越来越无耻了,不过,这世道,不无耻是不足以逆天的啊,窦虎郎心中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