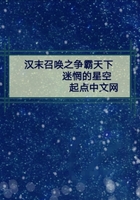长乐县隶属信都郡,人口六七万,乃是一个中县。
前些时日新来了一个姓房的县尉,手段很是凌厉,上任伊始,便革了县衙几个名声颇差的衙役,又领人将县城里一群城狐社鼠以及设套拐人的宵小清扫一空,县衙大狱人满为患,长乐县治安一改前风,颇有几分海晏河清乾坤朗朗之景象。
百姓交口称赞,提起房县尉,人人都竖根大拇指,道一声“青天大老爷”。
这天天色将晚,尉迟恭将最后一个锄头打好挂在墙上,锁上屋门走了出来,沿路几个相识的汉子纷纷打趣道:“铁匠,今天不去耍几下么?”
尉迟恭回笑道:“不了,这几日老娘身子不太爽利,俺要回家照看老娘。”
又一汉子喊道:“那待婶子好转了,你可得再陪哥哥耍两遭,上次被你赢了六十个肉好,哥哥回去好一顿被你嫂子数落。”
另一人哄笑道:“王家嫂子脾气可是不好,怪不得王家哥哥这几日蔫了吧唧,原来是夜里嫂子不让上炕啊!”众人纷纷哄笑起来,那王姓汉子也不恼怒,只是讪笑。
尉迟恭也道:“等俺娘身子骨利索了,俺就再输给王家哥哥一次,好让哥哥回家跟嫂子有个交代。”王姓汉子大喜道:“这么多人可听着了,到时你可不能耍赖不认账。”刚才打趣王家汉子的人驳斥道:“尉迟兄弟嘴里说出的话就是板上钉了钉子,咱们谁不晓得?”
尉迟恭辞别了众人,刚转过一个巷子,只听身后有人吼道:“兀那贼汉子,给老子站住!”
尉迟恭转身看清了来人,也乐了,回骂道:“俺道是谁?原来是你这杀猪汉!怎得,今儿个是来还俺钱的还是来讨打的?”
只听来人恼怒道:“呸!谁他娘的欠你钱了!俺今天是有事来找你了,莫说废话,快带俺去你家坐了,婶子烧的菜可是有日子没吃了,肚子里的虫子都在叫唤了!”
尉迟恭再一打量,发现来人身边跟着两人,其中一个是位少年郎君,只见他年约十五六,高壮挺拔,外穿一件半旧皮毛坎肩,内罩棉布短打,腰间配着一口长刀,更显得英姿勃勃,尉迟恭心里暗喝了个彩。另一人乃是三十出头的大汉,初看其貌不扬,黑如木炭,但仔细瞧便能发现他臂长脚大,站在在那里好似八风不动,也是好一条英雄好汉!
尉迟恭不禁问道:“杀猪汉,这二位是?”
来人也不回答,只是催促道:“先去你家再说。”
尉迟恭不再多问,便在前头带路,行了片刻,到了家中。尉迟恭高声道:“娘,俺回来了,那个杀猪的也来了!”
从屋内迎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面容枯黄削瘦,一张口先咳嗽了几声,道:“我儿回来了,呦,安祖也来了,外面冷,快快进屋里说话。”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从高鸡泊中赶来的窦虎郎、孙安祖、刘黑闼三人,孙安祖见了长辈却不复对尉迟恭的无礼,垂首恭声道:“孙安祖见过婶子,婶子近来身子骨可好?”
窦虎郎和刘黑闼也上前行了礼,只听妇人道:“老毛病了,这些日子又着了风寒,没甚大碍,快些进来,婶子去给你们拾掇几个菜,安祖啊,你可好些日子没来了。”妇人一边端茶倒水,一边说道。
“娘,您身子……”尉迟恭有些担心,妇人摆了摆手道:“不过是着了凉,歇两日便好,你莫要啰嗦,先陪客人说话,娘去烧菜。”
四人分宾主落了座,尉迟恭不由问道:“二位是?”
窦虎郎抱拳一礼:“见过尉迟叔父,小侄窦虎郎,小侄早就听过叔父名号,实在久仰久仰。”尉迟恭心下纳罕,俺有什么大名,值得这位少郎君称呼久仰。这时刘黑闼也道:“在下刘黑闼。”
孙安祖说道:“打铁的,俺老孙知道你为人,便不说些瞎话哄骗于你,这两位一个是俺三弟,一个是俺侄子,如今俱都在高鸡泊落了草,俺如今也是寨里的二当家的。”
尉迟恭一惊:“高鸡泊?俺也听人说过,说是天王窦里正立的寨子,这位少郎君?”
窦虎郎道:“窦里正正是家父,不过如今却不是朝廷的里正了。”
尉迟恭忙道:“原来是窦少当家,失敬失敬。俺来河北这些时日,也多次听人提起窦天王大名,仁义守信、侠名远播,只是未能一见,很是遗憾,今日不料却见到少郎君,幸会!”
孙安祖叹道:“自俺与你上次一别,回转家中,不料失手打死了县令,俺无处可去,便投了俺大哥,承蒙大哥收留,还让俺做了寨里的二当家。”
尉迟恭寻思道这窦少当家的自打进门,便灼灼盯着自己,好似自己是个黄花大闺女似的,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心里暗自怪异,却又不便说出口。
他哪里知道窦虎郎在想些什么?自打昨天听说孙二叔所言之人就是尉迟恭,他心中的兴奋之情,比最初得知自己是窦建德之子来的还要强烈了些。这可是尉迟恭啊,后世家家户户过年门上贴的可是他的画像,怎能不是久仰久仰了?
尉迟恭纯朴忠厚,勇武善战,一生戎马倥偬,这样的人物,窦虎郎怎能放过,他心中打定主意,宁可这次不能外出塞外买马,也要把尉迟恭拉到寨子里。
窦虎郎又不禁感叹,前世看《水浒》里面,宋江每每使计将某某赚上山来,当时自己对此还颇为不耻,觉得宋二黑子忒不地道。等今儿个轮到自己,才发现宋二黑子做的实在正确无比。
此时的窦虎郎早已把李世民当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自是不能错失机会,白白把这绝世猛将送给李二,给李二这猛虎再添一双羽翼,那是傻子才干的事情,他窦虎郎自认跟傻子是绝对不沾边的。
恐怕现在的李二还不知道他被自己给算计了吧?当然后世史书会不会写自己如何拉拢收服尉迟恭,后人读史又会不会也骂自己无耻,这些就不在窦虎郎考虑之中了。
窦虎郎越想越美,不由自主笑出声来,险些流出口水。尉迟恭眼中略带怜悯的看着窦虎郎,又疑惑的看了看孙安祖,心里暗替窦建德可惜,如此英雄人物,怎的有这么痴傻的儿子?
一旁刘黑闼看不下去,轻咳了声,又悄悄用脚踢了窦虎郎一下。窦虎郎才惊醒过来,却不知自己在尉迟恭眼里已经成了一个傻子。
《新夏书·尉迟恭传》记载:尉迟初见帝,大惊曰:此人有龙虎之姿也。复交谈,尉迟深感帝之卓尔见识,为帝之雄才大略所折,遂倾心,纳头拜曰‘愿效犬马之劳也’,自此,尉迟一生忠心事主……”
当然也有野史笔记记载了另一个说法,但世人皆以为乃是无稽之谈不予认同。
孙安祖这大老粗都能感觉出气氛怪异,插话道:“尉迟兄弟,哥哥我这趟来,乃是有事相求。”
尉迟恭虽憨厚,人却不傻,一听这话心里打起鼓来,这孙安祖如今已然从了贼,他找自己能是何事?莫不是要拉自己上山入伙?那可不成,自己还有老娘要照料,怎能去做那杀头的勾当?
于是不动声色,“不知哥哥所求何事?莫不是要我帮你们打些刀枪?”
窦虎郎咳嗽了下,掩饰了刚才的尴尬,出言道:“尉迟叔父,我曾听我家二叔谈起,尉迟叔父之前曾往来塞外,不知可有此事?”
尉迟恭答道:“这却不假,当年俺自己打些铁具,贩往塞外,跟那胡人换得些皮货回转中原贩卖,不料后来得罪了那马邑校尉刘武周,被逼无奈,带着老母来这长乐讨生活,如今已有三年了。”
窦虎郎喜道:“实不相瞒,这次来找尉迟叔父,乃是我高鸡泊中要从塞外购买马匹,苦于没有门路,所以想请尉迟叔父帮忙,事后寨中自有一份心意奉上,不会白白劳动叔父,不知叔父意下如何?”
“这……”尉迟恭不禁沉吟起来。
孙安祖见状也道:“尉迟兄弟,哥哥我在大哥面前可是已经把话说了出去,这才厚着脸皮来相求兄弟,难道兄弟这点面子都不给俺老孙么?”
尉迟恭苦笑道:“哥哥这是说的哪里话?小弟不是不肯,只是往来塞外,一去一回怕是要一两个月才成,家中老母无人照看,小弟着实放心不下呐!”
这时恰好老妇人走了进来,怒斥道:“俺怎么生了你这窝囊惫懒货!你整日间给人打铁,能有得甚么出息?如今安祖求上门来,你还拿俺当做借口!莫是要气死俺老婆子不成!”
尉迟恭慌忙跪下道:“娘,孩儿怎敢?只是孩儿担心娘的身子。”
老妇人又训道:“你且去!俺这老婆子还死不了,不用你来操心!”
窦虎郎一看有戏,忙道:“若是叔父不放心,可将奶奶送与寨中照料,小侄保证,若奶奶少了半根毫毛,叔父拿小侄是问!”他又转头对老妇人道:“奶奶,我寨中有一神医,医术甚是高明,到时可让他给奶奶瞧病,说不得便能妙手回春,让奶奶身子好转起来,您老意下如何?”
孙安祖纳罕,高鸡泊中哪有什么神医?正要开口,却被刘黑闼拉住了衣衫,孙安祖一征,便闭口不言。
老妇人笑道:“如此,便依小哥儿所言,老婆子便去贵处叨扰几日了。”
窦虎郎心花怒放,打定主意,回去就把上次给自己瞧病的郎中“请”到寨子里。
尉迟恭见状,只能无奈道:“罢了,俺答应了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