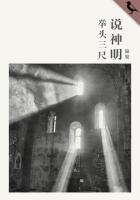我们沿着河流一直往上走,河岸两旁的树越来越茂密,起初河中央还能有阳光渗透进来,但船行了两天后,我们简直是在一条树枝的隧道里穿行,你只要一起身,头顶就能碰到新鲜的叶子。早晨浓雾笼罩河面,河流绿的发黑,头顶的树叶滴着露珠,我常常搞不清楚是否我的头顶正在下雨。说到下雨,我们在第四天的时候碰到一场洪水,萨米亚特说一定是森林上游下暴雨了。河水变得湍急,凶猛异常,我们不得不靠岸。汽笛船随着水面上升,几乎是挂在树枝上,船舱积满水,完全不能住人,我们只好在萨米亚特的带领下,在河岸找到一块高地。森林里到处是细流,我们在高地上扎营,像是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除了莉莉薇安,我们都担心得不得了,即使是萨米亚特也露出阴郁的表情来。他站在高地上的一棵树的枝桠上,忧郁地望着天空。莉莉薇安却格外的兴奋,我猜想那是因为她感觉到家的气息。她光着脚(她还不习惯穿鞋)站在溪水里,全神贯注的注意那些从这些临时的河流里穿行的鲶鱼。一条不知死活的小鱼游过她的光脚丫,她敏捷的将手里削尖的树枝插去,然后就看见那条十英寸的四须鱼活蹦乱跳的离开水面。我赞叹不已。一个下午,她足足抓了十二条。我耐不住好奇,也学着她的样子站在溪水里,手里拿着同样的树枝。这些在阴暗里流淌了一个月的水流冰凉刺骨,我几乎觉得脚趾麻木了。我花了十分钟才渐渐找回脚的感觉。有好几条鲶鱼从我脚边滑过,可惜我一条也不曾插到。莉莉薇安哈哈大笑,第一次像个孩子那样纯粹因为开心笑个不停。她说了一句土著语,可惜我听不懂。我猜想是在叫我诀窍,因为后来她又特意给我做了几回样子。但我依然毫无所获,我猜想我们白人在一千年前把这个技能遗忘了。
洪水到了第三天中午才消退。我们舀干汽笛船里的积水,试着发动引擎,引擎发出一阵欢快的响声,静谧的森林被打破,一大群鸟哗啦啦飞走。我们继续前行,一直到前伐木工人所在的衰败的木屋才停下来。河流变得只有几英尺宽,我们不得不改换步行。在那里我们稍作休整,汽笛船的船员不愿意跟我们接着走,我不得不安排他们在此等我们,并许诺给他们每人200美元的报酬——自然,我姨妈和理查德将担负这笔费用。
傍晚,理查德跟我一起去参观那座约拿·利维坦曾经修建的,现在已经腐朽的教堂。教堂采用随处可见的木材搭建,粗壮的木楔子当时看起来坚固,似乎永不会损坏,但时间是无情的敌人,甚至连上帝也无法跟它对抗。当年那一把火未曾全部毁掉的教堂,如今的却被太阳和暴雨侵蚀,大部分结构都坍塌了,象征耶稣荣耀和牺牲的十字架也倒在一旁,我们这些祂的子民视而不见,更别说有重新把它立起来的愿望。理查德显得兴奋异常,径直领着我来到利维坦曾涂画的那些圣人像前。时间和潮湿侵袭,这些画早已破败不堪,如今只剩下大致的轮廓和一团一团触目惊心的黄色和红色。圣人瞎了眼睛,十字架倒在一旁,背叛的犹大面目全非。理查德发表了一番演说,但我无心去听,这些画显然不如《印第安少女》一样叫人着迷,可是利维坦在画它们的时候必定是怀着巨大的虔诚和恭谦。他希望通过这些拙劣的画将上帝的仁爱传播开来,让那些只能酗酒、赌博、找女人和打破别人脑袋的伐木工从罪恶里拯救,甚至,我不怀疑他也曾感化那些未曾开化的野蛮的土著人。主的荣耀照遍世间,主的福音拯救祂的羔羊。我想这个时期的利维坦一定不负他先知的名字,他是虔诚的,是高尚的,毫无疑问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后来发生了什么?教堂火烧的痕迹历历在目,为什么暴徒要火烧教堂?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枪击?屠杀?或者一个小女孩(就像莉莉薇安那么童真可爱),一个怀孕的女人被侮辱,被杀害?任何一件不起眼的事情都能在这滋生罪恶的地方诱发更多的罪恶。我想象六十年前那场暴乱,我们的神父穿着破烂的圣袍,手里握着十字架,仓惶无助的奔跑劝说,白人的暴民们手里拿着长枪和酒瓶,一抬手把他推搡到路旁;印第安土著脸上涂着恐怖的图腾纹饰,手里是长弓和长矛,他们埋伏在树林、屋顶和寡妇、妓女的房子里,他们眼神冷酷,发誓要报仇。我们可怜的神父能做什么呢?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一团又一团的鲜血染红街道;白人们嚷着“你妈的”、“上帝”、“****”,印第安人则沉默不语,忽然他们一起喊起来,那声音像某种怪鸟交配的声音……暴乱最终以白人的胜利告终,他们丢下十一具尸体,印第安则抱走了所有战死的兄弟;白人们向天鸣枪,口里咬着威士忌酒瓶,妓女们再次打开窗户,把嘴唇和脸腮抹的绯红。长枪、火药和严密的军事部署战胜了野蛮。他们嘟囔着,叫嚣着,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印第安小姑娘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他们不明的还有为什么白人的神父,上帝福音的传播者要站在这些红种人一边。酒精燃烧着他们的智力,“见鬼去吧!”他们嚷着,我们可怜神父辛辛苦苦的教堂在烈火里显得多么无助。他的上帝这一刻鄙弃了他,他怒不可赦,刚刚那一场暴乱的记忆鲜明的印在脑海里,街上的烂泥里还有血迹,神父从一个围观的醉鬼手里拔出手枪——碰,简单而直接,枪口冒着蓝色的烟雾,一个人应声而倒。人群叫嚣起来,神父拔脚就跑。实际上那天,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后面追他,他耳朵里听到的叫喊声不过是恐惧、罪恶、还有被背弃的信仰在他脑袋里幻想出来的假象。
总之,他拼命的逃到丛林里。漫无边际的森林比上帝更加威严,更加让人畏惧。他迷失了,他向上帝忏悔,可惜能听到它忏悔的只有归巢的猫头鹰。他茫然无助,晕倒在河流旁——或者还有一段横生枝节:一头美洲豹静静从背后靠近,神父又累又饿,毫无察觉。美洲豹准备好,恶狠狠的凌空扑来,眼看着要咬断可怜神父的脖子,一只冷箭从背后射来,应声而倒的是美洲豹,猎人瞬间变成猎物,画着被祖先庇佑的纹饰的印第安人从长草间露出半张脸……
第二天我们启程,我、威尔·理查德、里内尔、萨米亚特和莉莉薇安一行五人沿着幽暗的河岸往森林深处走,我们真正走入森林之心。森林像一个活物,静静的张着巨大的口把我们吞没。我想起莎赫扎德那长长故事里的一段:一头巨大的鲸鱼伏在海上,张着巨大的口,海上冒险的船员把这张巨嘴当着隐藏宝藏和公主的山洞(虽然在鲸鱼的鱼腹里确实有珠宝)。森林是比这巨鲸要大上一千倍的怪物,那幽暗的嘴可以吞下一千亿个约拿先知。我心怀恐惧,沉默不语,我开始体验到那种要发疯的念头,每一棵树,每一次声响都像一个怪物靠近,我理解了理查德对什么都要开一枪的理由:我们这些所谓的文明人,丢弃牙齿和爪子,现在我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那冷冰冰的手枪。
第四天,我退去了手枪枪膛里的子弹,里内尔不肯这么干,他担心美洲豹。他眼神已经显出疯狂,我怕我再坚持他就会朝我开枪。莉莉薇安过来拉着我的胳膊,我从她的体温里感受片刻安心。“带着你的小蹄子滚!”里内尔朝我吼,妈的,真应该在他脑壳上来一枪。理查德被森林搞得疲惫不堪,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在心里诅咒男爵夫人。我有意恶意的嘲讽他,他置之不理。我渴望到达莉莉薇安所在的部落,我真希望他的族长父亲给我胸口来一下。我一会儿想象约拿·利维坦在森里里游荡,一会儿又后悔没有带着莉莉薇安一口气跑到东南亚去。我现在有足够的积蓄,我可以跟她两个在海边买一座小房子,我们可以一起游泳,享受太阳和海风。我可以教她用法语给我唱歌,不,我宁愿她用印第安语唱。我真后悔,我该死的,干嘛要来这叫人发疯的地方?我爱她,我要带她走。滚他的约拿·利维坦,滚他的上帝,男爵夫人****去吧!我把最恶毒的话在肚子里翻来覆去的骂,我现在只有想象我跟莉莉薇安两个的将来才能觉得平静和幸福。我真后悔没有带着她走。
第七天,如果今天再到不了莉莉薇安所在的部落,我就把一颗子弹送到自己脑子里去。
那天下午,我就觉得不对劲,头顶忽然有风。我抬头看看,全是树枝和绿的恶心的树叶。我怀疑自己真的疯了。萨米亚特跟莉莉薇安两个不时窃窃私语,我怀疑他们两个土著人终于盘算好要把我这三个白人当着猪一样烤了。我怀疑莉莉薇安原来爱上了沉默不语的萨米亚特,我简直要疯了。我从口袋里第四次掏出子弹又放回去。我跟理查德说柏拉图,跟他说柏拉图是个软蛋。他不理我。然后忽然脸上一阵痛,一枝箭划破我的脸,我喊了一句:“****柏拉图。”十几个印第安人把我们围住,手里拉着短弓。我挣扎着从腰里摸手枪,萨米亚特一拳把我打倒。“好你个萨米亚特……”我没说完,因为我看见我的莉莉薇安扑到一个印第安人怀里。我脑袋清醒过来,我们终于到了莉莉薇安的家,到了森林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