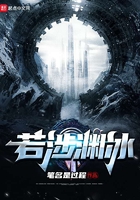理查德似乎有颇多的话要跟我讲,也或者不是跟我,而是跟随便一个可以聊一聊的人表达一下。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到后来我因为思考自己的问题而变得心不在焉,对他多半是不冷不热的敷衍。后来,我们两个礼貌的分手。我将他送到宾馆,因为时间很晚,我以不打扰他休息为由,早早的离开了,甚至没有想到上去看一眼那幅《印第安少女》的相片。
第二天早上,我正考虑是不是要去拜访理查德时,他先过来找到我。我当时正在办公室坐在热辣的阳光里喝第三杯咖啡。
“阳光太厉害了,”他说,“不过才九点钟。”他手里拿了一个摩洛哥皮提包,额头叫这美洲的太阳晒得发红。他一边抹汗一边跟我说。我问他要不要咖啡,他迟疑了几秒钟,后来表示还是喝一点好。“我昨天晚上累极了,可是睡了三个钟头又醒了——被热醒了。不喝点什么热烈的东西大概撑不下去。”
我说:“现在才四月份。真正热的时候还没来呢。”
他咂咂舌表示吃不消。喝完一杯咖啡,他说:“我给你带来了照片。”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一组照片,仔细看起来。
总体来说,理查德在报纸上那篇文章里的表述很到位,没有疏漏,也没有过分夸张。这组照片一共六枚,从各个不同的光照下拍摄的,几乎跟真画一样大小。除了不能亲手触摸颜色干裂后的纹路外,基本上可以看出这幅画的面貌来。画面里的印第安少女站在如同黑色宇宙的背景里,眼睛盯着看她的人——这双眼睛既非含着爱意,也没有任何****,甚至连少女的羞澜或者天真这一类的情绪都不曾表露。但你不能说她是毫无感情的,是像钻石玛瑙那样死寂的美,不,她不是这样的,她是活生生的,你甚至能看见生命在她身上流淌。这蓬勃的生命力让我觉得她好像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永不会消亡。我凝视良久,后来我得出结论,这个少女要么是美和生命本身,要么是邪恶和疯狂本身。我现在可以理解整个纽约为她疯狂的理由了。
我把照片还给理查德,他露出得意的表情,问我的感想。我带着保留意见慎重地说:“是一幅佳作。”
他哈哈大笑两声。“老兄,”他说,“你们英国人这一套并不总是讨人喜欢。老实说,有何感想?”
我叹了口气,直率地说了想法。我说:“这幅画有一种蛊惑人心的疯狂。我以为这不是真正纯粹的美在作怪,就是邪恶本身。”
他哈哈大笑,对我这说法颇赞同。“这幅画不能老盯着看,看久了叫人发疯。我想这也是你姨母没有信心购买这幅画的原因之一:她害怕这幅画。虽然她毫无疑问地赞美这是一副绝世佳作,但似乎这美超过了她能接受的程度。”
我说:“真正纯粹的美跟真正纯粹的邪恶是一样令人恐惧的。人类从蜜与牛奶的黄金国度堕落是人自己的选择,人并不都是喜欢与高尚的东西为伍,大多数人类灵魂的渴望是往下的。”
理查德对此不屑一顾,他嘲笑说:“我不否认人类堕落的欲望,可是这毕竟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上帝在伊甸园里故意放置了这么一颗智慧树,为的就是引诱夏娃堕落。在某些密教里,引诱夏娃堕落的蛇就是上帝本身。这是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没有人会指责堕落。世界造就了巴黎和伦敦,现在纽约肯定会超过这两个。人们口口声声追求美,但那不过是遮掩自己粗鄙无知的幌子。中国有个寓言:某个皇帝非常喜欢神话中的龙,宫殿里的柱子上,墙上,起食饮居的桌子、椅子和餐具上无一不叫人雕刻上龙的风姿。某天,生活在云里的龙终于被这位皇帝感动,特意显身去这位皇帝的宫殿,你猜怎么着——这位皇帝竟然吓得屁滚尿流,呼叫武士把龙赶走。人类对美也是这个态度。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当世不被人称赞的艺术家死后才遭人吹捧——因为他们创造真正的美,人类害怕他们。”
理查德的论调并不新鲜,我想他可能在某一期的文艺评刊上就对此发表过演说,不过尽管如此,在这个南美洲热的让人发昏的早上,能聊一聊这种可以让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文明世界抛弃的话题确实是令人愉快的。这不是苏格拉底的时代,人们现在很少能从纯粹的谈话里得到快乐和真理了。我们的生活被太多的东西诱惑,报刊、女明星、戏剧、花边星闻、一百五十英镑的帽子……太多太多的东西准备随时引诱我们逃避要独立思考的争辩。人们总乐意看评论周刊,像我姨母那样,总是在自己思考之前先观察一下别人的意见——这才是这个世界的大问题:我们都看着别的人生活。我们驻足不前,害怕闹笑话,害怕被人瞧不起,结果是这个世界变得只剩下一种声音了——只剩下那些靠说话、评论为生,不得不被推在前面的评论家的声音。我们的诗人在哪里?我们的哲学家在哪里?
我很有就这些方面探讨下去的欲望,不过理查德不久就恢复了他那强悍的本性,径直撇开一切艺术、美和人类堕落的话题。他不管我的意见,单方面跟我说了他的全盘计划:他打算凭借我在贸易公司的地位,组织一次汽船考察——说白了,就是沿着内河一直往上,到传闻约拿·利维坦最后几年生活的森林去查看一番。“我并不认为我能顺利找到约拿·利维坦遗作,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将肯定能发现点什么。指不定就是你说的——美的本身。”他丝毫不知道丛林的恐怖,用轻松玩笑的口吻跟我说。
我叹了口气,尽量真挚的把里内尔的话捡要点给他复述一遍。我说:“这可不是闹着玩,没有真正去过丛林的人从来不知道它有多可怕。”但理查德主意已定,当即给了我2000美元现金及一张更大数目的支票让我准备,并告诉我早上来之前他已经通过饭店给纽约的男爵夫人拍了电报,电报里称赞我热情的接待和大力帮助,并告知诸事安排妥当。我猜想他是要拿男爵夫人的影响力来迫使我帮忙。不可否认,我今天能在这家贸易公司立足,多多少少是靠了我姨母的那封推荐信。她总是不忘捎带给我提一提当年,我怎么能忘得了?
我只好答应理查德给他找船和向导,但我不保证有人愿意进入丛林深处。他表示感谢,问我说:“你难道没有去看一看约拿·利维坦最后几年做了些什么的欲望吗?”说老实话,我当然对他满怀兴趣。可是目前我对丛林怀有更大的敬意,我不认为我这样一个英国人能得到丛林的欢迎。这些绵延的森林天生是属于美洲豹、麋鹿、犀牛、野猪和在丛林里生活了千百年的印第安部落的。
我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怎么肯定你一定能找到约拿·利维坦?”
理查德回答:“我不能肯定。我手头有的不过是一些零落的、不可靠的资料。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那一份南美伐木公司职员的目击报告。在报告里标明了具体碰到那个跟土著一起生活的白人的位置。你只要给我找一个熟悉丛林的人,我保证能找到那里,说不定,凭借美国人的强悍,我真的能发现当年约拿·利维坦生活的部落。”
“我向上帝起誓,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向导。但是你肯定那些部落会欢迎你?会客客气气的跟你报告约拿·利维坦的事件?我听闻那些土著印第安人可是出了名的喜欢将白人的脑袋作为收藏品。”我怀着小小的恶意开了个玩笑。
理查德哈哈大笑。“美国人的头盖骨没有你们英国人,或者西班牙和荷兰人的漂亮,他们不会对我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