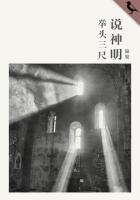一年之中,这座城市究竟失去了多少人,对于活着的人而言,毫无意义。绝大多数活着的人都是绝大多数不存在的人。一个人所能交集的并且拥有清晰图景的人群不会超过一万。
你在你的一生之中认识那么多的人,最后记得的只有那么几个。就像食物,你吃过那么多,可你能够历数的却是那么少。思想难以抵达舌头,这是一条化为缰绳的舌头,在口腔中成了死结。
所以马夫不介意送走这些毫无轻重的人,即便他们的身份与地位昭示了某种年深日久的假象,以为衣冠可以遮蔽虚弱的人体,实则衣冠更加暴露了作为上层人物最为致命的一点,他们的人身即是塑料制品,因为可以大量复制,自然可以大量弃置。
没有一个市长是不可替代的,水龙头常换常新。马夫有生以来已经见过不下百名市长,皆无所长。他几乎认可了所有的官僚都是寄居蟹,社会主义则是大海,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艘巨大的龙船并非驶向海外,它停泊在幻想的口岸,给那些成群结队的壳类繁殖生息的船舱,每个人赖以为生的就是船长提供了一个目的地,目的地不明好过没有目的地,时世艰难至此,每个人等待沉没犹如等待日出。
马夫把照片和光盘交给大丽花,大丽花例行公事般地交给上层,马夫不知道所谓的上层和我们经常听说的“上层”是否属于同一个平面?所谓的“上层建筑”倒是成了佛家所说的“未有第一层,先有第三层”,经济基础只是个幻觉,民主何尝不是如此。面对一个单子,你所能做的亦只是合成,如同堆积沙砾,化为城堡。
真正的意义就是我的意义,不是别人的意义。在他困惑的同时,大丽花曾如此解释,百经注我是一种方便法门。我执而行,一世无明。自己的无明不好过向他人借光么?
就是在我执里,我有我的意义。马夫说道。
一个极好的恐怖主义者,从来不畏惧他所造成的世界会是一个地狱,因为地狱必然是众人皆无所感才成其为地狱,无感即地狱,萨特所说的“他人”,即是因为他人无感,所以地狱存在。
我们不能察觉除了我们自身,尚有别人亦是人身。大丽花说,这是一个佛教徒的教诲,马夫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佛教徒。或许他见到那些手上戴有念珠、珠光宝气的和尚也是,神佛俱在庙中,为何庙门空空,和尚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只在挤兑世人,三十二相皆成白相。
不过,那个给他奇迹的女人曾经也信佛,后来转而信耶稣,因为耶稣允许有一个房间专门用来藏污纳秽。而她认为自己的污秽是与生俱来的,如同她的经血一般,每月都有那么几天要破身而出。
马夫不以为然,人本污秽中来,还本污秽中去。何劳洗心革面,以致面目全非,不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决然迥异,这一个皮囊中有什么是泾渭分明,而不同流合污的?
佛说清净身,是以要杀身。不然怎么豁开,怎么出来?大丽花问他。他自然无由说起,杀身成仁者,未必见仁。只是我们以为他见了,死亡时而消除坏的影响,时而在助长。
像狂信的教徒走向教堂,像严肃而单纯的僧人返回寺庙——我就是这样,在黄昏的、暗淡的幻觉中,百般恭顺,走上布鲁克林桥。
这里没有布鲁克林桥,这只是一座普通的石拱桥,大半的桥面已经粉刷一新,前面与它相连的另一座桥早已失去姓名,人们只叫它南桥,马夫正在俯瞰桥下露出来的石头,曾经有一颗脑袋与它撞击,并且沉没,复而上升,成为星辰,所有人都在为他哭泣,他的作为成了这座桥的一部分,人们开始解说他的作为,他不再是他,一个人只有失去他所仅有的躯体才能获得一个全金属外壳,晋升神祇,以他微小的功德而有零星的香火,甚至一点超乎想象的隐秘的权力。
箫声已经在剑影中歇下,青衣在竹林中歇下,伤口从荧幕中扩散开来,起火的城楼如今化为僵硬的石头,马夫从拥挤的看客中逆流而上,那些尖叫声近乎绝望,其实还有什么人能够深谙绝望呢?目光空洞的人群如同住户空洞的楼群,黑灯瞎火的城市只属于黑夜。
没有人知道火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又在什么地方熄灭?当他们彻夜谈论战争、屠杀以及天意之类的话题,大火已经烧掉了数百平方的货物,只要火舌舔到的东西转眼成熟食,人们在看到那些没有及时逃脱的宠物成了一道美味,散发的香气勾起了消防员的食欲,水枪不停地给大楼降温,仿佛要在这口煮沸的锅里淘冷面,配料就是那些尚未卤过的宠物们。马夫记得荧幕中那支尺八吹送的就是秦火。
今天你够运气,灶王爷没有请你去。大丽花在电话中轻描淡写地说着,其实心底还是有一阵紧张,马夫对她而言,已经不只是一个马夫。而她对于马夫而言,或许还是一朵大丽花而已。
你见过烧熟的鹦鹉么?
大丽花在线的那头,慢慢地构想一只烧熟的鹦鹉会说什么。
它说,要是凤凰就好了,还能重生。马夫说完,挂了电话,他不是凤凰,但他渴望重生,能够记起那些抹去的人们,恢复从前的身份,而不是隐身在无限的黑暗中,成了一个把柄。
如果我们并不需要自由,自由就不会成为口头禅,终日弹跳在嘴上,如同一尾活鱼终日弹跳在砧板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每个人自以为是刀俎,实则成了别人借用的刀俎,对于马夫而言,鱼肉不是名词,如同鱼肉百姓,鱼肉只在与百姓同义的时候才是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