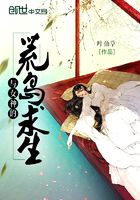一张油光水滑的,面白无须的脸。不是那太监总管陈公公是谁。
此时陈公公的脸上泛起了因激动殷红色,这个太监一直对柳澜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扭曲心态。
既想她死,又想猥亵她。
也正因为陈公公的这种心态,让他错失了刺杀柳澜的良机,反而将自己送进了鬼门关。
陈公公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宫里巡逻的侍卫在南门看到陈公公的时候,他是被吊在宫门上的。
是何杀死了陈公公,又因何要杀了他,而且还吊在宫门上示众。
陈太后惊怒。
二皇子不置可否。
大臣们隔山观火。
最痛快的,却是莫过于宫里长得俊俏的太监和宫女了。
这些人,谁没有被这位得宠的太监总管亵玩过。
但天炎公主与二皇子的成亲大典已定下时日,吉日不可更改,因此陈公公的死便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所有人在议论了几句之后,便又全都投入到了这场旷世大典之中。
天炎国皇宫的婚礼,没有哪一次有这次这般隆重的。
以前虽然也有来合亲的公主,但柳澜是以长公主的身分前来合亲的,再加上那长达数里的送亲队伍以及一百辆马车拉来的嫁妆。
这样的公主出嫁,本身就给自己做出排场,既然使了这一招来漠北救司空寒,司空寒的名下那么多产业,富可敌国,当然做戏做全套,天炎国当然不可能在气势上输给一个女人。
因此,虽然时间短促,却是做足了面子功夫。
祭奠祖庙的仪仗队由三千整齐划一的御林军组成。
白色礼服,白色战马,五彩旗帜,五彩鲜花,一路招摇在通往灵丘山的官道上。
铣钊身穿大红的礼服,骑着一匹通体黝黑的骏马,脸上一派严肃。
似乎比往日多了些威严。只是时不时看一眼身后的轿子,眼神中全是欣喜,方又显示新郎官该有的表情。
柳澜坐在骄中,心中却五味杂呈。自己居然就穿上嫁衣出嫁了,但却是一场盛大而虚假的婚礼,不但假还危险重重。随着骄子的晃悠,柳澜的心也越来越沉。
灵丘山祖庙前的祭祀台上早已摆好了祭拜的炉鼎,炉内香火缭绕,整个广场一派肃穆。
铣刀钊下了马,行至骄前。旁边的宫女掀开帘子,将柳澜从骄中搀了出来。
那一袭红衣艳差点晃花了铣钊的眼。只见他呆愣了半晌后才反应过来,之后便伸手牵了柳澜的手,向着祭祀台走去。
柳澜则因为这一牵手的动作心中产生了更为怪异的感觉。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礼仪的规矩,不敢随意挣脱,但亦没有太过反感。刚才一出骄子看到铣钊时,忽然觉得今天他似乎有些不一样,那眼神不再是前几天所看到的****,而是一种看不懂的深邃。
也许是因为气氛过于凝重吧,柳澜在心底给自己解释。
这不合礼仪的牵手,让祭祀台上的大祭祀皱紧了眉头。
但这人现下是漠北最为尊贵的人,即便是大祭祀也不敢对其多言。只能看着那两个牵着手的红色身影慢慢向自己走来。
祭祀大典开始,大祭祀先告了天地,便开始念祭文。然而令柳澜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念,竟然念了整整一个时辰都还没有结束。
五月的天气,太阳正好,香火缭绕,穿着繁琐的大红礼服,柳澜只感觉得到一个字,那就是——热。
细密的汗珠布满了柳澜的额头,那只被铣钊一直紧紧握着的手更是汗津津的难受。
就在柳澜觉得自己快要晕倒的时候,旁边忽然传来一句低语:
“再坚持一会儿,就快结束了。”
柳澜抬起头来看了铣钊一眼,只见对方仍旧面色严肃地看着前面的大祭祀,似乎刚才的话并非是他所言。柳澜刚想转头云看其它方向,不想那铣钊那只紧抓着她的手忽然捏了她一下,柳澜急忙敛了神情,不敢再往其它地方看去。毕竟整个广场连同后面的官道上,数千人都是静默肃立的,除了大祭祀的声音听不到其它任何的声响。
终于祭奠在柳澜汗湿衣裳和心中骂了无数便该死的太阳的情形下结束了。
但仪式并未因完结。
浩浩荡荡的队伍又沿着刚才来的官道回到了青在皇宫。
天炎宫门前,大殿之上早已张灯结彩,通往宫门的御道上都铺了红毡子。那三千御林军组成的仪仗队打头,之后是铣钊和柳澜的花骄,再后面跟着鼓乐队及迎亲使者,一行人自东门入得宫内,踏上红色地毡,缓缓行至天炎宫前。
陈太后早已居大殿等候了。今天的陈太后虽然一袭华衣锦服美艳无方,但一张脸却寒得如同三九天的冰霜。
本来祭祖大典只能是皇帝自己去的,哪怕是皇后也没有这等特权。
可铣钊却瞒着她将柳澜带了同去,这怎么不叫这个太后怒火中烧。
但即成事实,陈太后也不能在这大婚典礼上发飚,因此只是寒了一张脸,在漠北皇宫中等了三个时辰。
队伍行至大殿前停了下来。
铣钊下马,柳澜落骄。
这次从骄中出来的柳澜则是顶着红色盖头的。司仪女官将红绸的一端递给了铣钊,之后又将另一端塞到柳澜手中,同时还放了一个苹果。一对新人牵着红绸两端缓缓走入大殿。
正使持节,副使捧问名诏书立于大殿两侧,在钦天监官员说“吉时已到”之后,一对新人行了拜堂之礼。
下面文武百官也随之行跪拜之礼,三呼万岁。
之后,司礼官正准备宣布礼成送入洞房之时,大殿外却是一阵喧哗。
“何人在外吵闹?”陈太后此时的脸比之刚才更黑了。
“母后,是我,是我啊!”随着一声高呼,一行人追在一人身后涌了进来。
只见那人衣衫散乱,头发蓬乱,但一张脸却与铣钊一般无异。
“大胆贼人,竟敢冒充王上,给我拉出去砍了!”左相方锦林大喝一声,下面便出来几人预上前拿下这个大婚之日闯天炎殿的人。
“慢着!”
陈太后不等那几个侍卫走近,忽然出声阻止道。她也觉得这几日的铣钊与往常有些不同,但哪里不同又说不出来,但知子莫若母,是真是假这做母亲的是最能一眼看出的。
下面那个才是自己的儿子。
陈太后忽然转头看向一身红衣还拉着红绸的“铣钊”喝道:
“你究竟是何人,冒充王上意欲何为?”
不曾想那“铣钊”并未惊慌,而是忽然大笑出声。
“哈哈哈,冒充王上?谁说我是冒充的,难道下面那人就该是正主不成?”
在这些人说话的时候,柳澜早掀掉了头顶的红盖头,瞪着眼前的情形,柳澜心底那种怪异的感觉更加强烈。某种呼之欲出的答案哽在心里,要出不出。
“你究竟是谁?胆敢冒充我,来人,给我把那贼人绑了,我要抽了他的筋骨,拔了他的皮。”
下面一干大臣侍卫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心中惊骇莫明。
听太后的意思,似乎下面这个才是真的,可这两人站到一处,怎么看都觉得那个穿红衣的更像王上。
“哼!想要我死,你还没有那个资格。”
“铣钊”说着,抬手在脸上一抹,竟然撕下了一张人皮面具来。
“是寒王!”
众人在看到此人真面目后,具都惊呼出声。
“不错,是我!”
“你,你不是被秘密处死了吗,怎么还会站在这里,你究竟是人是鬼。”
铣钊乍见司空寒,惊得噗通一声坐到地上。
“呵呵,死的人当然不可能是我,就凭你还没有那本事要了本王的性命。”
“来人啊,快,快将其拿下!”
铣钊完全沉浸在惊惧之中,嘶声向着身后的人大场吼叫着,哪里还有半天王上甚至皇子的样子。
“御林军何在,寒王谋害先王,罪已查明,快将其拿下,打入天牢。”
陈太后坐在大殿上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气得手脚本发抖,见无人行动只得自己发号施令了。
不久之前寒王束手就擒的一幕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不曾想现在又要同样上演。
人们犹豫了,嗡嗡的议论声响成一片。司空寒见状,向殿外某处轻轻点了点头,数十支暗中待发的箭羽在无声无息中收了回去。
“漠北的众位大人,今天,本王来此只有两件事情要向众位宣布。”
司空寒运起内力,将自己的话语传了开去。
“第一件事,就是先王的遇刺。这件事现已查明真相,罪魁祸首便是我漠北皇族之人。”
“就是你,就是你相夺回王位,才害死了先王。”铣钊从地上爬了起来,又跳又叫。
“带陈六!”司空寒忽然对着殿外朗声说道。
不一会儿,那晚行刺柳澜的陈六就被带了上来。
看到五花大绑的陈六,陈太后的脸色忽然变了。铣钊则指着陈六喊道:
“他是谁?”
“他是谁,你可以问陈太后。”
“母后?你跟他什么关系?”
“哀家如何会认得这等人,来人,把这些闲杂人等都给本宫撵了出去,不要坏了王上今日的成婚大典。”
“太后,恕老臣多嘴,但有一事老臣不甚明白,既然寒王刚才都已言明谋害先王之人现已查明,并将此人带了上来,为何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就此审个清楚,也好让众位大人弄清真相。”
左相方锦林的话即时制止了侍卫的行动。是啊,这件事情本来就透着怪异,上次寒王这所以被擒是因为铣钊拿五皇子的性命相威胁。
虽然事后铣钊向大家解释说这样权益之计,并非真正会伤了五皇子。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还是让很多人都极为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