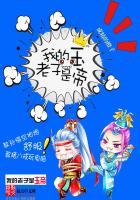一阵柔风拂面,让满脸胡茬的布鲁姆倍感舒适,脸上紧绷的肌肉也松弛了些许。
高耸入云的威利斯大厦的顶端被一群从墨西哥远道而来的候鸟掠过,在经历过一个温暖的冬天后,它们再一次按照原路机械的返回加拿大,年年如此却不知疲倦。楼顶上有鸟类观察学家早早的支起了各种观测仪器,对着天上能飞的任何动物拍个不停。
布鲁姆抬头看了看让这群学者入迷的鸟类,实在想不通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着迷,看了半天索然无趣,转身返回位于大厦顶部的旋转餐厅。
这个餐厅是会员制的,不是本部会员,任你多大身家的老板也只能望门兴叹。拐角处一个安静的四人座位的桌子旁,已经端坐着两个人了。其中的一个人穿着皮衣夹克,让人过目不忘的是他那条银质十字架挂链,本来平淡无奇的挂链尾端有一个长着血盆大口的骷髅头,让人毛骨悚然。单凭这条项链,知道的人能立刻分辨出此人的身份——血帮。
另一个人则看起来更像是满大街泛滥成灾的律师,此刻正抱着牛排大嚼。布鲁姆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了他们的对面,然而这张桌子上的每个人都并没有说话,那个律师模样的家伙连头都不抬,依然贪婪的啃着泛着血丝的牛排,看样子好几天没吃饭了似的。布鲁姆玩着自己的打火机,皮衣男则不动声色的看着布鲁姆,桌子上整整一分半钟没人打破这种宁静。
“布鲁姆,你把我们叫来,你倒是说话啊,我们来着不是看你玩打火机的。”吃饭的人率先打破了僵局,他擦了擦嘴,大口的喝着一杯果汁。
布鲁姆没说先笑了起来,看了看对面两个人,意味深长的道:“尼科洛夫斯基的运输线我给他停了,上头对他很不满意,谁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不按照规矩胡来,包括俄罗斯人。”他点了根雪茄,狠狠的抽了几口:“另外,我侄子的事你们都知道了吧。”
律师模样的人其实和律师没半点沾边,他是意大利在芝加哥黑手党的头目,和血帮一样,世界大大小小的帮会社党都想来这个美国第三大城市分享繁荣带来的利益,哪怕是不正当的手段。
“听着,不管是谁,只要能找到杀害考克莱的人,并干掉他,尼科洛夫斯基的这条南美路线就让给谁做,只是每个月多加二十万美金的月税,其他规矩不变。”
气氛一下活跃起来,血帮成员的眼睛都亮了。他坐直了身体,胳膊放在桌子上,凑近了布鲁姆:“为什么你不亲自动手呢,布鲁姆?”
“你的大脑是否还未发育完全?”布鲁姆嘲讽的看着对方:“一个警察去杀人,也太耸人听闻了吧?我可不想这么快就上芝加哥电视网的头版头条。”
皮衣男还未说话,意大利头目笑了:“你又不是没杀过,上次你朝那个墨西哥男孩连射了八发子弹,可是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的。”
布鲁姆的眉头一皱,杀人时没有皱眉,这时候居然皱了,颇为讽刺的意味:“老皮克,上次的事是因为墨西哥人杀了我们一个警探,说好尽量不杀警察的,是他们先把事情搞大,差点让我也曝光,我才这么做的,这么久了,你倒比我记性还好?”
“事情不会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吧,布鲁姆。据我所知,韩国人也被纠缠其中了,所以你才找我们俩,对吧,哈哈,你真是条老狐狸。”老皮克骂别人狐狸,自己却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布鲁姆的心事被无情的看穿了,可脸上依然波澜不惊。城府之深令人叹为观止,一般来说,不是经过类似于特工那种特殊训练的人,遇到任何能够使自己内心波动的事情都会或多或少的露出点破绽,有的是在行为上或者语言上,但更多的莫过于表情,因为你的眼睛是不会欺骗你的。这个心灵的窗户是让别人透知你内心的最为主要的途径。当我们看一个人的眼睛时,通常都会读出很多信息,有爱慕,有欣喜,有伤悲,有无助。可当皮衣男和老皮克盯着布鲁姆的眼睛时,愣是读不出任何有用的资料,布鲁姆只是自顾自的抽着雪茄,眼神没有出现哪怕是丝毫的慌乱,满脸的自信洒脱。
“好吧,看来你是对这条运输线没什么兴趣了,你呢?”他手里的雪茄指了指皮衣男:“有兴趣的话可以谈谈,如果和老皮克一样,我认为今天的午餐时间到了。”
“哈哈,用不着这样我的朋友,我可没说对俄罗斯的线路没兴趣,韩国人嘛,不也是图钱吗?我觉得咱们应该认真的谈谈具体问题,你说呢?”老皮克收起了狡黠,摆出了一副颇为真诚的表情。
胜利者最终还是布鲁姆,现在该轮到他笑了。他深吸了一口,吐出了一个浓浓的烟圈,烟圈在昏暗的灯光中半天凝聚不散,像被人施了魔法,悬挂在半空做出各种诡异的形状。
张东赫,没有你,我照样可以在芝加哥找到替代品!
被蓝色的海水环绕着如翡翠般的西雅图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
它海拔最低,却有古老的冰川,活跃的火山和终年积雪的山峰。西雅图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它拥有青山、湖泊,拥有港湾河道,拥有温润的气候,如春的四季。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像西雅图那样,山峦、平地都被密密的、几近原始的森林所覆盖。市区内外皆衬饰着幽静的港湾、河流、绿树,掩映着色彩丰富的街市。而在环绕着城市的青山之中,又错落地隐藏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湖泊。树木葱郁,草地青葱,甚至飘来飘去的雨,轻轻掠过的风,都带着青绿的颜色。西雅图市筑于丘陵地形上,一些市内最高的地方直接建在市中心附近。通过不同的地形改造工程市中心附近的地形被改变许多。恨不得世界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在西雅图都能找到,当然——除了沙漠。
刚下了飞机的何楚芳身边站着抱着受气包的糖豆儿。西雅图靠近加拿大,所以这时候的气温并不像芝加哥那样温暖,何楚芳给孩子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看起来胖乎乎的可爱。她看了看接机口的人群,并没有发现亚当斯的身影。想找i个地方那个休息下,可又怕亚当斯看不见他们。正值踌躇间,满头大汗的亚当斯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喘着:“对不起,我迟到了。你看,我总是把事情搞糟,难怪法官剥夺我的探视权。”
一脸的沮丧和歉意,让心里有点火的何楚芳倒是发不出来了,笑了笑:“没事,我们也刚到二十分钟。”
亚当斯心里歉疚顿生,他一把抱起糖豆儿,拉着何楚芳手里的行李转身就去停车场。
在停车场,糖豆儿一眼看见了飞在远空的大雁,大叫起来:“鸟!鸟!”
何楚芳抬头看见那群大雁拍着整齐的队伍从头顶缓缓飞过的同时,也看见了大雁身后的云层。它正在被阳光照射下慢慢撕裂,虽然很厚,但阳光的穿透力似乎更强。只要有一丝空隙,就能射出一道耀眼的强光,直通地面,就像一把锋利异常的手术刀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