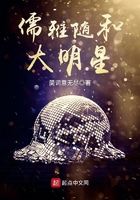李存良走了,走的时候所有人到机场送行,范风精心准备了礼物,那是本精装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老师笑笑收下了,毕竟文化人出身,送书最合适,谁也说不出什么来。程前走上前去,打开了李存良手里的书,翻到了某一页时,李老师的内心狂喜起来,从他眉头的舒展程度可以确认,因为那是一张整整十万美元的支票。
好像国内的人到哪都忘不了潜规则,不正常的事情得用,用习惯了以后,养成了惯性,正常的事情也下意识的得用。当李存良看见支票时,连客气都没客气,就直接放到衬衣内兜了。在登机口,他拉着箱子回头对群人摆手说道:“江湖不远,来日方长!”
说实话,其实李存良这种人还是受欢迎的,他不像那种收了好处不办事的,这种是最可恨的,吃别人的还特理直气壮。李存良虽然是个伪君子,但那也办实事的伪君子,比起国内那帮吃人不吐骨头的那帮人强的太多了。虽然在人品上李存良有些瑕疵,但那是人性使然,你范风程前难道高在哪了?并没有。相比较而言,与其做美国人那种虽然公开透明,但对方一个个锱铢必较都跟法律专家似的,他宁愿找李存良这样的做的爽快。吃点喝点算什么?住总统套又算什么?你美国人都是自己坐飞机来,可转了半天一个大子也没砸下就跑了,费劲扒拉的几个月下来,还不如中国过来一个团的销量。也亏的美国妄称自己是市场经济的鼻祖,不不如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见效快,效率之低下,令人发指。
办公室里,张素英和魏清在电脑旁飞快的敲打着键盘,范风手扶着素英肩膀,盯着电脑屏幕大气也不敢出。
“到了!到了!钱到了帐头上了!”
看到一连串滚动的数字,范风像羊癫疯患者一样,浑身的肌肉不停的颤抖着,他狠狠的亲了素英的脸颊,这一下太突然了,把素英搞了个措手不及,脸又红了起来。屋子内的所有人包括轮椅上的魏清,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兴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价值一千多万的数字,而且这只是房款的一半。
三年前刚到美国洗车的范风,何曾想过自己还会有这么一天。别说赚什么大钱了,当初的初衷是能有口饭吃,站稳脚就是烧高香了,毕竟这是和国内完全不同制度的美国。可就这么阴差阳错的结识了张素英,又误撞误打的闯进了韩国的黑帮,最后鬼使神差的认识了机灵鬼程前,一切好像是在做梦吧,范风掐了掐自己的手,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这是真的!眼前的数字都是真实的!范风拉起张素英,一把紧紧的抱住,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用尽全力的抱着。往昔的一切景象出现在眼前,在家中的无奈,事业的无助,父母殷切的目光和背影都一一浮现。
忽然泪水滴在张素英的肩上,他哽咽的说道:“这是不是就是美国梦。我要给我爸妈打个电话,就现在。”
所谓美国梦,就是在美国怎么样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仅此而已。
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内,糖豆儿被妈妈牵着手走在明媚的春风里。上个月从迈阿密回来后,何楚芳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她一边带着孩子,一边还要不停的应付设计公司的催促,忙的焦头烂额,毕竟单亲妈妈这个活不是谁都能干的了的。和去迈阿密之前的心境有所不同的是,倒霉鬼亚当斯的经历让她感触颇深。人与人的相同之处大概都是因为应付,但不同仅在于痛苦的程度不同而已,自己好歹还有糖豆儿在身边,可亚当斯只能拥抱自己,这一点上,亚当斯更惨。这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
电话响了起来,天哪!居然是亚当斯!
怎么连电话都会猜测人心了?想什么来什么!
何楚芳接通了电话,那头的亚当斯非常直接,直接的不容何楚芳喘息:“何,我现在就站在你家门口,我想见你。”
整整一分钟何楚芳没说出话来。她有点后悔接这个电话,但心里又好像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电话,她不知道见了亚当斯她能说点什么,而这一切又将给糖豆儿带来什么?她低头看了看吃着棒棒糖的糖豆儿,那根快吃完的棒棒糖是个小兔子形状的,一对耳朵已经不见了,剩下胖乎乎的肚子和短爪在日光下闪闪发亮。
加勒比海北部,像大海伸出了一只长长的触角,在触角的顶端就是墨西哥的坎昆。尤卡坦半岛东北端海滨,是一座长21公里、宽仅400米的美丽岛屿。整个岛呈蛇形,西北端和西南端有大桥与尤卡坦半岛相连。隔尤卡坦海峡与古巴岛遥遥相对。玛雅语中,“坎昆“意为“挂在彩虹一端的瓦罐“,被认为是欢乐和幸福的象征,坎昆也因此而得名。
这里的气候既有雨季,也有旱季,算是两个极端。七到十月份是雨季,几乎天天下雨,除此之外就是旱季,常年平决气温都在27摄氏度左右,偏热一点,还算温和宜人。这座城市三面临海,风景柔美,古玛雅文明的建筑图论遗址就坐落在这里,每年都有极多的游客慕名而来,而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个不是抱着旅行的目的的。
贝拉的腿上坐着一个骨瘦粼粼的男孩,深陷的脸颊说明了他属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孩子没有穿鞋,至穿着条短裤,黝黑的皮肤看被汗水覆盖。贝拉拿着手里的饼干,一口口的喂着男孩,男孩接过来就吃,并没有说话,无神的目光并没有被食物所吸引,只是机械的吞咽。按说墨西哥的经济发展还不至于产生如此众多的孤儿,但毒品泛滥的墨西哥,每年因吸毒死亡的人数就有几万人,由此产生的孤儿更是翻上一番,不得已没人领养的最后只能进了孤儿院。这是一个被上帝遗忘了的化外之地,没有母爱父爱,没有欢乐的童年,没有圣诞节和万圣节,有的只是生存和挣扎。当贝拉第一眼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脚步就再也迈不动了。她留了下来,每天帮助社工照顾院里的孩子,没有薪水,她自己唱歌卖艺,还在晚上的一间酒吧兼职做服务生,这样清苦的日子却让她乐在其中。
贝拉把最后一块饼干放到男孩手上,她轻轻放下孩子占了起来,活动了下四肢,看着远方白茫茫的海岸线,平静的就像是静态的画布,根本不像是澎湃的加勒比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