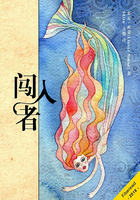见王政君冷静下来,公孙夫人道:“太后还有一事值得一提,方才掖庭狱来过,呈上陛下的御箭,说查得陛下昨儿回城时在城外射杀了看门侍卫,无一幸存。”
“骜儿为何杀人?”王政君刚理清的思路转瞬间又乱了套,看门侍卫不是敌人,更不是猎场上的畜牲,骜儿为什么要杀他们。
公孙夫人:“许是他们做了让陛下不顺心的事。”
王政君:“蠢奴才,什么事非得拼了命也要逆骜儿意思。”
公孙夫人:“陛下没留下一个活口,是不是侍卫知道了什么秘密,陛下要杀人灭口。”
王政君无奈的仰望着天际,今天是阴天,天空很矮亦很朦胧,如今刘骜的心思一如这云层,她拨开一层还是一层,怕是有生之年再也看不透他在想什么了。
王政君叹息了口气吩咐道:“传燕赤凤。”
“是。”
刘骜昨晚入甘泉宫后遣散了所有宫人,当即宣来郑太医替不古拔箭疗伤。刘骜从小到大的疾病都是郑太医亲手诊治。郑太医幽默风趣,一不涉政,二不理皇帝家事,只喜欢给刘骜讲故事,说说闲话。刘骜待他如父,信赖无疑。王政君也知他俩关系好,曾几次召见郑太医企图想从他嘴里获知骜儿一二,然郑太医总只字不提,转了个弯就给王政君讲起了故事,逗得她喜笑颜开。
郑太医告之刘骜不古并无大碍,箭不伤及要害,但她气血亏欠,怕是要睡上两天才能醒过来。郑大夫开了药方子后离开。刘骜看她气息恢复匀畅才稍微轻了口气,亲自给她轻轻擦洗身上的淤泥。看着她双腿上满是磕磕绊绊的淤青,刘骜心里不禁心寒。
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宁可搭上性命;为什么穿着乞丐的衣裳,难道放着娘娘高枕无忧的位置不做偏要上街讨饭,无论关乎他皇室的尊严还是她自己的尊严,他都绝对不允许。
刘骜给她换上件干净的衣裳,静静坐在床沿凝着她,而外殿传来常乐一声苦怨的惨叫,刘骜才转移目标去惩戒常乐,他已经把常乐倒吊了一个晚上了。
刘骜移步到常乐跟前,勃然大怒:“常乐啊常乐,朕可真是小瞧你,居然敢给太后通风报信!九鸾一畜牲尚且对朕忠心耿耿,你禽兽都不如。”
常乐被揍得全身是伤,只留一张脸皮是好好的。“奴才,再,再也不敢了……”
揍了常乐一顿后刘骜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常乐是陪他一块长大的,如今却成母后的眼线,他怎能泄愤。“吃里扒外的东西,养九鸾都比养你值!”
起码人家九鸾还会骑母马!
刘骜是他主子,王政君是主子他娘,命是皇家给的,岂能由自己做主。常乐欲哭无泪,他何尝不想做一只性自由的畜牲……常乐被折磨得快要断气,憋红的脸如喝醉酒。
刘骜手里打旋着箭支,威胁道:“知道在太后面前说什么了吗?”
常乐:“知……知道,说皇上日理万机、勤政爱民。”
刘骜懊恼的掌了常乐一记耳光,“说人话。”
常乐立马改口:“皇上宠爱赵昭仪,留宿甘泉宫。”
刘骜:“可以说得再细腻一点。”
常乐快要崩溃,竭斯底里大喊:“赵昭仪伺候陛下累倒在床上了!”
“中!”刘骜把常乐解下来,把弓箭塞进常乐手里,冷冷的命令道:“射朕。”
常乐被吓出眼泪,忙把弓箭扔掉,慌慌张张:“奴……奴才不敢弑君呀。”
“蠢材,”刘骜指着自己肩膀,“射这里,亮你也不敢弑君。”
果不其然,第二天常乐就被王政君暗里传召过去。王政君在竹园深处的小席上悠闲的闭目饮茶,神气不怒而威,不咸不淡的问道:“赵昭仪在甘泉宫可还安分?”
常乐跪着身苦不堪言,全身的酸痛在警告他要慎言。常乐畏畏缩缩,脸色发青,话语都干巴巴,“赵昭仪,安分。”
常乐的胆小王政君是见惯了的,所以不感觉异常。胆小的人好使,肯说实话。王政君轻视的瞄他一眼,质疑问:“噢?孤听说她迷惑皇帝,又怎么个安分法?”
常乐抿了抿嘴,吞吞吐吐道:“赵……赵昭仪晚上都,都累坏了,所,所以白天安分熟睡不醒。”
“混账,”王政君彻底被常乐的无邪击败,一杯烫烫的茶水泼到常乐脸上。“你怎么不劝劝皇帝。”
常乐被烫得轻呼了一声,连忙拿衣袖把茶水擦干。“陛下说奴才一个阉人不配在那事儿上说话。”
本觉跟骜儿说话幼稚,没想到跟常乐说话更是“自不量力”。王政君隐忍咽了一口气,“那甘泉宫里除了皇帝和赵昭仪,还有谁?”王政君本是想问他可见着麟儿。
“有常乐。”
王政君竟哑口无言以对,凶凶的瞪了常乐一眼,吓得常乐脑袋缩得更紧。不过听他的回答,八成麟儿是不见。可麟儿若是失踪,骜儿岂有心思行乐?若麟儿没有失踪,那去了哪儿?真相只有一个,是骜儿骗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