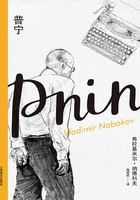苏沫笑她:“结婚又不是热恋,我现在和佟瑞安还不是一样,整天见不着面,见了面也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还有孩子。你放心,等有了孩子,你根本没空搭理他,”说罢,又赞了句,“周小全说得对,你老公还真不错,特别是穿白大褂的时候,那气质……男人还是要看气质,其次身高,最后长相。”
涂苒说:“要是太挫,我找他做什么,还不是想改造一下我们家的基因。”
苏沫点着她,又是笑:“你这样的还有改造的必要么?”想也没想,又说,“我孩子的主治医生,就是上次那个姓李的,漂亮吧,对她有意思真不少,我这几天就撞上了好几个。”
涂苒逗孩子:“人有才有貌,行情当然好。”
苏沫叹道:“是呀,职业也好,说出去都好听。哪像我这样的,这么多年要死不活的在中学里歪着,做做可有可无的副课老师,管管机房钥匙……”
每每说起这些,苏沫就不由委顿,职业和收入一直是她心里的刺,人在江湖混,最怕人比人,虽姻缘和美,良婿在侧,下有娇女,见着事业上风生水起的同龄人,却不免心生羡慕。她原本轻视名利随遇而安,秉持家庭和美身体健康才是人生的大事,何况婚后很快就有了孩子,更没心思和精力用于职场拼搏。
可是她的淡泊在别人看来却是没有出息,这个别人便是佟瑞安的妈。
佟老太是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教育下走出来的要强女性,此时又身处高校大院清净地,周遭都是书香门第或者名门之后,个个混得如鱼得水,只有佟家除外。
佟老太的丈夫佟教授,学术派高人,公关系低手,院士评选时硬生生被人夺了位置。
佟老太有两儿子,老大为人虚浮不是读书做事业的材料,老二甚好,学问好模样好人品好,却偏偏找了个没人脉各方面还拖后腿的外地老婆:学历一般不擅言辞,性格绵软近似窝囊,不思进取糊涂度日……老太太一生心高气傲,如何甘愿,只是无可奈何儿子的选择。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如眼不见心不烦,偏生又多了个孙女出来给她带,不带吧又怕小儿子有意见,影响母子关系,带了吧,心里又不喜欢,什么样的女人生什么样的孩子,想来想去,怎么都不喜欢。
好在老太为人圆滑,从不当人说重话,再不济也是含沙射影一番。
比如说看见隔壁家的媳妇,就状似无意中提起:他家儿子也不怎么出息,好在有个能干媳妇,也是中学老师,教英语的,学生家长请她补课,都是好车接送。
又或者:谁谁家的女儿学成归国,在北京的一家银行做事,年薪数十万。以前她父母还打听过我家小二的情况来着,可惜小二已经谈上了。
最次的:咱家大媳妇虽然学历也不高,却是男人性格,自己做生意能赚钱。
苏沫也不是傻子,对比自己每月一千出头的薪资,心下黯然,只是她的性格极为隐忍,并不反驳,顶多抓住佟瑞安发一顿脾气,也就过去了。
这会儿她和涂苒走得近些,难免为这事向朋友倾诉几句。
涂苒笑道:“苏沫,其实你这人也心高气傲,只是被环境给困住了。”
苏沫听了连连摇头:“我如果真是,就不会混成这样了。”
涂苒说:“你如果不是,怎么会拿你婆婆的激将法当回事?你这是人心不足。就说那位李医生,人条件再好也奔三了,指不定还羡慕你夫怜子孝人生圆满。个人总有个人的不满,对自己这样,对别人更是这样。你若阳春白雪,人谓你曲高合寡,你若下里巴人,人又笑你无锦衣华服,如今这年月,人人只爱锦衣华服,殊不知你心中高洁尤胜锦衣华服。所以呀,如果你只围绕别人的思维打转儿,又怎能安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呢?”
苏沫听了不觉点头:“人人只爱锦衣华服,殊不知你心中高洁尤胜锦衣华服——你的女文青范儿又出来了。”
涂苒笑:“这句话只适合你,不适合我,你生性纯良,我是比不上的。”
两人低声交谈,正是投入,冷不防听见对面一人大声说:“老张,你家孙子今天怎么没给药?”两人抬头瞧过去,那一声五十来岁年纪,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看言行就知道,是个快言快语,爽朗直率的人物。
老张面露难色:“陆教授,我存的钱不够用,才打电话去找朋友借了,现在还没到帐。”
陆教授说:“这孩子的情况现在不太好,所以一天药也不能停,咱们先得把这哮喘的问题暂时压制了,才能考虑后面心脏方面的大事,我给你开的药已经是最便宜的,你不是才打了钱进去,这么快就没了?”
老张说:“前天做了些检查,花了些,昨天护士长来说,钱完了就停药,这药是昨天就停了,娃儿一晚上没睡,不舒服,哼了一夜。”
老教授忍不住骂道:“说停就停,都钻钱眼里去了,这样,我先给你垫两千块,先把孩子的药续上再说。”
老张半天没吭气,一会儿用手抹了抹眼睛,点头道谢。
苏沫小声说:“这老教授人真好,听说是专攻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
涂苒点头:“才说了心中高洁尤胜锦衣华服,我等皆是一身铜臭味徒重欲望的俗物。”
生活里的许多事儿,发生之前都有预兆,当时不觉,过后想起来,才恍然。
两天后,涂苒傍晚回家,人多车少,不得以拦了辆出租。
这次遇到的司机相当健谈,一路上絮絮叨叨的埋怨路况,工作辛苦,油价飙升,乘客不谅解,家人不理解,孩子不学好老师搞孤立。
窗外是一拨一拨等候公车的人潮,疲倦阴沉,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一切喧嚣杂乱不绝于耳,每个人都在焦躁中渐渐丧失了耐心。
涂苒的思维在这时有些放空,大约是前方的家永远一层不变使她心生倦意,在到达之时,只会有洞黑的窗口以及冷锅冷灶等着她,毫无生气。
猝不及防,几句话从收音机里钻进她的耳朵。
起初是“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着是“心外科”,再是“一位陆姓主任医师”……,这几个词出现在本地新闻里已经让她相当讶异,继续听下去,却如当头一棒:“于昨晚在医院里散步时被疾驰的车辆撞倒,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
涂苒顿觉手脚发软,耳朵里嗡嗡直响,一时间竟然想不起陆程禹有没有心脏病,啥时候评上的主任医师,昨晚是否值班还是呆在家里……她的记忆在突袭之下乱轰轰揪成一团,末了又想,这是在播报新闻还是在讲故事呢。
迷糊间,司机在一旁讥诮道:“这年头也真是啊,自家门口走几步也会出车祸,背运啊,老天爷要收人……”
涂苒猛的转过脸去看着他,倒把那人吓了一跳,然后她细细索索的说了句:“我,我要去同济。”
涂苒下车后一路小跑,晚饭还没吃,低血糖又犯,浑身不得力,惨白着一张脸,眼神儿游移不定。
路上也没见着个熟人,电话依旧打不通,她越往前走越是脚软虚脱,终于到了外科住院部的前台,看见一位伏案工作的护士,便忐忑不安地上前询问:“你好,请问今天是陆程禹陆医生值班吗?”
那小护士抬头来打量她一眼:“来推药的?别忙活了,陆医生不理这些事的。”
涂苒一愣,正要说话,却听见旁边有人笑道:“小胡,你弄错了,”说话的是位年轻医生,上次跟着陆程禹查房,和涂苒有过一面之缘。
那年轻人看起来既疲倦又忙碌,一边赶着手里的报告一边对涂苒说:“要不您去阳台上看看,陆医生可能在那儿休息,今天够忙的,这一整天,也就这会儿才能歇口气……”
涂苒赶紧道谢,心里总算松散下来,在走道上倚着墙边站了会儿,顿时觉得自己犯浑:其一,凭他现在的年资,最多是个副高,不可能到主任级别。其二,他一向生龙活虎怎么可能隐匿心脏方面的疾病。其三……
阳台在走道顶头,靠左手边上,对面就是电梯和楼梯间,中间隔着一大扇窗户,先前她心里着急,也没注意,这会儿才慢慢走过去,稍微往外头瞧了眼,就瞧见了那人。
他正静静地坐在长椅上,手里拿了瓶矿泉水,却是没喝,只是就着半明半暗的霞光,凝望远方,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涂苒犹豫了一下,转身往右走,伸手按亮了电梯开关。
紧闭的电梯门照出她模糊的身影,看起来有气无力没精打采,原本绾在脑后的长发微微松落,几缕乌丝垂在脸侧,身上的裙装有数处皱痕,手里还拎着一大只“麦德龙”购物袋。
她不觉冲着镜子里的人拌了个鬼脸,想起以前做药代那会儿,打扮可比现在这样讲究,也不会拎着超市里的购物袋满街跑。
购物袋也旧了,还是她第一次去“麦德龙”的时候,花一块钱买的,结实耐用,她习惯将袋子折成小小的三角形塞在皮包角落里,以备不时之需。
袋子很大,简直要垂到地上,这使她看起来更滑稽,好在里面装的东西并不多,全麦面包,一小盒牛油,两盒切片奶酪,萨拉米片肠,再加上一袋小熊软糖。
除了软糖,其它都是陆程禹让买的。
他在饮食方面并无的挑剔,就是对早餐有点要求,以前吃中式的总觉得热量不足,工作繁忙又消耗体能,不等中午就饿了,后来出国一阵子,觉得全麦面包抹上黄油夹几片奶酪火腿相当顶事,做起来又省时省力,所以这个习惯延续至今。
过了一会儿,先前指路的小医生怀揣着饭盒小步跑出来,见涂苒在等电梯,于是问她:“您找着陆医生了吗?”
涂苒对他笑了笑,就见陆程禹已经打外面进来,问那小年轻:“报告写完了?”
小年轻答:“写完了,在您桌上。”
陆程禹微一点头,这才看向涂苒:“怎么这会儿来了?”
涂苒说:“我来看看苏沫家孩子好些没。”
“儿科在楼下,”他想了想,又道,“她们不是昨天已经出院了吗?”
“是吗?苏沫没和我说,”她停了一会儿,又问,“吃饭了吗?”
“还没。”
涂苒把购物袋递给他:“要不先吃这个垫垫肚子?”
陆程禹往袋子里瞧了瞧:“也好。”
两人去阳台,涂苒把购物袋铺在长椅上,掏出湿纸巾给他,又指了指他手里的水瓶:“口干,借我喝点。”
从他手里接过瓶子,却是怎么也拧不开瓶盖,只好递还回去。
陆程禹动作很麻利,在帮她拧开瓶盖之前,已经在两片面包间搁上了奶酪火腿片,然后放到她手里。
涂苒喝着水,皱眉:“我不要,我已经吃过了,”她一直吃不惯黑面包,嫌它酸涩干硬,几乎到了难以下咽的程度,但也不会忘记替他补给食物,可是这几样东西只在一家超市有售,她每去一次几乎要横跨大半个城市,若是下班后才去,哪里能腾出时间吃晚饭。
几个月相处下来,不得不承认,她是一名称职的主妇,至少超出他的预想。
涂苒早饿了,想去拿小熊糖,动作又比他慢了半拍。
陆程禹把糖塞回袋子,再次把面包递到她跟前,坚持道:“尝一点,并不是那样难吃,对身体好。”
涂苒拗不过他,无法,只好捧在手里一小口一小口的咬,慢吞吞的嚼咽。
天已经黑了。
这座城市最近干燥风大浮尘也多,四周又有光线污染,却还能隐约看见几颗星光,天边那只月亮既不圆润也无神采,但是涂苒依旧盯着它发了会儿呆,见不着的时候往往想不起来,见着了又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不停地猜想它的反面会是什么模样。
她累了,便不想说话,不多时,一份三明治竟然啃去了大半,剩下的那点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下,于是随手往旁边一搁,搁在陆程禹的手上。
陆程禹才吃完一份,这会儿又接着吃起来。她记得他排班到明天早晨,嘴里还是问了句:“几点下班?”
陆程禹说:“明天早上,然后去参加同事的追悼会,大概下午才回去。”
涂苒这才想起来:“出车祸的医生也是你们科室的?”
“不是,呼吸内科的一位老医生,”他又问,“你怎么知道这事的?”
“新闻里说的,好像姓陆。”
他点点头:“你应该见过陆教授,就是前几天会诊的时候,在儿科重症监护室里帮人垫钱的那位。”
涂苒不由吃惊的张了张嘴,半响才说:“真没想到。”
陆程禹“嗯”了一声:“我以前在呼吸内科轮转的时候,就是他老人家给带的。”
涂苒沉默片刻,才问:“肇事车辆抓着了?”
“抓着了又能怎样……”
两人一时都没说话。
陆程禹轻轻拍去手里的面包屑,站起身来:“好了,我也该开工了。”
涂苒跟着站起来,走过去,张开手臂将他抱了一下,这么做的时候她的内心有些不确定,仓促间,脑袋碰到他的下颌。
他一低头,气息淡淡的拂过她的脸颊,停顿稍许,说:“早点回去吧。”
涂苒觉得他应该继续做点什么,或者自己再主动点,就像其他小夫妻那样,相互间有更多默契用以维持某些亲昵却不张扬的习惯性的小动作,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如同往湖里扔了颗石子,石子咕咚咕咚缓缓下沉,那水像是深不见底。
她松开手,收拾好长椅上的物品,陆程禹已经走进里间,路过走廊尽头时,他顺手把紧闭的窗户推开了点,便向值班室去了。走道顶端的灯只把室内照亮如同白昼,他的背影和周遭环境毫无间隙的慢慢吻合,愈加坚硬和疏离。
涂苒等着电梯,室内空气有些混沌,她往窗口站了站,有风缓缓吹动她的头发。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她便是在这里,怀着某种侥幸心理鼓起万分勇气,对他提出缔结婚姻的暗示,那会儿,他给人的感觉也是这般疏离。
涂苒想,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会不会像对待工作一样,投入饱满的热情,在另一个人身边享受着爱情。
电梯门开,涂苒走进去,抬手看了眼腕上的表,时间还早,又想到家里的老太太托她买药的事,于是决定回去瞧瞧。
老太太虽说高龄,身体一直还算硬朗,只是有些血压高和关节痛,一直以来坚持服用的药物也不过是维他命C和维生素B6,涂苒从不觉得这些药物有何作用,老太太却将此当命根子一样看待,把小药瓶儿常备在枕头边,一天也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