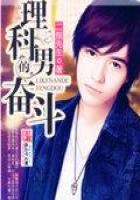因为我是村上春树小说的热衷读者,常常向往书里的那些图书馆。无论是《海边卡夫卡》里的甲村图书馆,还是《世界尽头冷酷仙境》里小镇上的图书馆,每次读到总是细细品味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那种平静、厚重、古老甚至有点冷清的意境,虽然知道这样的地方也许并不存在,但总是心存幻想有朝一日能在伦敦某个僻静的街道遇到这样一所人迹罕至的古旧书店或者图书馆。推门进去听不见烦人的流行背景音乐,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旧书所散发出的那种独特的油墨味儿,杂乱无章的图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不知道是不是店主人坐在收银台后,一心只盯着手里的书,或者甚至就不知所踪,让人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倒退着出门但看到牌子上明明写着OPEN。于是我可以自在地东看看西看看,晃悠上好久也不会被保安催促说“你到底买不买书”。当我问老板有啥推荐好书时,对方头也不抬地抽出一本封面连字都磨没了的书狠狠扔在我脸上:“Take this!You'll laugh,you'll cry,it'll change your life!Now get out!”最后我屁滚尿流地付了钱(还忘记拿找头),拿着书走出书店,却又不自觉地在门口流连忘返地想,嗯,下周还来吧。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即使找到了这样的地方,搞不好半年后也宣告破产,或者不得不把自己装修一番,开始在二楼卖起咖啡三明治,被迫在书架上摆出《我来告诉你如何变成百万富翁》这种破书。所以如果世界上有这种地方,还是不为人知的好吧。如果你知道有这种仙境的存在,请偷偷写信告诉我,我一定回请你吃章鱼小丸子。
远古人类生活考
我记得还在不久前,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马甲、小号,没有数不清的账户,没有人要求你变着法子绞尽脑汁想出几年后自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用户密码。如果我想跟你说话,我就带上话梅去你家,问问你昨天晚上有没有也准时收看了《秀逗魔导士》。话毕也无需寒暄,登26女车各自回家。没有准备好的表情符号跟着话语出现,你那张没有PS修饰过的长满痘痘的脸上,无论表情是笑是哭还是迷惑不解,我都觉得特别好看。
想再多说两句的时候我们就沿街坐下,边请你吃炸臭豆腐边继续扯淡,直到日落西沉觉得再不回家老娘老爹就要提棍出门喊打时,才飞快地赶回家去挨骂。除了父母的唠叨,没有人打扰我几点听广播,几点看书,几点抠鼻屎洗脚睡觉。
如果我很快又开始想你,想问你无穷无尽的问题,就满怀激动地快快睡下,等着。
因为第二天,又是崭新的一天。让人充满期待。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像所有人都人格分裂了。
看不见的运营商说这是信息时代,必须更完全地展示自我,煞有介事地说是要扩大或区分自己的朋友圈,完善不同需求的满足,参与新奇的用户体验。这些华丽辞藻堆出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还没说完我就听得快要睡着。
敢问又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比过去更孤单?
直到我发现自己开始偷虚拟的菜,造虚拟的楼,炒虚拟的股,开虚拟的公司,交虚拟的朋友,关心虚拟的粉丝。生活越来越丰富,心里却越来越空虚。现在看来,这些绚丽的泡沫只是被我们被商品竞争五马分尸后,残破灵魂的梦游。
今天我在这里,明天我在那里。早上我拉了屎,刚才我放了屁。上一分钟我还在家里,下一分钟我就会在健身房,甚至在过程中还要更新,我在“离开家并且去到健身房的路上”。啰唆又胆战心惊,害怕自己会人间蒸发一样到处留痕迹。人人渴望更亲密的交流,被人更多的了解,实际上却在更深地掩饰自己的同时,更贪婪地偷窥别人的隐私——然而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所谓的隐私都是不真实的。
人类的适应能力强得可怕,可以很快地变聪明,也能很快地变愚蠢。我们快要成为一群史无前例的高智商蠢蛋。如今我站在泥潭中央,看着身边的大军依旧奋不顾身地朝着泥潭中央坚定地走去。
我充满疑惑和不安。
如果跟上大部队我将永远也回不到我原来的地方,可如果停下不再前进,很快我将孤身一人。
我的心很想抽身回头,但双脚却牢牢站在原地如同生根发芽。向前后望去都看不到所谓的边际。
看久了甚至分不清到底哪一边才是原来的岸。
我深深怀念,那些似乎已经遥不可及的过去日子。
我偶尔想抬头看天时,不用拍下天空的图片作证,也不用更新我看天的状态,也没有人根据我看天的事实做回复评价。
我就单纯地站在那里看。
而且我还能确信这些生活里,铁证如山,朴素无用,瞬间即逝的片段,都真的发生过。
Delicate
昨天在回家的路上,觉得高速公路上安静得出奇,偶尔有驶过的车辆,驾驶座上的司机也都仿佛一边想心事一边默默不语独自前行的样子。看表才意识到竟然已经快10点了,由于北半球夏季白昼漫长的缘故,总让人错觉还只是傍晚五六点的光景。太阳完全下了山,地平线上的云已经融入山丘的阴影中,虽然夜空还很明亮,但已经可以看到头顶6000米高空的卷云背后,星星和月亮都升了起来。
车里的收音机中正播放着Damien Rice的《Delicate》——So why do you fill my sorrow.With the words you've borrowed.From the only place you've known.
我出神地听着,想起大学时一个住在我宿舍楼上的女生。我每次去找她玩,她几乎总是在堆满化妆品的书桌前一边敷面膜一边用笔记本电脑看《康熙来了》之类的综艺节目。印象里她的屋子总有一股香香的味道,窗帘很少拉开,床上堆满了好看的衣服。有一次我们正一起看视频,她突然问我,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动画片《大力水手》?我说记得啊,她继续问,大力水手不是有个女朋友叫奥利佛?对啊,怎么了?我问道。然后在一阵短暂的停顿后她转过头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最近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觉得他们好像分手了。”
后来这个女生转学去了其他学校,毕业后就回了国,我们也就再没了联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时常会突然想起那天她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想来这根本是一个完全不成逻辑的推理,但在荒谬的背后为什么我会感到某种真实的失落,并为这种失落而伤感呢?就好像大力水手和他的女朋友真的分手了一样。
And why do you sing.Hallelujah If it means nothing to you.Why do you sing with me at all.思绪回过神来时,Damien Rice正反复唱着这段歌词。这诗一般的语言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简单却又绝不简单地萦绕在脑海里。我们总是拿借来的话语去安慰别人或者表达自己,唱着说着自己也不太明白的话,很多时候我面对坐在我对面滔滔不绝的人,都一阵茫然,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重听那些当年觉得老掉牙的“经典情歌”时,总会一阵阵恍然大悟,心想这歌里说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这样的歌词不是现在的我,也不是未来的我多努力就能写出来的,有些事情我就是再努力,注定一辈子也做不到像别人那样好,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争个第一呢?有舞台就有观众,如果观众是我的位置,那在此时此刻这般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的歌,被旋律和歌词打动,那也许就是最适合我做的事。
又想起某天清晨我5点起床去赶火车,发现楼下的土耳其小杂货店已经开门在摆摊了,店主在清冷的空气里推着一桌桌水果从后门仓库出来。那天晚上我回家也很晚,11点从地铁站出来时发现这家店才刚刚开始收摊,早上看到的那些蔬菜水果根蒂的部分经过一天的氧化作用已经有点发黑,老板微微带着疲态一样样把盒子箱子搬回仓库。
从很小我们一路被指着前进的方向都是,报名好的小学,升入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学,如果有机会就要出国深造,目标职业不是金融商务就是IT管理。虽然在这些行业里,最好你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最好你能在这些企业里一路厮杀,打怪升级,成为总管、经理、CEO、大老板,最后站上金字塔的顶端。所以我从来也没想过小店老板过的是一种和我多么不同的生活。我也不能想象渔民、矿工、牧人,这些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没有电脑没有坐班没有老板的生活,是以什么为轴心在旋转?他们会因为网络慢而气愤吗?会因为谈到客户而开心吗?会有怎样的欢乐和烦恼?会有怎样的理想和期望?
在日剧里常看到主人公家里是开豆腐店的,世世代代,做着街坊里豆腐的供应。4点起床做豆腐,7点开店,送孩子上学去,营业,进货,忙忙碌碌到晚饭时刻等着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放学,好多人围在一起吃晚饭,一天天过去。做豆腐显然不可能是我们的家长希望我们去成就的事业,往往这种手工业被认为层次低下无趣,更提不上是所谓的成功人生。但是每次我看到他们满足平和的笑容,就深深怀疑我脚下的这条所谓光明大道将带我去向哪里。
成功真的是人生的唯一真谛吗?追求成功的人生,应该只是万种生活中的一种吧。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作为唯一的标准呢?用这种狭隘的模式催生现代人的痛苦。
我们这么容易觉得沮丧和不满足,就好比拉车的马匹,戴着无法看到四周光景的眼罩,只有眼前一条窄窄笔直的道路,仿佛生活的目的就是到达目的地,也看不见路两边的美景和发生的美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戴上这样的眼罩,也许我们就不会视到达终点为唯一目的,而是走入路旁的景色里,享受这个世界多样的美好,尝试奔跑跳跃。一条路变成了无数条,有着无数个方向,我们就能有更多时间在行动前停下来看看想想,有的马会选择去高地,有的选择停留在沼泽,走在路上的,有的选择慢慢走,有的选择快快跑。体会和享受选择带来的每一个真实的心情。
我们如果能自己选择自己要去的地方,也就比较容易能安心地生活在自己的选择里。就像住在大楼里的人,有人乐于登高望远,于是他选择住在顶楼,有的人希望能每天浇花种树,于是他选择住在底楼。没有什么对错之分。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教我们要争第一,要成功,却没有人教会我们要快乐。如果我们能学会满足和快乐,无论在哪里,无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还是能很好地活下去。
不是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情,终于决定不再努力,不再给自己压力,不再争取证明什么。两手一摊坐在地上,心里顿时觉得好轻松,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畅涌上心头,手里拽着的所有气球都一口气放了,看着它们越飞越高,终于消失不见。就像在人潮拥挤嘈杂无序的放映厅并不靠前的位置,找到一只舒适合身的小板凳,于是踏踏实实地坐下来等待聚光灯下的演出开场时的心情。
世界这么大,总有属于我的小小的一片天地,那些天才型和努力型的人也总会源源不断地从背后赶超上来,于是我就靠边走走,把看不到的远方留给他们,挥手致意希望他们跑出好成绩。而我只要能在书中读到他们后来的传奇故事,在收音机里听到他们红遍大街小巷的主打歌时,不自觉地哼唱摇摆,就已经足够。
到最后,发现我想要的原来只有那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