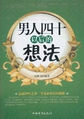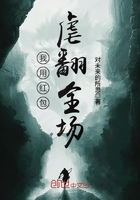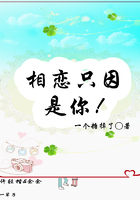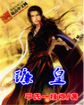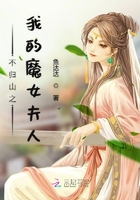当坐在马桶上又忘记带书时,我偶尔会想想自己喜欢的死法。
我希望自己能多多少少保持着健康的体魄,最后晚年的某天在睡梦中静静离去,但这样的死法非常奢侈,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若需要一个致死的因素,想在性爱高潮中领便当,或者大笑着升天。
人死后依照传统总要举行葬礼,说实话我对此类烦琐的仪式向来厌烦。在人均地皮面临严重压缩的今天,据称北京的高级墓地的价格已经超过商品房,怪不得有人感叹真是连死都死不起了。曾有人建议可以竖着放置棺材来节约地皮,我觉得干脆连棺材都不需要,直接挖个竖坑把人戳土里,露出上半身的话岂不是连墓碑都可以省了?我先生常因我听音乐时偶尔会考虑这是不是适合在葬礼上放而哈哈大笑,笑我说办婚礼还没操心够啊还要操心葬礼。可我就是不想让来见我最后一面的亲朋好友听那讨厌的哀乐,走那无聊的程序。所谓遗体告别真是马后炮般的行径,真要告别难道不是要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告别才对吗?所以我的葬礼应该像party那样热闹,人们走着红毯欢笑着进场,围着我的遗体把酒当歌。背景音乐到底放巴赫还是摇滚我还没有想好,或者来个Remix版本的哥德堡变奏曲也不错,如果能再有个多媒体大屏幕滚动播放一下我生前画的画,做的动画什么的就更好了。有条件的话在墓碑上嵌个iPad,每年来扫墓的人还可以玩玩《植物大战僵尸》打发时间。
文学上人们总是用“远去““离开““告别”或者“在另一个世界”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人的往生,导致一说到死亡我就不免联想到旅行,本质上说都是启程去别处的感觉,只不过死亡拿的是单程票,放下的东西是生命中的一切。若照此理,那些在生活里决心改头换面的人们,大到更名改姓抹杀过去的亡命之徒,小到辞职旅行也罢搬家也罢,出于各种原因去到新的地方生活学习的人们,是否都在某种程度上,也实行了“将自己的某一部分杀死”的精神仪式呢?而那些被杀死的部分到底是什么?留下的部分让我们更真实地接近自己了吗?
无论怎样,只要活着,人们就常为死亡操心,但死后的事情没人知道,就好像我们没人操心出生之前的情况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生长在富裕抑或是贫穷的家庭,无论是开心也好,悲伤也罢,面对不同的苦难、幸福与命运……生的体验也许不尽相同,可死亡对我们的影响却是相同的。无论是小时候看到同学别黑纱的压抑,直面死亡降临的震撼,还是面对家族成员死亡的迷茫与深深思念,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的心联系在了一起,因为人人都会死亡,人们才能懂得在活着时更善待他人。
既然有如此的联系,那死也许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延续。在生命里,死和生是等价的。姑且不管活着的意义最终会是什么,人活着之所以能有意义,也是因为不远处有死亡在等待。这样一来,对“活着的意义”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死亡的意义”的思考。活着就是等死。这句话其实说得很对。但等死的过程可以无可奈何,也可以乐观积极,生与死之间这种转换的可能性,反而赋予了单纯独立于死亡之外的生命更丰富的内涵。
死亡是生命给予我们最后的王牌,没人会在斗地主的时候上来就扔炸弹。
让我们在去死的路上,且行且珍惜。
You'll laugh,you'll cry,it'll change your life.我很喜欢逛书店,在书店里一坐就能坐一天。但是现在不知怎么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翻到想买的书后,会直接掏出手机上Amazon查书价,发现差价有十几磅的时候,毅然决定为了省钱就不在书店买了。有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身为并不富裕的一个普通人,“遇到一样的东西一定会买便宜的那个”也是人之常情吧。但在自作聪明地满足了消费优势后也常会担忧,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到店里只看不买,那书店迟早得倒闭。而且那种走出书店却发现手里无书的感觉,就好像早上特地为了逛书店而背出来的书包一样,无精打采地瘪瘪地耷拉在背上。
以前上海有过一家书店叫思考乐书局,因为晚上会开到很晚,我夜游时跑累了也会跑去那里坐在地毯上看会儿书,喜欢他们的台灯和大木书架。还有在静安寺伊美广场出口出的那家季风艺术书店,小小的店面安静整洁,不但书目丰富,店里还提供画册预订送货上门的服务。两年前回国时突然发现书店人去楼空,唯有门口卖章鱼小丸子的摊点还是那样生意兴隆,我恨不得点上一支香再供上两个小丸子来纪念又一家书店的离去。曾经一度在伦敦Oxford Street上灯火通明的大型连锁书店Borders也早已关门倒闭,当时非常震惊,不敢相信规模这么大的书店会就这么关了,书店本来的位置上后来建起了热闹的时装店,才不到几年Borders曾经存在过的踪迹就消失在了过往人潮的记忆里。跟友人说起书店低迷的事,他表示着消费者虽有一定责任但商家也必须为了应付如今的网络购物便利而想别的办法,比如书店在功能上的多元化,卖唱片卖周边,提供咖啡饮料等来增加收入。虽然很多书店目前是这么做了,但想起Borders一度也是以“Book.Music.Cafe”为主题,不还是倒了,觉得前景依旧堪忧。
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去书店,是去静安寺百乐门酒店楼下的那个新华书店,那天父母给我买了一套凡尔纳科幻小说全集,一共二十几本,怎么搬回家的至今想来也是个谜,好像就是用绳子捆一捆然后坐公交车拎回去。那个年代的人真是臂力过人,不像现在我在公车上拿手机看东西,才举了几站就觉得脖子发酸。
真正开始喜欢看书,确切地说一开始只是看漫画书,是从初一开始。我家对面有一所少儿图书馆,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是一栋三层的老洋房。房子外墙刷成蓝色,木质的楼梯踩上去嘎嘎直响。我周末得去那儿三楼的多功能厅上英语补习班,有一次补习班的房间停电,老师把上课教室挪到二楼时才发现了图书馆的存在。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我去过的所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是凶巴巴的,一副我欠了他们的书几年没还的样子。不过大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所图书馆异常安静,几乎达到太平间的标准,大概所有声音都被管理员大妈管理了吧。不久后我在这个图书馆最里面发现了一间儿童阅览室,阅览室里大部分的书都是漫画。我身为一个初中生还待在儿童阅览室其实是很丢人的事,很多在附近上班的大人都把这里当做临时托儿所,阅览室里常爬满了五六岁的小朋友,这让坐在其中的我显得非常突兀。可即使这样,我还是背负着压力与内心的羞耻感坚持一没人注意就溜进儿童阅览室看漫画。后来当我开始有点兴趣看文字书籍时,图书馆开始装修改造,我也去了寄宿高中,结果竟然再没机会回到这个图书馆里了。再等想起来时已经过去好几年,当年是图书馆的这块地现在已经被隔壁警备区司令部扩建的工程所吞没,配枪的警卫纹丝不动地站在图书馆原本大门所在的地方。
我高中的图书馆在规模和藏书上其实已经非常壮观,加上我的室友在图书馆打工,根据她的内部情报,我总能及时知道哪本特别难借的书什么时候还回去了,并可以在第一时间冲到图书馆抢走。高中时的图书馆因为有空调总是挤满了人,虽说不上特别浪漫,但在避人耳目的拐角也会有很多情侣来占位子,桌上放几本不知所云装装样子的书一边写作业一边眉目传情。图书馆因此被教导处主任列为重点“扫黄”地点,有一次教导主任得意地抓住一对貌似在图书馆谈恋爱的学生,正要教训却得知他们两个压根不认识对方,只是碰巧坐在了“情侣专座”上。高二时学校开始分级教学,我数学特别差,于是分到ABCD的D班。开学后我努力了一个月发现成绩毫无起色,于是干脆自暴自弃搬到最后一排上课吃吃泡面看看小说,同时也跟坐在我前排的几个别班的男生混熟起来。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在男生中流传着一本超级黄书,抢手之程度令人咂舌,传说这本书自从开学第一天从图书馆外借出去后就根本没时间回图书馆歇歇,一直在坊间流传,预订此书的人数已经达到50人之多,一连丢过好几本都是被学生窝藏最后下落不明了。这个流言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但是男生们为了保护稀缺资源就是不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其实我对书有多黄不感兴趣,只是好奇到底是本什么书。最后过了三年临毕业我才从某个男生嘴里撬出这个秘密,原来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总之出国以后再去的书店和图书馆就比较正常,或者说让人印象不那么深刻了。大学图书馆艺术类书籍虽然多得惊人,但所有画册都被翻烂,一打开内页就哗啦啦地往下掉。工作以后有时会去唐人街附近的查宁阁,算是伦敦比较少有的中文图书馆,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占了很多位置,虽然馆藏有限但总比看不到强,似乎如果特地去订他们也会帮你从国内引进。由于很多书都是台湾版的,于是慢慢练就了纵排版书的阅读习惯。第一次接触到自动借阅机也是在那里,感叹虽然破但是硬件还很高科技,就跟古老伦敦城建筑物们外旧内新的特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