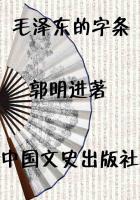两个人你谦我让的,都让对方先吃。“我就要吃你吃过的,这样的感觉好近。”韩鲁手捧着饭盒,当作托盘一样。
吃过了早饭,馨一浅浅的睡着了,倚在韩鲁搭过来的手臂上,“手好些了吗?”馨一悬着头问道。
“睡吧,我没事。”韩鲁把馨一的头轻轻的倚在自己的手臂上。
看着她熟睡的样子,像个襁褓中的婴儿,脸上写满了清澈。他闲暇的翻着杂志,杂志里有关于盛懋集团的报道,在杂志的后几页有关于任游新届才俊的报道,同时隐性的报导了任游即将大婚的消息。
韩鲁阖上杂志,对于任游,他隐隐的听说过,不是关于青年企业家的事情,而是关于他和馨一的关系。她不在乎她的过往,更不在乎她没有对他说过什么,他珍惜的只有当下,每个人每天都是‘向死而生’,他现在的‘生’,馨一带给他希望、带给他温暖、带给他对于未来的诠释。
春色春景萌回,夏风正劲来袭的日子里,他携着馨一的手走向婚礼殿堂……这美好的一幕在阖上杂志的一刻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坐在去往江东城的汽车上,韩鲁计划着春暖花开的时候结婚要准备置办的东西,硬件的东西已经准备完成,只有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需要置办。大家同窗好友结婚的好多,都争着抢着要当他的伴郎,还有几个女同学要给他‘出谋划策’,举办同学们中间最好、最有创意的婚礼。
汽车一路颠簸,土坡、山路崎岖泥泞,方圆十里左右的城市这几日下了雨,道路高低起伏不平。馨一在火车上劳顿了二十几个小时,此时又微微的泛起了困意,韩鲁拉上了窗帘,像抚摸小孩子的额头一样,“睡吧,到了我叫醒你!”馨一微微的点了点头,长长的睫毛扑烁烁的闪着温柔的光芒。
座位像是被一扫而空一样,不像在火车上必须按号入座,韩鲁提着大包小裹,现在只有最后一排的座位了,刚巧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便把司机后排一侧两个人的座位让给了他们。馨一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没有‘抢’到好座位,你坚持一会儿啊。”韩鲁小声的对已经坐在角落里的馨一说着悄悄话。他坐在汽车中间过道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左、右都没有什么把持或倚靠的地方。“那你扶好”,馨一也悄悄的回了他。
他们出门早,加上坐火车长途跋涉,馨一像是被嗑睡虫缠身一样,困意十足。韩鲁的手臂一直搭在车窗上,微微的和馨一的身体保持了一点点距离,他怕他的头不小心撞到前面座位。
天一点一点的蓝了起来,天空像湛蓝色柔软的丝绸一样倾泻下来,汽车渐渐的驶入崎岖的山路,司机没有看清楚前面有低洼的沟,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汽车被重重的弹起了很高,后又重重的被自由落地。韩鲁第一时间便看她的头有没有撞到,幸好他的胳膊一直扶在窗边护着她。韩鲁由于个子高,头顶在了车棚的位置上,脖子和肩膀立刻便有了像睡落枕了一样的感觉,失去了自由灵活。
馨一束手无策,抚摸着他的脖子,轻轻的揉着。
在他的心里,脖子疼痛一直忍着,但她的手覆在上面,他觉着虽然身体疼着,但心里却是热的,并且热烈的快乐着。
韩鲁的手搭在车窗的位置上太长时间,麻麻的感觉好久也没有缓过来,手臂一直是僵直的状态,索性便把大包小裹都搭在肩上,没有让馨一拎一个包裹。
馨一的父亲早早便侯在这里,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三年没有见女儿了,见了女儿一把鼻涕一把泪,远远的便认出了她,奔跑了几步迎了上来。抚着她的头发,看着她眼眸中依旧闪烁着纯洁的光芒,父亲放下了心。馨一的父亲有些泪水潺潺,却止住在了眼眶里。韩鲁的心里波漾,怕他们父女相见感怀悌零,便主动做了自我介绍。
馨一的父亲似乎和天底下的父亲一样,都是那样的慈祥,眼神中含着期许,还有积蓄已久的老泪纵横,只是横在眼眶里,微微的盈动着,用眼睛对女儿身边的男人细细的端详着。父亲瘦削的样子,韩鲁不忍心让叔叔接过包裹,“整天在大地里面干活,不碍的,不碍的。”父亲接过两个行李包的时候身体微微的颤了一下,心却在颤的一刻绽放了。看见了阔别已久的女儿,又看到了身边的男人,血脉再一次用火把连在一起,熊熊的燃烧起来。
“吃吧,我开的稳。”父亲对韩鲁说让他尝尝他早上亲自烙的饼。韩鲁早已饿的鸡肠辘辘。父亲以六十几岁的年龄驾着三轮车,仍然驾轻就熟。
馨一始终都没有说太多的话,谈话和交流都被父亲和韩鲁占据了,只是父亲在见到她的时候轻轻的抚了抚她的头,她把手递给了父亲。
父亲坐在前面驾着三轮车,能感受到一股暖流在父亲的怀里涌动着,也能看到透着前面的玻璃隔板父亲在笑着……
“我的车技还可以,你们都睡会儿。”后面的座位上是母亲亲手给缝制的羊毛座垫,暖暖的垫在下面,心已经被暖意包围。
父亲日益佝偻的背在山路一巅一起的时候会不经意间撞到后背的玻璃板上,小的时候,自己永远都在父亲的前面走着或跑跑跳跳,从来都是这样,现在才明白,那是父亲的眼睛可以看到女儿的一切,让女儿安全、让女儿自由,让女儿不受任何伤害。
如今的父亲,坐在前面,还要给自己开车……,她的心里面一阵阵黯然。
馨一开始悔恨自己,悔恨自己的无情和残忍。鼻翼里飘过父亲亲手做的饼的味道,还是小时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