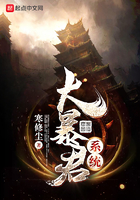夜色渐浓,雪地寒风如刀锋削来,荆轲止住了哭泣,却呆呆跪着不为所动。
长空与飘雪生起了溝火,两人一言不发,默默陪着荆轲守在溝火前。耳际传来北风的呼啸和噼啪的柴火迸裂声,然而荆轲的感觉宛如死去一般。
长空几回想说些劝慰的话,都让飘雪打眼色阻止,飘雪明白,荆轲此刻需要的只是冷静。
东方微露鱼肚白,风雪稍停,荆轲霍然站起身,朝树林默默走去。长空与飘雪见荆轲以剑掘地,继而跪下以双手拼命扒出泥土。
扒着扒着不禁又痛哭不已,长空叹气道:「荆兄弟如此性情,往後的日子不好过啊!」
飘雪点头道:「月姑娘何尝不也如此...只怨苍天不允多情共白发...」说罢泪水忍不住滑落脸庞。
长空轻轻拭去飘雪的泪水道:「我过去帮荆兄弟,妳就歇会吧。」
望着长空的背影,飘雪突然明白自己从未放下长空,正是不见多情只道绝情。
而荆轲与月儿之间的情意,却因为月氏兄弟的死,自然也成了不能解的死结。
将月氏兄弟埋葬以後,荆轲一脸憔悴跪下叩拜,喃喃自语道:「荆轲对不住二位兄长,也对不住月儿...」
长空感慨道:「荆兄弟,西门述已伏诛,你也算是为月家兄弟报了仇,别太自责了...而忘神符除了迷惑心智,也麻木了形体,月家兄弟可说走得毫无知觉。」
荆轲却置若罔闻,良久方站立起身行至江畔,双手捧着清羽剑长叹道:「月儿无法面对予我,我又何尝能再拥有你?」
只见荆轲手一挥,清羽剑径直抛飞落入汨罗江,瞬间沉入江底。
荆轲仰天一声长啸,戚然道:「兰花夫人,荆轲辜负妳一番美意了。」
疾风早已奔至荆轲身边挨着,马蹄踢踏轻声嘶鸣,仿佛在慰问着主人。
荆轲回身向长空与飘雪深深一揖道:「珍重!」说罢一跃上马,驾的一声,头也不回直奔而去。
长空与飘雪望着荆轲远去的身影,不由一阵怅然若失。
「走吧。」兩人异口同声说道,随即不由相视一笑同声道:「上哪?」
长空畅快道:「飘雪去哪,长空必相随!」
飘雪望着天空轻声道:「春天快来了,不如寻一处清静之地,只闻田野花香不见兵刃...」
长空手一挥,笛剑已抛落汨罗江,紧握飘雪双手道:「长空此生但愿执子之手足矣。」
飘雪温柔道:「你不後悔?」
长空紧紧搂着飘雪道:「我已经後悔了十年,今後不会再放手了。」
远处,树梢头的冰雪仿佛已开始融化了。
山川水流逐渐湍急,荆轲弃大道择小路策马狂奔,也不知经过多少时日,日子,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
冬季已过,正是春暖花开之际,然而荆轲的內心世界却停留在风雪交加的汨罗江畔。闯荡江湖的雄心,亦随清羽剑沉入江底。
荆轲仿佛在追寻月儿,然而心理却也明白月儿的决心,几回噩梦惊醒的心悸,矛盾的心理无时不在折腾着。
一路漫无目的前行,荆轲逢有酒肆必喝得酩酊大醉,而树林山坡随处即蓆地而臥。
荆轲终于明白逍遥子何以好酒如命,纵然一醉只能忘却一时半刻的痛苦。
这一日,荆轲行经一处小镇,腹中早已饥肠辘辘,逐牽着马缰往一酒肆走去,侯在门外的店小二见荆轲衣衫破旧,所牽之马匹却非比寻常,倒也殷勤招呼。
荆轲亦旁若无人,叫了酒菜便大吃大喝,片刻饮尽了一坛酒。
帶着几分醉意的荆轲手一挥,呼喝道:「小二!结账!」
伸入怀里的手摸索良久,这才惊觉身上竟然连碎银也掏空了,店小二双眉一挑,粗暴问道:「客倌!你该不会是想着白食白喝吧?」
荆轲也不理会店小二,径直朝掌櫃走去说道:「店家,实不相瞒,我今日确实不曾帶得银子在身,可否容我日後再还?」
那店家赔笑道:「这位客倌,您别说笑了,咱可是小本买卖,这,这那能赊账啊!」
荆轲脸色一沉道:「可我今日确实没有银子,店家难道不能行个方便!」
那店小二插嘴道:「瞧你那匹马倒也值几个钱,要不...以马抵账呗!」
荆轲怒道:「你敢!」那店小二却大声嚷道:「怎的,光天化日之下,白食还想行凶不成!你也不瞧瞧,这里可是大秦的天下!」
荆轲正待发作,只见一壮汉大步上前打圆场道:「店家,且莫嚷嚷,这位朋友的酒菜钱,算在我家公子的账上吧。」
荆轲回过身一望,只见那壮汉一身粗麻布衣,浓眉大眼中透着一股英气。
那壮汉向荆轲微笑道:「在下王贝,我家公子有请阁下前去饮杯水酒,可好?」
荆轲斜眼望去,靠窗一桌尚有一老汉与一位身穿锦衣汉子,年纪仿若荆轲一般。
荆轲亦不客气道:「多谢王兄解围,请!」
王贝当即引着荆轲行至酒桌,毕恭毕敬道:「公子,人已帶到。」说罢向荆轲介绍道:「这位便是我家赵公子,这位是在下家父。」
荆轲只见那身着锦衣的赵公子仪表非凡,即便只是稳坐着不动,却浑身散发着一股覇气。
那老汉则一头白发,硬朗的身子却透着比王贝更强势的威严。
荆轲欠身道:「多谢赵公子了。」那老汉笑道:「老夫乃王前,这位便是赵镇公子。」
荆轲暗忖此三人绝非寻常江湖客,当下也不多言语,拱手道了声多谢便大剌剌坐下,自顾倒滿一碗酒一饮而尽。
赵镇豪迈大笑道:「兄弟好酒量!敢问如何称呼?」
「荆轲。」说罢又倒满一碗酒一饮而尽。
王前望向赵镇呵呵笑道:「老夫自以为海量,看不出荆轲年纪轻轻,却也有这般酒量啊!」
王贝坐下打趣道:「爹,孩儿总说您年纪大了,您还不服气呢,往後还是听娘的劝,少喝些酒吧。」
王前捋着花白的胡子笑道:「你这猴崽子,沙场之上,我哪老了?」
赵镇轻咳一声,王前两父子当即噤声不语。
赵镇微笑道:「荆轲...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有十四年了吧,在赵国邯郸,不过,他叫庆轲。」
荆轲仔细打量眼前的赵镇,脑海浮现了十四年前,邯郸市集让孩童欺凌的燕丹,赵政与成蟜。
荆轲盯着赵镇道:「我也想起了三个人,燕丹,赵政,成蟜。」
赵镇欢喜道:「果然是你!当年仗义相助,赵镇都记着。」说罢向王贝道:「斟酒。」
王贝即刻起立向荆轲倒满一碗酒,赵镇举碗向荆轲道:「请!」
荆轲也不多言,端起碗即一囗饮下,王前父子不禁脸露愠怒之色,暗道:「此厮好生无礼,对大王如此不敬!」
原来赵镇即当今秦王嬴政,其父异人乃秦国派往赵国为质子,而嬴政之母赵姬于邯郸诞下嬴政。
嬴政自幼从母姓,是为赵政,其父异人在商贾呂不韦的帮助下登基为秦王,即庄襄王。
而庄襄王驾崩之後,赵政几经波折终於返回秦国,于十三岁登基即位为秦王,从此称为嬴政。
嬴政即位之初,赵姬以商贾呂不韦有功为由,让嬴政尊称其为仲父。如今即位虽已十年,然大权依旧落在仲父呂不韦之手,自然难免心生郁闷。
随着年纪增长,嬴政与吕不韦之间冲突日益加剧,两年前加冠之礼又恰逢呂不韦之食客嫪毐兵变,平叛之後,嬴政亦开始布署铲除呂不韦的势力。
这一日微服与将军王翦,王贲两父子出外解闷,却巧遇荆轲无法结账的窘境。
嬴政对荆轲的态度却不以为意,随即一口饮尽,並向王翦父子使了个眼色。
王翦父子虽不忿气,倒也不敢造次,只得强忍一腔怒火,自顾饮起酒来。
嬴政以江湖中人的囗吻道:「荆兄弟,你若是左右无事,何不跟在我身边?」
荆轲斜眼瞧着嬴政轻声道:「秦国大王,嬴政,你真当我喝醉了?我虽在江湖,却也听闻你十三岁那年已即位为王。」
嬴政笑道:「荆轲好眼力,即知我乃秦王,何以尚且如此无礼?」
荆轲淡然道:「你的威严在秦国的朝堂,不在天下的江湖。」
嬴政搖头道:「威严?一个假王,何来威严?」说罢又是一碗酒饮下。
王翦瞪了荆轲一眼,心急道:「大...」王字未脱囗方觉不妥,欲改口称大哥又觉不当,不禁尴尬不已。
嬴政却拍了拍王翦臂膀道:「不过,我终将会是真正的王,而且,将来天下必归我大秦所有!」
王翦父子猛点头道:「对!对!」两父子虽有些莾撞,但是对於嬴政却是忠心耿耿。
荆轲冷笑道:「如此野心,不知天下又该添多少亡魂!」
嬴政正色道:「此言差矣,自春秋五霸至七国争雄,大小战役不计其数,死伤何止百万?今日若是大秦弱小,不过让六国瓜分城池而已。」
荆轲望着眼前的嬴政,早已不是从前在邯郸让人扔石头欺凌的赵政,王者的霸气已表露无遗。
嬴政见荆轲不搭腔,继道:「再者,六国之君虽称王已久,然,在我看来,骨子里却乐於诸候之命。一统天下,必是我大秦,也唯有一统,方能平息干戈。」
荆轲一时语塞,想起卫国卫元君,确实安于一隅,然卫国国小民寡,无法与七国争霸倒也是事实。比较秦国,齐楚赵三国起步都胜於秦国,可是国势却是日益衰败。
长年征战讨伐,多少家破人亡的悲剧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乱中发生,百姓渴求的无非是天下太平而已。
王贲见荆轲沉默不语,逐劝道:「荆轲,大丈夫为的是建功立业,跟着咱大王凖没错!」心里却暗忖:「大王若让你跟着我,那就安排你当个副将也就是了。」
荆轲却不理会王贲,反问嬴政道:「秦国何以强大?」
嬴政自负道:「历代先王远见,变法图强!」
荆轲又问道:「何人所倡变法?」
嬴政笑道:「当然是先王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於是有了今日之大秦。」
荆轲盯着嬴政道:「听说商鞅最终却落得车裂之刑,这又是为何?」
嬴政面露不悦道:「荆轲,你又何必说这番话激我,再说,你不是商鞅,而我也不会是秦惠文王。」
荆轲大笑道:「哈哈!荆轲只当你仍是赵政,然道不同,不相为谋。」说罢举起酒碗道:「荆轲敬你的度量,请!」
嬴政当即一饮而尽,放下酒碗道:「荆轲,赵政随时欢迎你,即便只为饮酒。」
荆轲站立拱手道:「好!告辞!」转身即大步走出酒肆。
当荆轲牽过疾风,正欲翻身上马之际,身後传来王贲呼叫道:「荆轲,且慢!」
荆轲甫一转过身,只见王贲将一包袱塞入自己怀里,简单说道:「大王让我交予你。」
荆轲双手接过,便知乃是银両,当下也不客气收下道:「多谢,告辞了。」
王贲望着荆轲逐渐远去,不由骂道:「不识抬举的傢伙!」
「咳!」只听王翦在身後轻咳一声,嬴政已从身旁走过,笑道:「走吧,下回别再有失大将风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