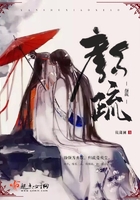还未见到人,庄砚已是心头一喜:“眉生!”
那个眉目清秀的少年欢喜雀跃地一路小跑到了对影亭边,开心地拉住庄砚转了一圈,又上下仔细看了一番,笑嘻嘻地说:“真没想到阿姐竟跋山涉水地回来了。”抬眼见到庄砚身边的阿塔儿,又笑嘻嘻地打招呼:“姐夫也陪着阿姐一同回来了呢。”
庄砚有些紧张地压低声音对眉生说:“你姐夫的身份你可对谁都不能说破,对父亲和大娘都不行,知道吗?”
眉生笑眯眯地说:“我哪有那么不懂事,都晓得的。阿姐放心吧。”
庄砚开心地上下看看眉生,他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几年不见,又抽条了不少,已经比她高出了一个头。肩膀宽了,穿着长衫再不像从前那样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眉眼也变得更好看了,眉宇间多了一丝英气。他已满十五,刚刚束发,头发整齐地高高束起,扎着青色的逍遥巾,迎着风长身玉立,眉生这个昔日弱不经风的少年竟也有一些男子气概了。
庄砚看着眉生的模样心下欣慰,说:“眉生这么快就过了束发之年。”
一旁的阿塔儿插嘴:“束发之年?”
眉生不好意思地低头一笑,抬头看着阿塔儿说:“男子十五称束发之年,就不再是小孩子了。”
“能娶妻了?”阿塔儿打趣他。
眉生的脸唰一下红了,喏喏道:“这个……这个倒还不能……不过母亲……已经在为我物色了……”
庄砚看着弟弟通红得要滴血的脸,笑着说:“娶一个好人家的女儿,自己也可心的。以后要在一起过一辈子呢。”
“知道了。”眉生窘迫得急于想转移话题,说:“阿姐和姐夫不要总站在这里,我们回屋说话吧。”
三人又回到白鹭堂,就着茶水和点心絮絮聊了许久。
原来自从眉生那次和庄砚在芷珪相见,商队的旁人都一直被看守着,所以并不曾直到他们姐弟相逢的事情。回到了扬州,众人对庄石潭添油加醋说了在赤黎的那一番历险,庄石潭便再也舍不得让自己的宝贝独生子再去冒这样的风险。哪怕生意比从前小一点,毕竟曾经是江南一带最大的布庄,也不是几年间就会落败的。因此便绝了那往西域通商的心思,将眉生放在自己的布庄上跟着自己学做生意。
直到日落西山,木槿来说:“老爷回来了,听说姑爷和小姐回家探亲很欢喜,已经吩咐备下了酒菜。此刻大家都在前厅,就等着姑爷和小姐了。”
庄砚在心里叹了口气。欢喜?她的这个父亲,几时见到自己时欢喜过?想必是听大娘添油加醋说姑爷未知姓名来历但气度不凡,也许是个达官贵人,所以才摆出这副讨好的嘴脸,想捞一点好处吧。
跟着木槿到了前厅,庄石潭一见到他们出现在门口,便起身迎了出来,满脸堆笑高声说:“砚儿,你可算回来了!你可把爹想死了!怎么竟几年没有一封家书回来,爹爹还一直都以为你不在人世了!”说着说着,满脸的笑容渐渐隐去,眼眶里倒是憋出一点泪花来。
庄砚行了个礼,淡淡地说:“山遥路远未便通信,要爹爹担心,是女儿不孝。”
庄石潭抹了抹眼角说:“哪里的话!回来就好,让爹爹再看看你就好了。只是可怜你的娘亲,都没能等到这一天,竟早早地故去了……”
庄砚看着父亲在阿塔儿面前假仁假义地说着这些虚伪的话,心下不快。但听他提起了母亲,也忍不住酸了鼻子红了眼眶。
许氏从后面走上来挥挥手中的罗帕,扶住庄石潭说:“哎呀,砚儿回来是喜事,不要提那些悲伤的事情。”
庄石潭这才又回复了笑意,亲热地拉着庄砚,眼却看着阿塔儿,问:“不知道姑爷是何方人士,做什么营生?”
阿塔儿欠身行了个礼,说:“小子名叫柯吉,是硕桂城人,在那里做一点小买卖度日。”
“小买卖?”庄石潭转了转眼珠,又问:“不知是什么买卖?”
阿塔儿照着这一路已经说了几百次的谎话顺溜地说:“小子在硕桂城做屠羊卖肉的营生。”
许氏在庄石潭的身后嫌恶地皱了皱鼻子。
庄石潭也是一愣,但到底比许氏见得多世面,还是面不改色,继续问:“这么说生活还衣食无忧吧?可会委屈了我的女儿?”
阿塔儿笑道:“小子蒙令千金错爱,自然不敢让她受委屈,衣食上自然一应不缺,有几个闲钱时也会给娘子买朵花戴。只是惭愧比不得岳父大人家大业大。”
这一番话说得一本正经,听得阿塔儿身后不远处的哥里达拼命憋着才没有立刻笑出声来。
眉生见父亲只是不停发问,似要将阿塔儿的老底都翻个清白,便上前说:“父亲,阿姐和姐夫千里跋涉而来,还是赶紧请他们入席吧。人都要饿坏了。”
庄石潭这才如恍然大悟一般,一手牵着庄砚,一手牵着阿塔儿,带他们入席坐下。心里却已经对阿塔儿颇不以为然。
看着是有气度,没想到几句问下来,竟是个在边城杀猪宰狗的屠夫!他哪怕是做点两边倒货的买卖,也能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助益啊。
席间庄石潭又几番试探了阿塔儿,终于确信他的确就是个在边城卖肉的屠夫,不禁大失所望。此后席间便默默无语。偶有眉生因为气氛太凝滞和尴尬而出言想要调和,却始终都没有人愿意再开口说话。
夜里,庄砚因为白天父亲和大娘的态度心里不痛快,一直在床上辗转无法入眠,便索性披了衣服起来,走到窗前打开了窗子。
因着白日里下雨,此刻天上一点星光都没有,,只有一弯月亮朦朦地发着光亮。
庄砚默默看着窗下那绿油油尚沾着雨水的芭蕉,轻轻叹了口气。
身后阿塔儿也起身走到她身后,扶着她的肩膀轻声说:“还在为他们不快吗?”
庄砚望着芭蕉说:“我本也知道,求父亲疼爱是奢望。打小便是冷言冷语不闻不问,大娘更是如此。可是没想到我离家数年归来,他们还是这样。罢了,原本就是我奢望得太多了。”
阿塔儿笑了,说:“这不是你的错,或许是我这个屠羊卖肉的女婿让他们失望了。”
庄砚苦笑,说:“我母亲只是父亲的妾室,我又是个女子,因此从来受不到父亲的重视。母亲当年也不是心甘情愿进门的,只是个中曲折我便不得而知。大娘又是个厉害人,从小不知挨了她多少打骂。旁人看着是长在高门大户里,锦衣玉食,其实冷冰冰的,只能每日和琴棋书画作伴。可到头来连要个和静人生也不能,还被父亲当棋子一样地远嫁……”
阿塔儿抚了抚她被窗外进来的夜风吹乱的头发,说:“你这样的辛酸,却是我没有尝过的。这种不知冷暖的家,这样势利的爹娘,本不该回来。”
庄砚摇摇头:“只是看着眉生,我心里才有些安慰。可惜他中断了学业,小小年纪竟跟着父亲行商。”
“各人有各人的路要走。读书入仕对眉生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也许像他这样读了几年书再去行商的,反而能成个儒商,也未必是坏事。只要他性情纯良,做什么都不要紧。”
听阿塔儿这样说,庄砚才觉得心里宽慰一些,又说:“我想尽快去祭拜了母亲,我们便离开吧。——我实在不想呆在这里。”
阿塔儿心疼地将她揽紧怀中,让她的脸颊贴着自己的胸膛,说:“好。”
庄砚贴着阿塔儿的心口,听着他胸腔里那一声一声有力的心跳声,心头涌上了一股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