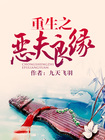到长安的第一天,玄奘在街上游行了一天,二十多里的路途上,人山人海,迎接的人群前呼后拥,只能缓慢行走,直至天黑才到达馆驿。
夜深了,可玄奘毫无睡意。窗外呼啸的寒风使他清醒,他仰望深邃而神秘的星空,似乎在感谢佛陀的保佑,这十七年间,他历尽人间艰险与苦难,终于又回到了生育他的故土,当年离开这里的时候是那样的狼狈,归来之时,朝廷如此礼遇,国人如此热情,他不禁感慨万千,不知不觉中已是热泪盈眶。
玄奘不曾料到,更隆重的欢迎仪式还在后头。朝廷已作出决定:在朱雀门大街南头集中陈列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和佛像,然后举行护送他去弘福寺的盛大游行。
正月二十八日,长安城一派节日的欢乐气氛,朱雀大街上设案陈香,张灯结彩,街南头更是热闹非凡。街两边整齐地排列着几百张宝案,宝案上挂着花团锦簇的帐幔,旁边插着幡旗,主案上供奉着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珍贵的佛像和佛经。川流不息的人群到街头拜遏瞻仰,赞不绝口。
不久,游行开始了。乐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供着佛像、佛经的富丽堂皇的宝案宝舆,一排排香炉队紧随其后。再后面是万余名身着袈裟的僧尼行列,一队接着一队。从朱雀大街到弘福寺,几十里之间,倾城出动的老百姓,朝廷和外地官员都站在道边瞻仰,并烧香、投散纸花。官府恐因拥挤发生事故,派出许多兵卒上街维持秩序,并明令就地烧香散花,不许跑来跑去。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难得一见的盛会。
玄奘终于到达弘福寺,然而,他的心情并未就此轻松下来,他深知,中国的情况与印度不同,朝野上下崇信佛教的人固然很多,但冷漠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人亦不在少数,毕竟尚未见到皇上,译经的事尚未最后落实。在弘福寺稍作安顿之后,玄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又匆匆踏上赶往东都洛阳的旅途,他要面见唐太宗,当面争取皇上对译经事业的支持。
这时,太宗正调集兵马,准备远征辽东,但还是抽空在仪驾殿接见玄奘。太宗亲切地说:“法师西行求法,怎么不给朝廷报告?”
玄奘回答说:“玄奘临去之前,曾写过几个报告,未蒙批准,因求法心切,便擅自出关。现在想来又惭愧又害怕。”
太宗说:“出家人已远离世俗,也难怪。你能舍命求法,惠利苍生,是应当奖励的。法师不必再为此事心烦。从中国到印度,山川险远,语言风俗相异,真难想象法师是如何到达的。”
私自出境得到太宗的谅解,玄奘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虑:“我听说能够乘疾风的人,到天池都不算远;能借助龙舟的人,渡长江亦不为难事。自从陛下统御天下以来,四海清平、九域安定。您的仁德圣威犹如清凉的微风吹遍炎热的南方,葱岭之外的戎夷君长,每见从东方飞去的鸟,就认为是从我们大唐出发的,立即躬身礼敬。况且我这个有手有脚的人,亲自承受过圣教育化,仰仗陛下天威,所以能够来去无阻。”
太宗一笑,说:“这是法师长者的话,朕哪里敢当。”
接着,太宗详细地询问了往返的经过,从西出阳关直到印度境内,山川气候,物产风俗,帝王故迹,佛教遗踪,都问到了。而这些在史书中很少有记载,玄奘却谈得有条有理,要言不烦。唐太宗听了极为高兴。
唐太宗对陪同接见的侍臣说:“从前符坚称释道安为神器受到朝廷大臣们的尊重,朕今观法师词说典雅,见识渊博,不但无愧于古人,而且远胜古人。”
在旁的长孙无忌插言说:“确如陛下所说。臣曾经读过《三十国春秋》,知道释道安的确是知识渊博的高僧。可是那时佛教东传不久,经论不多。他虽然努力钻研,但多是一些枝节问题。哪里比得上法师亲到印度,探本求源,下过一番功夫?”
太宗说:“你说得对。”又对玄奘说:“佛国遥远,那里的圣迹和法教,前代文书都不清楚。法师既然亲眼目睹,应该写一部书,给人们看看。”玄奘听了,当即应允。
太宗同玄奘笑谈了半天,觉得他博学多闻,口才流利,很有公卿的才能,就劝他还俗,辅助朝廷处理政务。
这真是出乎玄奘的预料,他做梦也想不到唐太宗会说出让他还俗的话来,玄奘对唐太宗说:“玄奘从小出家,笃信佛教,对孔教一向生疏。陛下令我还俗,无异于把行舟搁在岸上,让它变成朽木。玄奘希望毕生译经传法,以报国恩。这是玄奘平生的心愿,若能如此,玄奘将非常感激。”玄奘这样再三辞谢,唐太宗只好作罢。
本来唐太宗是在繁忙的军务中抽暇作短暂接见,原来的打算是一种礼节性的接见,谁知竟在不知不觉中,两人已经谈了一天。在旁的长孙无忌说:“法师住在鸿萨寺,太晚怕来不及赶回去了。”太宗这才想起,现在已经快天黑了,于是忙说:“匆匆谈了几句,意犹末尽。朕打算请法师随朕东行,一路观光。朕在军务之余,还可小叙,不知意下如何?”
玄奘辞谢道:“玄奘刚从远路归来,身体也不太好,恐不能陪驾东行。”
太宗又说:“法师孤身西行万里,如今东行不远,还用得着推辞吗?”玄奖答道:“陛下东征,军务繁忙。玄奘跟随,只会增加途中麻烦。再说兵家相战,戒律禁止观看,玄奘不敢不奏明。望陛下体察苦衷,则玄奘幸甚。”这样,太宗才又作罢。
玄奘乘机向太宗说:“玄奘从西域获得梵文经本六百多部,计有五千余卷,至今一字未译。如今得知高山之南、少室寺之北的少林寺,远离尘俗,泉林悠闲,是一个安静的去处,玄奘希望去那里译经,请陛下明察。”
太宗说:“不用在山里。法师西行后,朕给穆太后在长安造了弘福寺,寺中禅院十分清静,法师就在那里译经吧。”
玄奘又说:“现在百姓好奇,见玄奘从西方回来,都想来寺院里参观,这样寺院就成了闹市,虽然人们并未触犯纲纪,却明显妨碍法事,希望朝廷派人加以防守。”太宗说:“法师的意思是要保护佛经和译经人的安全,理应如此。您可在这里休息三、五日,然后返回长安到弘福寺组织人员开始译经,所有需要的东西,直接找玄龄平章办理。”
据《高僧传》记载,这次会见“从卯至酉,不觉时廷,迄于闭鼓。”也就是说,是从早晨五时一直谈到晚七时,前后将近十四个小时。
太宗召见玄奘,是玄奘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就唐太宗而言,这是他调整宗教政策的一个步骤,这不仅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同时也为译经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物质的保证。
这年三月,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入居弘福寺,之后又搬到慈恩寺。从此,他便集中精力投入翻译佛经的事业中,直到逝世前一个月才绝笔,前后共十九年。
玄奘深知,要把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翻译成汉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合适的助手,不建立严格的规章,缺乏相应的物质保证,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玄奘一回来就给房玄龄写信商讨,列举出所需人力和物资。房玄龄派专人把玄奘的要求告知唐太宗。太宗传旨:“按法师所需要的供给,一定要做到十分周全。”这样,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只用了两个月,一切准备就绪。
首先是翻译人员,均由政府下令从各地寺院调集。计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宇学”高僧一人,又有“证梵语梵文”高僧一人。此外,“笔受”、“书手”,也已报到,各种应用物品也都购置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