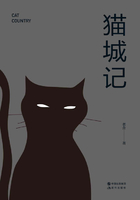在翻译开始之前,玄奘拟订了系统的翻译计划。玄奘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开拓者。他研究的重点是大乘瑜珈行派,但是他的学识并不局限于此。他还熟悉大乘中观和小乘各主要部派。他雄心勃勃,希望通过翻译和著述,把大小乘观点贯通起来,把大乘中的“空”、“有”学术分歧融合起来。因此,玄奘的翻译计划是高屋建瓴的,注意到各宗派理论的来龙去脉。首先,以大乘瑜珈派的根本论典《瑜珈师地论》为中心,安排翻译计划,这是他舍命求法的主要目标。其次以瑜珈源流之一的小乘佛教毗昙之学总结性论著《俱舍论》为中心,译出瑜珈派的重要论著。第三,再以中观宗的根本典籍《大般若》为中心翻译一系列著作,以使空、有之争得到调和。
在翻译前,玄奘还制订了详细的翻译程序和方法。玄奘在吸收前代官办译场译经的经验基础上,拟定了严密的集体合作、分工负责的翻译制度、程序和方法。当时,官办的译场,由译主和若干翻译、助理人员组成。译主,就是主译人,也是译场的总负责人。其他翻译、助理人员各有不同的分工:
义证:是译主的主要助手,负责审查译文的意思是否与梵本有出入或错误,与译主商量决定。
证文:需核通梵文,在译主宣读译本时,检查是否与原文有误。
书手:也叫度语,把梵文的音义写成中文,以使人名、地名、术语统一,前后一致。
笔受:负责记录译主的汉语译文。
缀文:对译文进行文字整理加工,使之合乎汉语语言结构。
参译:校勘原文是否有错,并将译文翻回去,回证原文,是否有误。
刊定:由于梵汉语文体制不同,因此要将译文的章、节整理得简明扼要。
润文:对译文进一步润色,使之流畅优美。
梵呗:译完之后,诵读译文,修正音节不和谐的地方,以便传诵。
当年五月,弘福寺举行译经仪式,正式开译。译主玄奘坐在正位上,手执梵本,面向翻译人员,用焚语大声诵读。坐在他左侧的“义证”与他评量梵文的含义,而坐在右侧的“证文”则查验诵读有无错误。这一步过去,再由译主宣译汉文,由坐在一边的“笔受”记录下来。然后,再经过“缀文”、“证译”、“校勘”、“润文”、“梵呗”等程序,一部书的翻译才算完成。这是名副其实的集体翻译,每次译经时,各类职责的人总数有时达两百人以上。
在这个翻译集体中,玄奘作为译主,真正做到了事事带头。为了做到有计划地翻译,他坚持做到今日事今日毕。他入住弘福寺时,已经四十六岁,搬到慈恩寺后,已年近半百。为此,他每天自定课程,如果白天因别事耽误,一定在夜里补上。往往是“三更暂眠,五更复起”,分秒必争。
玄奘翻译的态度更是严肃认真。尽管玄奘精通梵汉两种文字,熟悉佛教典籍,又深谙佛教理义,翻译起来得心应手,但仍一丝不苟地做好译前译后的细致工作。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原则,也就是既要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又要通俗易懂。因此,他的翻译以直译为主,辅以意译,务使表达精当,无损原意,形成一种“精严凝望”的翻译文体。对重译本,主要是力求完备,对旧译的长处尽量保留。由于梵汉文字不同,直译、意译都难尽其意,玄奘则创造性地在节末加若干注释性的说明,使文章更为明白晓畅。现代学者认为,玄奘的译文已进入“化境”,既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存原有的韵味。
玄奘回国后,十九年****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一千三百多万字。在数量上占隋唐时期的一大半,在质量上则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历史上称玄奘开创了“新译”时期,使唐代的翻译水平产生了一个飞跃,在中国翻译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一页。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十一日,唐太宗让玄奘至坊州宜君县凤凰谷太宗避暑的玉华宫相见。玄奘到达之后,太宗非常高兴,慰劳有加。太宗对玄奘的才识极其赏识,这次又对玄奘提起让他还俗的事来,当初在洛阳宫奉见之际,太宗就劝他还俗辅政,和上次一样,玄奘仍然坚决辞谢,太宗知道玄奘的译经与弘扬佛法之志不可夺,即答应给予支持;又询问《瑜伽师地论》,玄奘为唐太宗讲述了大意,又让人到长安取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详加御览,览毕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侍臣赞叹佛教广大而高深莫测,因敕所司选秘书省书手抄写新翻经论为九本,分别赐给雍、洛、并、兖、相、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七月十三日,太宗施玄奘衲袈裟一领以示关怀。
八月,太宗应玄奘之请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宗于明月殿召集百官,命玄奘坐,使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将《大唐三藏圣教序》当众宣读:
盖闻二仪有象,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苞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象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象显可征,虽愚不惑,形潜莫睹,在智犹迷,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弘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抑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像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旨归,曲学易尊,邪正于焉纷纠。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被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塗间失地,惊沙夕起霜,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露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探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爰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乾焰,共拔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唯人所讬。譬夫桂生高岭,零露方得法其华,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微物不能累,所凭者净则浊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成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舆乾坤而永大。
另外,皇太子李治也作了一篇《述圣记》。太宗及太子李治所写的两篇序文一出,王公大臣及僧俗欢喜雀跃。弘福寺主持圆定及京城高僧联名奏请镌二圣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得到太宗的许可。于是,弘福寺僧怀仁等集王羲之的字(行书),写刻于碑石;后来,大书法家、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又以楷书写了两本,一本刻在长安慈恩寺,一本刻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倅厅。这些碑文到现在都成了有名的字帖。
有一次,太宗在玉华宫问玄奘“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回答:“弘法度僧为最。”太宗即下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全国三千七百一十六座寺院,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这算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度僧活动了。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八月,太宗突然派人召玄奘入宫,面对玄奘,唐太宗提出了一个要求,这要求可难坏了玄奘,到底这是个什么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