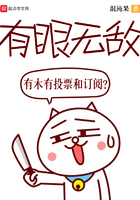一年之末了!十二月二十八的拂晓,气候严寒,灰色的天空笼罩下之大武汉,被那狂驰的北风扫荡着每一个角落。
在隆安号栈中的我们,都已从梦中醒来,忙着打铺盖,吃早饭。父亲和旅馆主人办妥手续后,立刻就要准备出发。
黄陂街的小巷的一个角落里——就是隆安号栈的门口,停了数部黄包车,我们的行李和人一一上车之后,便向来送行的“寄爹”等人告别。
车子到了汉口码头停下,付车资,购渡江轮船票。
码头处没有人,非常冷清。
祖母行动不便,父亲正找人把老太太驮下去,我便和湘铭两人先下码头。我手中提着一只箱子,湘铭背上背了一个铺盖,经过木板的长码头而到了趸船上。我只注意着自己的东西,不注意湘铭把铺盖向哪里一放,只听见他口中喊着要去驮祖母,就跑过去。当我奔出趸船回头时,祖母已由父亲雇了一个汉子驮来了,接着后面又连续地来了许多人。
一只渡轮已由武昌开到了这里,我高声地喊他们快些上渡轮,但“叔叔”等人还在后面,行李已一件件地由莲芬及湘铭等人装到轮船上去了,而人还没有到齐。我赶忙奔回趸船,只见莲芬已在船上守着行李,湘铭还想搬一只箱子过去。趸船上的警员开始关铁栅了,“叔叔”一口气赶到趸船,和警员挣扎着到了栅外,又被警员一把拖回。我们已可听见那只渡轮的机器声,并且见到它逐渐脱离趸船了。
望着那只在江心渐渐消失的渡轮,本没有什么可遗憾之处,因为不到数分钟便可乘第二只渡轮。不过那船上有许多行李,莲芬一人到了武昌怎么拿上岸呢?有人以为到了那边一定会叫脚夫搬上去的,又以为她没有钱怎么雇脚夫呢?况且只有她一个人,行李说不定给脚夫偷了去?……
时间不肯等人,我们上了第二只渡轮,这里剩下的行李虽然点来点去,但不知道那边有几件,所以无从计算是否有丢失的。
到了武昌,见莲芬在码头上等待,行李也都上岸了,她说她将行李用绳子一捆,肩上扛一担,两手提若干,这样地上岸的。我们一到武昌见到了莲芬,喜出望外,以为没有出乱子,连点行李件数的工作也忘记了。
天下着微雨,怪阴的。父亲又雇人驮祖母上那壁直的高数十级的石级,我们各自提了行李登码头,其它笨重的行李又雇脚夫搬上去。人在雨点下奔走着,衣服和帽子都有点微湿,口中呼出的气浓烈地向上飞跃。
毛雨最惹人讨厌,虽然比大雨要小一点,而空气仍是阴凄凄的,不像下大雨那么爽快。
人和行李皆已在码头上集合了,又忙着雇黄包车。一部当然不够,我们在风雨中赶前赶后地吆喝着。
马路对面的汽车间里驶出了一辆汽车,和其它汽车交叉行驶起来,一阵“苏苏”的声音后,车轮底下飞溅出无数的污水。
黄包车若干部都唤来了,我们过马路到了那边和车夫讲价钱,一面嫌多,一面嫌少。车子刚才不够,现在又嫌多,一边抢装行李,一边抢装人。我上了一部车子,又被撵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才和母亲合坐一部黄包车行进。只有平安一人是跟车子步行的。
在车中觉得气候极冷,手也有些僵了,如果吃饭的话,手一定不会把筷子抓得很利索了。
在中途,我们见到雪花了。一点点的白色的雪花,起初是少量的,慢慢地下降,到后来增多起来,雪花纷乱飞来了。
到武昌总站时,正是风雪交加的时候。地下泥泞不堪,人站在水洼中看守着行李,父亲到站台上去望火车。
风声,雨丝,雪片中望着那来去不绝的士兵和情绪紧张的乘客。
父亲的影子渐近了我们,他高声叫我们过去,我们各自提了负责的行李奔到那边,父亲指着前面一节火车车厢说:
“上去,上去……”
我们找着了车厢的门,里面已有若干乘客,同时也有两三乘客在上车。我看清了车厢上写着“二等”两个字,便放心地跨上车去。母亲和“叔叔”等也都上车了。我一到里面,便好像进入大火炉。里面的情形是,座位和桌子还不算坏,所以印象小至于像瑞和轮的船舱那样。
玻璃窗上厚厚地遮上一层水蒸气的幕,有些地方已化成了水滴下来。我可以透过窗子,模糊地看见父亲等人在赶着前来上车,他们刚在站上将行李处置好——“结”行李。
父亲上了车后,又立刻离开这节车厢。他回来时,只听见他说:
“车厢房间没有了!早被人家抢走了!”
“怎么?……为什么?……你买票时那人说一定有……怎的他们这……为什……?”大家听见了,聚集拢来七嘴八舌,都有些愤慨。
父亲说:“事已如此,现在绝无办法,房间早被人家占去了。”
“那末祖母如何睡觉呢?”
“就只可以睡在这凳子上了。”
凳子上?这真是无奈了!非常时期到底非常,手脚慢一点就要弄出事情来。但反过来一想,国家在患难之中,将士在前方浴血抗战,有车可乘已是万幸,既然没有办法,那只有一声不响地各自找着各自的地盘坐下了。
荣哥和我、湘铭、莲芬、平安等五人,挤不进藤椅的座位,只得跑到这节车厢的末端,那厕所门前的一块小地方,坐在红漆的小板凳上。门外便是这节车厢和另一节车厢的连接处。假使在车子开动的时候任意跑去逛,那末跌落下去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窗外的风雪中,有儿童的叫喊卖报声。
父亲等在那旁边点起行李来,发觉少了一只铺盖,里面并卷有小皮箱一只,箱内有墨水、铅笔、颜料及母亲的眼镜等物,我们去帮忙找寻,但东找西找找不到。湘铭到站上寻了一周也是没有。但他提议说到站上去打电话到汉口武昌两渡轮码头问询,可是时间怎能容许?立刻就要开车了。
站上响了钟声,接着便是火车头的汽笛声,火车开动了,车轮先在铁轨上作迟慢的摩擦声。我们向武汉告别了。站上人很少,更看不见有送行人挥着的手帕,只有那雨丝和雪片在飞舞。那逐渐加快的轮声锵锵之中,只见武昌站的最后一根木栅在窗外越过了我的视线。
没多久,我们可望见窗外秀美的山峦和明亮的湖水。并且在那里有许多新式的洋房,父亲说这大概就是武汉大学。
我的思潮随车轮转变,突然想到在汉口码头我同了湘铭在木板道上行走时,清楚地看见他背上扛了一只铺盖,到了趸船上就不知他丢在什么地方而奔回去,我们到了武昌又没有查,对了!这铺盖一定是他丢掉的了!我急忙去找湘铭问他,他正在那边讨论这件事,我奔过去高声地问:
“喂!喂!我看见你在码头上扛的那铺盖,你放在什么地方才回去的?……”
“不!不!我没有那箱子,不!我没拿铺盖……那是……”湘铭说。我听了有些愤怒,他素来是我的好友,怎么现在抵赖起来了?于是对他高声说:
“我明明看见你扛的,怎么……”
“不是……那是她在船上……”他用极高的声音盖住我的话。
“我的的确确看见你在码头上……”我天生不甘屈服。
“对你说不是!那失掉的是莲芬在船上的……”他的声音更高,架势是在骂我了。
我更忿怒,当众宣布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旁,是我亲眼看见的。他现在的抵赖委实造成我极大的忿怒,于是我更不能示弱,又高声地:“我亲眼看见你……”我的话没说完一句,他咆哮了!涨红了脸,提高了嗓子压我的话:“不是!说不是还要……”他一面说一面便走回自己的座位。我心中极为不快,好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拿不出来,因为他阻止我说话。我气闷中踌躇了一会儿,决定还要对他弄个明白,便跑到他那里用了很大气力发表我的意见,可是每次都给他的高声阻止。我心中愈弄愈怒,他简直骂起我来了:
“还是荣少爷好!你怎么如此瞎缠?我跟了屠李二位老太太从镇江到汉口管理四十余件行李,半件都没有遗失,难道这次我会如此糊涂?”
我完全失败了!如果再争论下去,无疑地更是瞎缠了!我心中受到极大的委曲。我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侮辱了,我奔出了门外,望着脚下滑过的枕木,听着那永不变更的重滞的车轮声,我没有地方发泄我的愤怒,我像小孩子似的哭了……
我竭力使我不发出哭泣的声音,我拭我的眼泪。荣哥走来了,对我低低地说:
“你何必同他争论,你应该明白你现在的身份,不能再像少爷的样子了啊!”
上午,我们的火车到长沙了。长沙的车站比较大一点,但非常陈旧。那位军人王焰生,告别我们,要下车了,他还以为我们是到湘潭的,临行时说:大家在湖南,将来或许还有碰面的机会。我看着他跳下车去,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火车离站时,我们可以看到长沙的风光。铁道似乎造在街道上似的,我们看见两旁有许多住屋和店铺。渐渐地,火车行进在山峦之中了。
父亲唤我到那边去,说刚才有位乘客下车去了,有了空位置,我便移到那边去,荣哥等人还在原处。
我的座旁,一位是九江人,预备到了广州,转澳门到香港去。一位上海口音的青年,到衡阳去的。坐在父亲座旁的,是一位说北方话的青年,本在津浦路上当职员,现在因战争发生,留职停薪,也和我们一样要到上海去。我没有事做,便和他谈谈话,用聊天来消遣。
午过株洲。
我的一个小册子在荣哥那里,因为他要用它写生。我睡了一晚,把要记的地名遗忘了,记地名的工作因而停顿。
傍晚,我在父亲的桌子上发现了两本别人遗下的《文摘》和其它杂志,便取过来阅看,有一篇鲁迅的《说胡须》,很感兴趣。
晚上,车到衡阳。从只有几盏灯的光线下望见那潮湿的站上,堆得像山一样的货物;那地下支离的水迹倒映着几盏支离琐碎的灯的亮点。但当我一放开了那长久收缩着的视线时,便见到那伟大的重重高山模糊的黑影,包围着整个衡阳站,那是多么伟大而雄壮啊!
那位上海口音的青年下车了,但他发现失去了一只皮箱,赶上赶下地寻找着,仍是没有,据说里面的留声机等物价值数百元之多,比我们失去的铺盖贵重得多了。
小除夕——三十日——的中午,车子过郴县。
火车穿过不少长长的山洞,次数之多,也算不清了。在京沪路上视为希奇的穿山洞,这里是家常便饭了。
一路见南岳衡山山峰之连绵不断:崇山峻峣,怪石嶙峋,花果奇异,树木萧森,峥嵘的悬崖,崎岖的山道,岚烟混沌,弥漫于高峰之下,溪流淙淙,锦鳞游泳,涟漪平躺于碎玉或玲珑的白石之上。这些,都是在粤汉铁路上特有的视觉享受,将令我永远不会忘记。
中途的一个站上,和许多人一起跳下去玩,并且在火车头旁观看。
下午,过砰石,已在广东边界了。砰石站的后面,有千仞绝壁矗立着。崔巍而嵌崟,好像那绝壁上面还有一条条纹路,是我所仅见的。
三天的工夫,一直未遇到空袭的惊吓,可是我们却看到了以前铁路被炸的遗迹,在隔了一条河见到了以前炸毁的一段旧铁道及轰倒的火车头。无疑我们所乘火车下面的一段铁道是新铺建的了。
那地方的风景又逐渐美丽起来,碧绿和深绿的树木和花草,和没有止境的无穷的浓阴,高高低低浓浓厚厚地布满于重重叠叠的峰峦之上,布满在碧绿澄清的溪涧之旁。起初我还以为那条碧绿的溪水不过在铁道下数尺的地方罢了。但待我看到两个人在浅水中曳木筏到浓阴深森的树叶洞里去的时候,才发觉那条溪水和我们的铁道高下相隔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我见那两个人简直像蟋蟀那么小。
凡在旅途中,我有一个困难,便是大解不通。火车里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只得硬着头皮进那极其污秽的厕所。本来二等车的厕所是很清洁的,可现在是非常时期。无人收拾,弄得满地是粪,马桶圈上也是粪,我没法,只得多用掉几张草纸。
车厢中,因缺乏服务员,也是极肮脏的。橘子皮糖果纸,在座位底下堆积成山了,脚就在那上面行走,最坏的便是橘子皮腐烂的臭气。幸而在某次火车停在一个站上的时候,平安去弄了一把扫帚把所有垃圾污物扫出车外,乘客无一不表示感谢。
我独自到三等车厢看了一下,那里比二等车厢更糟。
祖母和车厢中的一个常州同乡攀谈起来了,那是一位三四十岁的女人。她说自己的儿子现在尚在宜兴或其它地方,她的儿子本在省立常州中学读书,常中迁宜兴时,她的儿子不愿去,但她却强迫儿子去。而在她儿子去后不几天,即因时局不对而自己同了别人逃离常州了,所以她的儿子至今无消息。祖母闻此事极为感叹。
半夜里,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停了好久,又开进站来一部火车,是国际列车。不行了,我们的火车本在国际列车之前,现在被车站当局故意捺慢,说不定要给国际列车先行了。事实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国际列车先行了。
一会儿的瞌睡,醒来见火车一动也不动,便把头伸出窗外探望,却见前面的火车头正由另一轨道行到车尾去。不久火车便开动了,好像方向不对,是的,怎么开倒车了吗?我还不信,用力注视看那窗外的景物,是反方向的,火车是在退后的啊!困难来了!困难来了!事情没有理想的那么容易。到底什么事,我们全不知道,难道前面轨道不通了吗?有空袭吗?敌军在广东登陆了吗?那末国际列车又为什么可以行进呢?这里没有报纸,一切无从得知。看吧!看它拖我们回武昌去!全车的乘客大多在发怒了。我却继续我的睡眠。
大除夕——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早晨,我发觉我们的火车停在一小站上。
好久没有动静,令人气闷之极。一会儿,火车开动了!啊!原来又是倒行的,因为车头还没有掉到前面去。但火车行得很慢,没有多大工夫,便开进了一个山洞,车厢内顿时黑暗起来,待车头和车尾全部进了山洞之后,火车便停下了。不错,在汉口时我曾见报载铁道上火车在敌机空袭时避难的宝地是山洞;大概刚才站上有空袭警报,所以车子开到这里来的。
大衣袋里的一个沃古林眼药水盒子装的樟脑粉——预备牙痛用的——倒翻了出来,以致各处都是樟脑味儿。
中午,火车仍开回到原站,但火车头并不掉到前面去,火车也不再开动。
肚子饿了,预备吃的面包早已吃光了。有许多人下车到站上去找食物,我也在窗口购了一些东西充饥,荣哥却跟了一大批人到附近的小镇上去吃饭。
荣哥的离开火车我们并没有太注意,可是火车开动了!我非常着急!幸而事情还不过分糟糕,火车仍是开进山洞。不过心中不知回站时荣哥在不在那里,仍急了整个下午。
午后,大概敌机已经远去,我们的火车又慢慢地开出了山洞,停在原来的小站上。大批的乘客早在那里等待了,见车子一到,便一个个地上车来,荣哥也在其中。他上来了见我们刚从焦急转到安定的态度,便说:
“不要紧!我们有一大批人同去,其中有一人是这火车的列车长,所以放心胆大了。”
我们又问他去什么地方吃了些什么,他说吃的是米饭,那地方也算有街市,而房屋之低矮、街路之狭小,和常州的前黄比起来,前黄是天堂了。
我们看见火车头已从车尾处绕了大圈子掉到前面了,总算定下心来。不久站上的口笛响了,火车开始行进了。
傍晚,车过乐昌。
在那晚霞出岫的当儿,火车奔驰于原野,我的头伸出窗外,瞻仰着广东的风光,尤其引起我兴趣的便是那好像长蛇蜿蜒的公路。
天未黑前,车过曲江。曲江站比较考究些,火车还经过铁桥。
天黑了,见许多运输汽车的两盏灯,远远地蠕动着。
午夜,车过英德,但并没有经过英德市镇,车站在英德附近的小镇上。
车过军田。
似乎风平浪静了,行进是没有问题了,可是不行!火车停在一个小站上,不开动,原来又是在等待国际列车,国际列车有好多部,我们统统让它们先行。国际列车进了站一直没有停,不过行驶得稍慢一点。只见一个穿大衣的人手中持了一具路签,奔到国际列车车头,给了火车司机,立刻那部列车加速了,离开车站了。
一部国际列车先行了,我们后行也无妨,可是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据一位青年——也是乘客之一,曾在津浦路上做职员——说:路签已给国际列车先拿到,那末我们这部车子,必须要等国际列车到了下一站,由那边站长发了路签给这边站长——发路签类似打电报——这边站长将路签给了我们火车的司机,我们的车才可行驶。
料想起来,国际列车可早到达下一站了,而我们的火车一动也不动,只看见龙头在冒烟。
乘客一批批到站上去问讯,得知那边还没发路签,其它一无理由。
我们的那位青年发表意见了,他说我们这部车子没有路签也可以开,本来用路签的意义是避免两车相撞,现在只要我们的车子开出站后,这里的站长在未接到本车到达下一站之讯息时不发路签给那边的站长,那末那边一定不能开车子过来,当然不会发生两车相撞的事了。除了那边也以此法放行火车过来。这办法虽然大家一致赞同,可是火车司机却不立刻开车,因为若无路签而开车,即有极重大的罪责,最后由这里的站长及本车列车长和全体乘客作保,于是我们的火车才得以浩浩荡荡地开出站去!
哪知不久就是广州小站,天已黎明。
火车再行了一个不十分长的时间,天际已亮了,并且立刻就要到广州了。我们互相提醒着当心各自的行李,荣哥及湘铭等人也集合到这边来了,各人收拾用具,穿上大衣,准备下车了。当火车渐渐停下来,车轮下发出了放气声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次逃难途中的粤汉长途,总算告了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