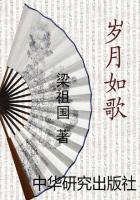上次“叔叔”“寄爹”等参加杨裕三先生的盛宴,说是鱼圆(丸)烧得最好吃,在江苏从未吃过。讲起鱼圆,本是新堤的一种特色菜。新堤靠长江,渔业极为发达,所以新堤人对于制鱼类食物,也特具超技。我们在栈内吃饭,鱼每天都有,尤以鳜鱼为多,味道也很不错。市上的鱼行里,我们可以看见成千上万的咸鱼,一股浓腥刺鼻。鱼市上的鱼大都新鲜活跳,几尺长的大鱼是不足为奇的。价钱也相当便宜,所以吃鱼很是合算。
讲到鱼,又想到肉,我第一天到新堤的印象便是见满街跑着的猪。新堤的猪都是白毛的,黑毛猪很少见到;但白毛猪的尾巴总是黑的,白尾猪更是少见。这里的居民,差不多每家都畜猪。所以猪并不十分贵,而肉又很肥。
除了鱼肉之外,菜中常用的还有野鸭和雁。有人说野鸭就是雁,有人说雁为大者,野鸭为小者,我不曾研究过,所以不得而知。在江苏从没有雁吃,就是有了,价钱总是贵得可以。而在湖北,常有雁类飞过,所以猎人猎下的雁和野鸭在新堤市上也是大宗的食品。不过雁都是用枪打下的,枪孔处的肉有毒,所以烧雁的厨子若是手续不干净,吃了很不卫生。我们栈内有一位贩雁的商人,运来了十数桶雁,他们一桶桶打开上盐时,只见都是血肉淋漓的东西,骇得大舅婆和太姻伯母从此吃饭不下雁肉碗的筷。
这里新堤的币制还没有统一,法币当然是流通了,而我们通用的铜板在这里却不能用。他们还是用的大铜板,而大铜板还有两种:一种可当两个铜板用,另一种可当五个铜板用;均须用国票兑换。我们在汉口留下的铜板都没处用,只好将来有机会再带回汉口去用了。新堤这地方在湖北,币制还不完全统一,再到内地,币制恐怕还要紊乱呢。这里的一般人,很不开通,有听说一生没有见过火车的,铜板用的还是清朝铜板,街上简直看不到一个穿西装的人,还有禁止缠足委员会等机关设立。社会的守旧情况,可见一斑。平民倒大都老实诚恳,而滑头滑脑的人是比较少见。
大嫂慧兼本住在旅馆楼上,现在由仲方表兄接到新堤西桥巷二号自己家里去住。她的三个孩子却常到旅馆里来玩。乐平每日白天虽然玩得起劲,但是晚上就总是哭,因为思念他的在天津的爸爸啦!
那天慧兼同了她的三个孩子到旅馆来玩,珑妹加入他们的游戏,他们称珑妹:
“小姑姑”。
这位小姑姑同他们很费力地讲着南腔北调的官话,真是滑稽。
乐勤和乐新到我们房里来了,这时我、荣哥和湘铭都在,见了他们自然非常欢迎。恰巧这时来了一个卖花生的小伙子,我们便买了一些花生款待。调皮的乐新吃了还不够,嚷着再买,湘铭便从袋里掏出了一毛发亮的硬币,一面对熟识的卖花生者挤一下眼,意思要同乐新开个玩笑,看看小滑头怎么样儿。乐新拿了一毛法币去,递给卖花生的,说:
“要买一毛钱花生米儿……”
卖花生的不给,暗里把钱还给了湘铭。湘铭向乐新讨钱,而乐新向卖花生的讨花生,卖花生的一溜烟跑掉了。乐新无法应付,湘铭还说要告诉他的妈妈,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但这孩子到底是无邪的,第二天仍旧谈笑依旧,我们也不再对他提及这事了。
我们一天的生活,不外乎睡觉吃饭逛街开话匣子。荣哥说,把功课荒废了,也不是事儿。便从箱子里抽出一本《英文最常用四千字表》和一本袖珍小字典来,这本《英文最常用四千字表》里的四千个英文字,若能熟记,则对于阅读英文书籍极有帮助,所以荣哥预备在这上面用一点功,由我担任翻字典求释义和考查他成绩的工作,一方面也可以带把温习温习。
几天阴雨,街道泥烂得无法可逛,只好闷在房里查字典上的生字。报纸上的消息见了要心跳,敌军直入南京,又打到芜湖了!
天天同湘铭到码头上去打听船的消息,祖母的指课卜得非常之灵,说不来就不来,虽然母亲在汉口来信说不日就要回来了。
毕竟在一天午后,我们在旅馆里听见了火轮的汽笛声,荣哥、湘铭和我以及其它许多人“登顿登顿”赶到码头上去。父亲母亲及详姨等人都乘火轮来了,一大批人到了旅馆。母亲的小藤包里带来了许多东西,如橘子、手电筒及小搪瓷碟等物。吃晚饭时,详姨令开二桌,因为人增多了的缘故。一时非常热闹,而菜中又有一种生萝卜片,有一些辣而味极美。但荣哥说:
“辣的东西很败胃,而且又具有一种‘嗜好品’的性质,会上瘾,吃惯了不吃便不够刺激,还是少吃一些好。”
我虽然很爱吃,但听了荣哥的话也就少吃了些。
当夜我和荣哥搬到楼上去住,因为下面的房间住不下人了。湘铭也上楼住入一小房内,我们就住入上次慧兼的房。床好像是炕,在墙壁上。最妙的是壁上挂着四联单条,上面写的是: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杜甫的诗句。
心想,慧兼见了不知作何感想。
母亲说,预备在汉口法租界租屋去住。因为住在新堤音讯不通,银行的迁动又是隔膜,所以不预备再住下去。李抱宏在汉口赁了一所房子,说是和我们合赁,已付了十块定洋。但母亲一想:抱宏这人过分精明,和我们性格不同,一定不能长久过共同生活,而这所房子的租费又很昂贵,所以马上还给抱宏五块钱,以免有所后患。居住问题容后再考虑。
祖母和“叔叔”从常州到汉口的旅费都由详姨垫付,所以父亲母亲在汉口同抱宏和详芝算了账。算法是这样的:详姨把所有的用费那怕半个铜板只要是在逃难期内支出的,都记入了账簿,共有若干元。点点人数有若干名,用来一除,每人用去若干元。我家三人,祖母、“叔叔”、平安占三份钱,如数付出。但又有“抑尤有进者”了,是湘铭的路费也由我们负担。因为母亲在常州曾对详姨说过,带了湘铭走,祖母在沿途须由湘铭照应,即如码头上驮上驮下等事,旅费我们来付。但详姨虽带出湘铭,而并未告诉他这个约定底细,所以湘铭沿途也并未十分照应祖母。我们出了他的路费,他自己还蒙在鼓里!
夜已深了,湘铭房内的煤油灯已旋暗,人也睡了,荣和我在他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便挨身进去,仍把门关上了。湘铭睡眼惺忪,爬起来问道:
“什么事?什么事?”
荣哥把煤油灯旋亮了,与他稍谈了三两句之后,便轻轻地问他道:
“你可知道你的路费是谁出的?”
“是太太(即大舅婆)家出的呀!”
说了一些转弯的话之后,荣哥很庄重地说:
“是我们出的。”
“什么?什么?那不可能!……”
湘铭大为惊讶,并且不能置信,经我们一番解释了之后,他坚决地说:
“明天一定要去问二小姐(详姨)!一定一定!”
虽然我劝他不必再去多事,以致弄成僵局,但他却无论如何要去问一下才甘心。
次日这事终于被大舅婆知道了,她老人家极为震怒。湘铭去问了一下,知道事情确是如此,因此亦忿忿然,并问详姨说:
“你们把所有的账统统记下,那末我为蒋家老太太(我祖母)买了一块钱香肠,你们也吃的,可曾记账扣算没有?”
详姨说:“那倒没有。”
湘铭说得紫头赤颈地出来。
详姨奉大舅婆命令,把钱来还给母亲,母亲当然不会接受,于是钱推来推去,事情愈弄愈“鸭屎臭”,最后我们当然仍旧没有接受。
那天,我们跟了母亲到仲方家去拜访,他们竭诚招待。房子在西桥巷,路很近,在市街一转弯就到。大门对着新堤商会。进门有一长方形天井,其角落里有一小木房子,好像夜巡警的岗室,进去一看,是厕所。天井里有青苔,走路须小心滑跤。这青苔据说是每年水涨时江水渗过地面而生的。从天井旁的一扇门里进去,便是一个砖铺地的厅,或称中堂,挂着一些字画,摆着茶几。厅的两侧有房间,左面的房间是仲方等住的;右面的房间便是这里的房东张大婆的房(“大婆”是新堤地方的尊称)。仲方的房间光线很充足,他吃的食物也很“现代化”,在这古旧的新堤倒是少见的新家庭。后面是“寄爹”睡的房间,她是美术家,所以室内装饰也很富于艺术。慧兼住在另一间房内。仲方有两个孩子,大的叫阿英,小的叫阿真,年纪都尚小。我们又被邀到张大婆的房内去参观,则是一片古董货的气息。母亲与令德(仲方妻,我称她二嫂)等谈话时,我去和“寄爹”聊天,回家时我又向“寄爹”借了数本《生活摄影画报》回旅馆翻阅。
父母亲对于我们的居处问题,已考虑多次。本想到汉口租界去住,但一时不易实行。而现在住在新堤旅馆里又决非长久之计,便想暂且在新堤赁屋住一阵子。于是我整天同了仲方、慧兼等跑巷头,想看到一所合适的房屋,但一切都是旧陋的,最后在一条有扫荡报新堤运销处的街上,看上了一所房子,但并没有仲方的房子好,因为光线不足,所以还没有决定赁它。
我与荣哥又因茶房之要求搬入隔壁的房内居住。
房内挂着一副对联:
“比于石崇咄嗟可辨,如逢诸葛淡泊自甘。”
又有四联单条,写的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诗句。
每日无聊之极,只有无意思之嬉戏,或在楼厅的木炕上伏看一张中华民国全图。一日荣哥在满是尘埃的楼面后部发见了一块活落地板,用力把它撬开,一看,通着下面的小厅(在饭厅的对面)。惹得小孩子们大开玩兴,把皮球抛上抛下。但这事颇有危险性,后遂被大人禁止。
十二月七八日间,父亲为母亲汇在长沙的一千元大洋牵挂,决定亲自到长沙一行,以办理清楚。荣哥也要去,一方面可给父亲接接手,另一方面则他自己要借此机会去看望章育中。至于到长沙去的路程,本应先到武昌,然后乘粤汉铁路火车前往,今听栈内有人言:可以先到岳阳,由岳阳乘火车到长沙,既近又方便。在新堤不远处有一码头同老官庙,那里有火轮班开往岳阳。父亲决定就走此路。
十二月十一日午后,我写了一封给重庆双桅子水沟二号余宗英先生的信,大意为请余老师关照,熟人多方便,以期我们将来可以入川等语。父亲目前亦曾写信给四川某友请求一职位。
十二日上午,父亲和荣哥打点行装就道。我去寄航空快信给余老师,从张街的邮政局转堤街(即市街街名)回来,到江边码头上去一望,见无人。回到旅馆,听说父亲和荣哥已乘小舟出发了。
谁知事情没有如此便当,傍晚时父亲和荣哥仍旧倒车回来,只看了一天乡村小学的情形。荣哥去长沙梦不成,而父亲却不能久待。十三日恰有一班轮船开往汉口,父亲便同了详姨及姨夫抱宏到汉口去了。
母亲和珑妹也搬到我们房内居住,有两张床,倒不十分见挤。
慧兼同了她孩子来,与母亲说:
“兰姑,孩子们每天野得不得了,我请你帮忙,每天上午叫他们到你这里来上功课!”
母亲答应了,于是每天有一班小学生到我们房里来上课。读的书是他们原来在学校中用的书籍。珑妹也一同上课。不过这所学校不久就解散了。我却天天为荣哥查字典流汗。
荣哥有拉链一条,每日作拉力运动,可以促肌肉发达。这拉链我们名之谓“扩胸器”,钢的,有弹性。上次在汉口又购了一条绿色牛皮筋加上去。湘铭见了,便上来拉着试力,并且又立刻去请旅馆内若干茶房来拉。还以为不够,最后拿了“扩胸器”到堤街鱼市前,会同若干茶房来,他当众表演,引得许多人围观,而以为荣耀了。
新堤有发电厂一所(我们却没有找到),所以也有电灯的装置。但装电灯的人家很少,除了一部分在热闹区的店铺外,其余的人家均点煤油灯及煤气灯。我们的旅馆在热闹区,所以有电灯设备。荣哥便想将“叔叔”从常州带来的收音机取出,设法通电试验收音。他把收音机搬到楼上,许多茶房七手八脚,少见多怪地来愈帮愈忙;将一盏电灯的灯泡摘除,由灯头通电到收音机里去,收音机内的五盏灯泡倒是亮了,但一无声音。原来这里电厂里的电压和我们常州的不同,所以试验不成,完毕甘心。
上次向“寄爹”借的《生活画报》已看完。荣哥在卖花生米的店里发见了旧英文报纸,是良好的英语读物,于是向那店里大量购买!价钱相当贵,却不能计较了,购回来大看特看。后我又向“寄爹”借了上下册《说岳全传》来看,成天浸在小说里,人不胜有些头脑昏涨。几天的工夫也在昏头昏脑中无形地度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