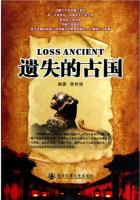丁:前一段,德国汉学家顾彬对当代中国作家的批评,曾引起一些作家和学者的争议。从学理上说,顾彬的批评只是一个特定的角度,确实可能有相当多的地方需要进一步论证。但他对中国当代作家基本素养的判断,我以为还是发人深省的。特别是他对中国作家关心当下现实的良知和勇气非常不满意,这绝非无的放矢。
谢:最近,不少人都在谈论一部德国电影《别人的生活》。我也看了这部反映前民主德国现实生活的影片,感慨万端。其实,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民主德国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而言是最高的。但人活着,并不只是需要物质生活,有房有车是不够的。人需要有尊严的生活,需要免于恐惧的自由。艺术家总是向往自由的表达。亲人之间的出卖是可怕的,人对人的保护是可敬的。影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对于我们来说,更不感到陌生。导演才三十几岁,就能如此深入地表现他们国家那一段令人窒息的历史,实在难得。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素材,可惜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没有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丁:在中国,关注现实、勇于表达的作家艺术家也是有的。他们的作品在精神品质方面,也可以和《别人的生活》媲美。只是他们往往处于文艺界的边缘地带,没有机会像《别人的生活》那样走向世界,夺冠折桂,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顾彬批评的,我想不是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国作家,而是主流的作家。中国目前主流的文学和艺术,在社会良知和洞察力方面,的确乏善可陈。不要说和外国优秀的同行比,就是和改革开放的早期相比,精神状态也出现了整体下滑。那时候,对自由的向往是中国文艺的主潮。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台新戏、一幅新画出现,感动的不光是读者和观众,也激发着同行创新的冲动。兄弟艺术互相启发,大家争相突破禁锢,好像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不同了,即使个别作家艺术家有追求,有突破,也得不到同行足够的关注,继续处于边缘地带。某些作品受到圈外读者或观众的好评之后,同行往往不愿意正视他们的存在,有时还冷嘲热讽,说出的话酸溜溜的。
谢:你是指王小波那种情况吧?他活着的时候被称为“文坛外高手”。
丁:主流文学界冷落王小波是十年以前的事了。现在,胡发云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境遇和王小波很相似。当然,主流文学界只是一个宽泛模糊的说法。主旋律是一种主流,学院派喜欢的纯文学、先锋艺术也是一种主流。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中国当代纯文学的潮流似乎与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爱好相关。中国当代一批作家和批评家,受马悦然直接间接的影响,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这种因素最初不是主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因为马悦然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实际上左右了不少有才华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艺术定位。他们心中的象牙之塔,与中国的现实渐行渐远。
谢: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虽然他是高本汉的学生,但他对中国语言的理解力不无局限。因为他有过研究中国方言的学术经历,所以他比较偏爱具有区域语言特色的文学作品。但另外一些即使在语言上也产生了创造力的当代作家,未必能引起他的兴趣,比如对中国语言已经产生影响的王朔、王小波,还有在汉语的纯净、美丽和丰富性方面做出成就的章诒和。我想,无须苛求马悦然的偏爱。就是我们自己阅读中国文学,也有诸多盲点。马悦然对谁感兴趣,是他的自由。我只想讨论,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关心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否必要。
谢:像《别人的生活》这样的作品,只有那种对现实生活,对人的自由始终敏感的作家才会把握住。我们的生活其实比《别人的生活》更丰富。我想,这还不只是一个写出这样的作品能不能出版、拍摄出这样的影片能不能公映的问题,而是涉及,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如何把握我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主流的文学艺术,不是让人对生活更敏感,对自由和尊严更敏感,而是长期引导人们在娱乐中陶醉,在搞笑中麻木,或者在自恋中出世,那将不只是艺术的缺欠,而且是民族精神的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