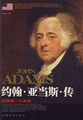康熙皇帝在执政期间,曾称赞秦始皇“兼六国,罢封建,置郡县,是一统之盛”。同时也抨击了汉初的分封制:“武帝分锡茅土,鲜克有终,于此可见封建之不可复行矣。”由于他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因而面对南方“三藩”割据数省、北疆噶尔丹图谋自立、海上郑氏后代占据台湾等各霸一方的局面,康熙不仅重视武备,并且大兴师旅,逐一进行平定,剿伐。在长期的战争中,康熙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军事思想和用兵策略。
康熙亲政期间,亲自筹划军旅之事,简阅军器;强调国家武备的重要性,认为承平之日更需严加训练士卒;在督军作战时,总能周详熟审,因情用兵,期于必克。
康熙执政初期,南方有“三藩”割据数省,西北有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割据,东南有郑氏的后代占据台湾,东北则有沙俄的觊觎和入侵。可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局势。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叛乱之后,接着进取台湾,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台湾郑克壤出降。此后,康熙为了对付准噶尔部噶尔丹的策划自立,于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和三十六年(1697年)三次率师亲征。五十六年(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帘扰西藏进行叛乱,为此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康熙是这些战争的最高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曾对臣下说:“用兵之道,朕知之甚明。部院诸事,朕向与诸臣商酌之,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划。”也正是在这些战争实践中,康熙逐渐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218康熙一贯反对穷兵黩武的思想,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欲除寇虐,必事师旅”。“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当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受到威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坚决主张用战争手段来平息封建割据,抵御外敌的入侵。
战争,并非康熙的嗜好也非他的首选。他看到“自古以来,好勤远略者,国家元气,罔不亏损”,因此,对于征伐之事总是尽力避免;
只是为了除暴安民,才不得已而为之。上述战争多数是国内问题,是为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战争;也有国家之间的问题,是对外反侵略的战争。为了领土主权的完整和人民安居乐业,无论国内问题、国家间的问题,都必须解决。康熙首先用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方不肯接受和平方式,坚持并首先使用武力时,才不得已而用武力回击对方,用战争制止战争,以达到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统一完整,人民安居乐业的目的。问题到了非用战争不能解决之时,不拿起武器,就会助长敌人的野心,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康熙说:
“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康熙的本意,但愿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不过,既然战争强加在了自己头上,他也木会屈服。“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师旅。”用兵是为了息兵,作战是为了去战。这是康熙对战争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各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当战争势在必行,难以避免时,他认为切不可苟图目前之安,容忍退让,而应全盘筹划,勇于进取,打主动仗,以安民为使命,图长治久安之策。康熙在始息兵安E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一劳而天下永逸,一勤而兵革永宁者,非大有志与断不能也。凡人狃于常习,卒然临之以事,必苟且图目前之安,不为长治久安之策。虽暂取逸于一时,终因循蔓延而不可收拾,往往悔诸事后,诚何益哉!予自临御以来,留心机务,每遇大政,则谋之以深沉,断之以果决。其始未尝不慎重三思,而其要则惟以安民为念。”康熙一生所经的历次战事,无不如此。
在战争中,康熙十分重视民心士气,认为城郭之固与山河之险均不足恃,战争胜负与国家安定与否的根本在于人心的向背,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还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由此可以看出他很注意人心向背的,相信众志成城,不以砖石长城为御敌之良策。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他在参加多伦会盟后的返京途中,对扈从人员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回京不久,有人建议修复古北口一带的边墙,康熙不予批准,驳斥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秦筑长城,随即灭亡;以后汉、唐、宋、明,历代修补,皆未能阻挡北方民族的勃兴。为此康熙还赋缭恬所筑长城》诗一首:
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
当时用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
军队是从事战争的基本力量。康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方针。他说:自太祖、太宗、世祖以至今,清军“野战必胜,攻城必克,历向无前”的原因,除了士卒英勇奋战外,“实由我朝军纪森严,信赏必罚,兼以兵马精强,器械整齐之所致”。即所谓“师出以律,可奏肤功”。因此,亲政之后他总是紧紧抓住以严肃军纪为中心的军队整建工作。
康熙在治军方面首重训练,他认为人皆“由学而能”,而部队军事素质的高低,全在训练的好坏。因此,提出官兵全须训练,并强调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训练方法和不同220的训练内容。并要求将领具备“才”、“勇”两个方面的素质,但高级军官应“尚智不尚力”,有“谋略学问”,所以极力提倡军官读书学习,知古今得失,懂兵法韬钤。他很强调军队纪律,认为“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从“得民心为要”的思想出发,强调军队纪律的核心就是不扰民。康熙讲究恤兵之道,要求将帅爱护兵丁,关心其疾苦,严禁克扣兵丁粮饷、剥兵以自肥的行为。为此,他强调指出,如不善于抚恤,“兵虽良,无用也”。此外,他十分重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并在清军中建立了专用火器的特种部队“火器营”。但他也不迷信火器,认为“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火器不是战争胜败和政权巩固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军队纪律直接关系战争的成败,因此每次出师之前,康熙都申明军纪。早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正月,吴三桂反叛之初,派遣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赴荆州时,就曾叮嘱说:“行军之道,惟得民心为要。所过宜厚加抚恤,严禁侵掠。”此前,曾谕兵部,详申军纪:“遣发大兵,原为扫靖叛逆,以安百姓。凡兵丁厮役,于所在地方,恐有恃强掠民财物,拆人庐舍,坏人器具,污人妇女,扰害生民,及损坏运河闸板桩木。统兵主帅,各宜体朕为民除叛用具之意,申明纪律,严加钤束。倘有违禁妄行,从重治罪。着即速行晓示。”在后来的平叛过程中,仍一再严申。但有些王、贝勒等竟带头违犯。诸如有人“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借端引日,坐失事机”;亦有人“干预公事,挟制有司,贪冒货贿,占踞利薮”;
“更有多方渔色,购女邻疆,顾恋私家,信使络绎”;“尤可异者,新定地方,亟需安辑,乃于所在,攘夺焚掠,种种妄行,殊乖法纪。”虽经一再警告,仍无显著改进。于是,在胜利之后,著令议政王大臣等举太祖、太宗军法,严行议罪。经奏准,将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等五人,一并削爵,并罢议政、宗人府等职。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被罚俸一年。其中情节最重的勒尔锦“仍令羁禁”。八名派出王、贝勒中,只有安亲王岳乐、信郡王鄂札立功受奖。由此可见执法之严。
至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1696年),又“规酌旧制,参以新谟”,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军令。这项军令共有十七条。其中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军队出征至凯旋善后全过程各环节、大小事项上的官兵守则:
一、大军出征,统兵将帅要“审视官兵甲胄弓矢,暨一切军中器用,务期坚利”。而且兵器、盔甲和马匹都标以单位姓名,违者追银。
二、大军启行后,自始至终,携规定行装,“按旗队以次前进”,不得紊乱,违者鞭责。
三、途中“毋离纛,毋酗酒,毋喧哗,毋叫呼”,违者即行捕责。
四、所经之地“不得扰害居民”,如侵犯子女,掠夺马畜,蹂躏田禾及擅离营伍,入村庄山谷,强取一物者,兵丁厮役,俱从重治罪。
五、士兵逃跑,在边境以内的,缉拿治罪;出边而逃的,追捕正法:追捕不获,往追人从重治罪;其主并该管官一并严处。
六、安营必须按旗列方位,不密不疏,越旗乱次者,将该管大臣官员分别治罪。兵役有盗窃军中物品行为者,视轻重鞭责或治罪。
七、出哨“勤加巡视”,隐蔽目标,备好马匹,及时报告敌情,“无寇妄报与寇近不知,以致传报稽迟者”’“将该汛坐哨官兵,立刻正法,军前示众。
八、值夜巡察官兵,必须高度警惕,对夜行者必问,衣服器械有异者擒拿,如贪睡偷安或人数缺少,从严治罪。
九、与敌相近时,管兵将军大臣要派人往探,掌握敌情和地势险易;严饬营中夜无燃火。
十、对敌列阵时,主将依敌我情况,指明各队各旗出击目标。进兵、收兵均鸣角以为号令。官兵擅离本队、本阵,或观望不进,“照所犯轻重正法、籍没、鞭责、革职”;分阵进击时,某旗队阵,敌坚222不动,即令所备援兵助击;但对面临阵时,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或不依次,喧阗拥入,或见敌寡,不请擅进,此次非但“功不议”,且“仍以罪论”。
十一、攻入敌阵,“不得掠人畜财物”,违者“重惩不贷”。
十二、敌退我追,“接踵继进”。
十三、师旋日,军器不得出售、存留给诸蒙古,违者从重治罪,该管官一并议处。
十四、随军驼马,妥善放牧、管理;如将遗失驼马隐匿乘用、或将瘦弱之马委弃宰杀者,严治以罪。
十五、官兵口粮,计口按日支领携带,“倘不如额,查出即从重治罪”。
十六、武官有亲随士兵者,不得再从营伍中抽调,以免分散兵势;无亲随兵,需抽兵随从者,只许各抽一名。
十七、大兵存驻时,“每日较射,磨砺器械”,不要闲惰。
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太祖、太宗以来行军作战的纪律,并结合新形势有所发展和创新。
康熙令兵部将此军令刊布颁行,对统兵大臣以军令为准进行升赏和处罚。军令内容比较全面,而其中心则在不扰民。康熙从实践中看到“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因此把军队纪律紧紧扣在不扰民这个主题上,又把不扰民和成功连在一起。用这一指导思想建设军队无疑是正确的。
在战争的指导上,康熙疆调战前要有周密的谋划和充分的准备,以期于必克;作战时,要因情用兵,相机而行。为此,他提出了“虚己以视机宜”的主张。“虚己”,就是因情应变而不固执己见。在战争中,他总是给予前线将领相机处理兵事的权力,反对凡事请旨而行的作风。
康熙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相机而行。他曾说:
“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机。”“一应军务,惟在相机而行,固不可急,亦不可缓。”“故为将者,必相机调遣,方能济事。”要做到相机而行,就必须“虚己以视机宜”,不固执己见,根据实际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方案。比如平定“三藩”之战,原先拟在湖南战场实行正面突破,派遣宁南靖寇大将军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率师赴荆州。但历时一年多,进展缓慢,各地形势又发生变化,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降贼,耿精忠割据福建响应吴三桂,尤其是陕西提督王辅臣叛降吴三桂,使得西北以及江、浙形势骤然紧张。因而,维护江、浙财富之区及京师侧翼,便立即成为了矛盾的焦点。于是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率师往攻岳州,借以牵制吴军阻其东进江浙;分别向浙江、江南、陕西、广东等地派出大将军。将正面突破改为先剪除东、西两翼,继而突破中路的战略方针,获得成功。至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福建耿精忠及广东尚之信相继归降清朝,这时才又将主要精力投入湖南主战场。进攻主战场的策略,根据吴三桂大力加强沿江防务的形势,也改正面进攻为迂回围剿。下令安亲王岳乐从江西进攻湖南长沙,以断贼饷道,分贼兵势,扼广西咽喉,并稳固江西门户。
要相机而行,还必须热知军队情况。在征剿噶尔丹时,康熙坚持亲征,朝臣有异议,康熙认为“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历其境,乃有确见。”由于亲自率军出征,能够及时直接处理军机,得以相机行事。“塞外荒漠,虽甚寥阔,而蒙古所行之路,所居之地,必依水草资生。是以亦有定所。朕于蒙古等行经路径,一一洞悉,所以遣发官兵,数道围困,皆扼贼之要害。噶尔丹迫蹙己极,计无所出,遂饮药以死。”在战争中,如敌众我寡,则兵势宜合不宜分。吴三桂为摆脱在湖南三面被围的困境,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四月,率众迁往衡州,派遣伪将军七人率贼兵三万至湖南南部的宜章,企图进犯广东,图谋两粤。这时,康熙一面令广东清军加强防守;一面派征南将军穆占,224会合大将军简亲王喇布规取衡州、永兴,“遏贼后路”。穆占遵旨,于收复茶陵州及攸县之后,乘胜南下,收复安仁、酃县,并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初,又连克郴州、桂阳,召降桂东、兴宁、宜章、临武、兰山、嘉禾、永兴等城,彻底粉碎了吴三桂进犯广东的企图。但因新收复地方增多,诸王不予配合,穆占不得不分兵防守,自驻郴州,以都统宜理布驻守永兴。六月,吴三桂集中优势兵力强攻永兴,战斗激烈,昼夜不息。都统宜理布等战殁,前锋统领硕岱率兵入城死守,情况十分危急。康熙也为之忧心忡忡。直到吴三桂死后,敌人撤退,才转危为安。简亲王和穆占都不敢丢下驻地驰援永兴,事后互相抱怨。对此,康熙则居中调解,劝他们彼此和衷,并总结永兴失利的教训,指出:贼以大军攻永兴,“有必死之形”,我方“兵势太分,以致失利”。此后,他进一步概括战略战术原则,说:“凡摧寇破贼,必审量己力,可击则击之。如贼众我寡,即宜调集诸路合为一军,壮其声势,以图攻剿。倘株守新复城池,以已经驻镇,惮于旋师,迟留疑畏,于大事殊无所济。”同样的道理,如果敌人四方煽动,形成联合之势,则必须分清敌人的主次,重点打击主要敌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他的势力最大,首先笈难,煽风点火,鼓动耿、尚两藩及其他势力随后叛乱。康熙综观全局,紧紧抓住了吴三桂和他盘据的湖南为主攻方向,“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吴三桂为“贼渠”,“湖南一隅,诚贼根蒂,四方群寇所观望。必速灭吴三桂,底定湖南,则各地小丑,闻风自散。”而且在对策上也有区别,对吴三桂重在剿,对耿、尚二藩则多用招抚。这也就是擒贼先擒王,使力量集中,切中要害,以带动全局;瓦解敌营,孤立贼魁。
在历次战争中,康熙重视并善于将战争与和平手段、军事与政治手段的结合运用。这里所说的和平、政治手段,也就包括和平谈判、和平交涉、招抚等措施。
平叛战争中,王辅臣在康熙十三年年底叛降吴三桂,清军将其围困于平凉、固原一隅。康熙十五年,大将军图海率军在平凉城北一战,击败王辅臣后,派人入城招抚,王辅臣投降。对此,康熙总结为:“剿抚并用”,说:“大将军图海,恭承简命,秉钺临边,即宣布恩威,剿抚并用,平凉一带,旬月绥平。”康熙下令将“剿抚并用”的策略推行于平叛战争的各个战场,要求对“叛变之人”,只要有“悔罪输诚之心”,皆可容受。康熙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在敕谕中申明了招抚政策:“今特颁敕谕,概示招徕。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人等,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或有擒杀贼首,投献军前,及以城池兵马来归者,仍论功优叙。”招抚或和谈成功的条件,一是力量强大,即首先必须在军事上有力量,有优势,这样才能迫使对方不得不降;一是真理在手,即促使对方服从正义,弃暗投明;一是政策优惠,即让对方看到投降比顽固到底更有出路。因此,在招抚时又须视具体情况、不同对象,而采取不同的具体办法。
康熙平定三藩,分主次对待。以吴三桂为主要敌人,进行重点打击。对福建的耿精忠则认为其“必系一时无知,堕入狡计”,因而一再派人前去招抚。至康熙十五年九月,清军收复建宁、延平等府,耿精忠无力再战,于十月初四率众投降。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酹,率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叛逆,“图功赎罪”。
广东尚之信与耿精忠的情况相似。康熙抓紧招降福建,为广东作出榜样。耿精忠投降后,尚之信在军事上没有出路,也主动降服。康熙令其“相机剿贼,立功自效”;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也各复旧职。
对其他参与反叛的吴三桂手下人员,也多次招抚。康熙指示:叛乱之罪在吴三桂,“与胁从之人无涉”,如能悔罪投诚,“概行宽免”。即使对吴三桂,亦不排斥招抚。康熙说过,吴三桂“果有悔罪输诚之心,亦何不可容受。”对被招抚者的政策,总的是来归者得到宽大;降比不降有利。但226政策的具体内容则不尽相同。如平叛战争中的投诚官兵,初为优升职级,以原班人马投入平叛战争;后来降者增多,战事减少,一般情况下则尽量避免降人聚集在一起,因而降官进京陛见,然后或立即擢用,或候缺补用;降兵或自愿归农,或补充绿营兵。战争后期招抚对象集中为吴三桂手下的骨干成员,康熙认为他们不属胁从者,其投诚后又令回南方保护家口,以作内应。这些举措实是招抚与反间相结合,扩大敌营嫌隙和狐疑。但降而复叛者不再予招抚,而从严处理。
康熙指示:初叛被胁迫,降而复叛,“则甘心附贼可知。罪情重大,国法难容,不许招抚,亦不许其投诚”。对这种人,逮捕后处理极严,一般是本人磔死,家口籍没。
在征讨噶尔丹的战争中,剿抚并用又是一番不同的情景。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大败而逃,曾声明知罪,发誓不再进犯中华皇帝之喀尔喀及众民。但随后又背弃誓言,与清廷为敌。康熙决定亲征,一切部署就绪,即将开战之时,曾遣使往说,还带去敕书。其中主要是历数噶尔丹的罪行,并正式宣战,使其惊逃;当然也有招抚之语:
“觌面定议,指示地界”,免失万一的和平解决之可能。之后,仍一再遣使,颁谕招抚噶尔丹,促其欲降从速,许诺若肯来降,亦待以显荣。但针对噶尔舟的剿抚并用政策,显然以剿为主。而对其部众则大力和大量地招降、收纳,并妥为安置。
在与台湾郑氏集团的战争中,与三藩、噶尔丹又有不同。郑成功原系南明郡王,反清,占据台湾,阻碍祖国统一。但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行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清政府要实现国家统一,是正义之举,但水师薄弱,收复台湾的力量也尚感不足。所以康熙先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抚为主,多次遣使、贻书,晓以大义。双方多次举行和谈,谋求和平统一的办法。而且,清朝目标仅在将台湾与大陆统一,辖于清政府,并不取缔郑氏势力,台湾仍可任其居住,凡来降者待遇优厚。后来,在郑氏集团坚持不受招抚的情况下,康熙转而重点招抚郑氏下属官兵,并削弱、瓦解其势力。最后才决定以武力攻取台湾。经澎湖激战,全歼郑军主力后,再事招抚,郑克壤率众投降。此时,康熙仍以宽大为怀,予以接纳,肯定其“纳士归诚”之功,授以公衔,一切人员也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抗击沙俄侵掠中,以进行武装反侵略战争为主。但康熙也并不放弃和平手段,对沙俄长期反复进行忠告、交涉、倡议、谈判,力争不死人、不流血,划定地界,共同遵守,以达到促使俄国从中国撤兵,实现边界和平的目的。当这些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不得已而用兵之后,侵占雅克萨俄军战败投降,康熙仁至义尽,令勿杀俄俘,一律释放,遣返回国。
康熙之所以热衷于寻求政治的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哪怕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不放过;轻易不肯诉诸武力,是他始终认为战争非善事,对人力、物力损伤太大,只在不得已时才被迫为之。和平交涉、谈判、招抚,如果能解决问题,既可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和财物的破坏,又可分化瓦解敌军,争取来归,从而孤立最顽固的敌人,加速胜利进程。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康熙一生虽战功卓著,但从不穷兵黩武;
虽武艺高强,但并不迷信武力。即使战争在残酷地进行中,也尽可能地减少杀伤:敌军士兵只要放下武器,即留其一条生路;其军官投诚,亦得宽大乃至优待。可以说宽仁二字,不仅是他的政洽思想,也渗透在他的军事思想之中。
军事思想在康熙的思想体系中颇具重要地位。它的来源,除儒家的传统思想之外,较多地继承了满洲祖先的宝贵经验,也兼有法家、兵家学说中的精华。康熙将其全部附会成儒家学说的成就,这可能是为了争取和团结汉族士大夫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康熙读《左传》的一则感受,可供参考。僖公二十七年冬,楚国及诸侯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欲伐与楚关系密切之曹、卫,借以救援宋。选拔元帅时,有人推荐郁毂,理由是他“说礼乐而敦诗书”。经全面考核:观其志向,考其事功,报其劳绩,感到条件具备,便委任为中军元帅。后来又经228使民安居、示信知礼等步骤,才“出谷戍,释宋围”,并于翌年与楚国战于城濮,终于成为霸主。但(佐传》却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康熙读后,在《古文评论》中以《亚文公始霸》为题,这样写道:“晋为三军谋帅,而必日说礼乐、敦诗书;以战功取霸,而必日文之教。此等议论识见,非三代以下人所及。”看来康熙就十分欣赏这种表达方法。
康熙在战争中还能够做到知人善任,信者不疑。统一台湾时,康熙宣称自己不熟海战,全权委之于前方将领,因此选任贤才对于整个战争的成败就显得至关重要。康熙见现任水师提督万正色“不能济事”,便力排众议,采纳李光地的建议,任命施琅“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而且极为信任,以为施琅不去,“台湾断不能定”,并授予专征大权,表现了超人的胆略和气魄。后来事实证明,施琅果然不负皇帝重托,在姚启圣、吴兴祚等人的大力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统一台湾这一伟大任务。
对其他统兵大吏,康熙也主张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关怀。他在斛筵绪论》中写道:“今言官论事、论人,多指摘瑕疵,但见及一偏,而于大局全体所关,不能审度其轻重。即如用兵之地,督抚大吏职任至重,至其制备鞍马、招募技勇、激赏将士以及供馈官兵之费,势与内地不同,倘复事事苛责,恐隳其任事之心,亦将何以展布其手足?”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与福建巡抚吴兴祚共同商定,互相配合,分别收复了海坛岛及厦门等地。得旨嘉奖,下部议叙。然而兵部却认为是万正色弄虚作假,“密遣人至伪总督朱天贵处,预定投诚,然后率兵进取,以致各岛败遁,恢复空地,并无杀贼、攻克之处。”为此迟迟不予议叙,并上疏建议:“应俟提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明白回奏之日再议。”康熙认为兵部是毫无根据的“妄奏”,并驳斥说:“进剿海贼一案,原系吴兴祚、万正色会同定议,不俟荷兰国船只,即奋勇前往,志靖海氛”,从而“克奏肤功”。尔部乃称万正色与朱天贵密约投诚,任意妄奏,“以为滥冒军功,殊属不合,着遵前旨,即行议叙。”按照传统思想,有所谓“穷寇莫追”之说,而在康熙的军事思想中则与之相反,三次亲征噶尔丹即是最好的例证。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三十日至六月九日首次亲征,出师漠北,于昭莫多全歼噶尔丹主力,使蒙古族欢欣鼓舞,清朝声威大振。但因噶尔丹率少数残敌脱逃,仍是隐患。于是在同年九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日举行第二次亲征,出师归化城及河套地区,指挥清朝将士及西北各部族,沿阿尔泰山西南侧及新疆哈密一带,组成一道防线,过往之达赖喇嘛使者、青海台吉使者及噶尔丹使人、亲侄、亲子塞卜腾巴尔珠尔等,均被截获。其部众纷纷归降清朝,噶尔丹仅率少数部众被困在阿尔泰山的密林深处。“收降其部众,遏绝其外援”的目的至此也完全达到。回京休整刚刚一个半月,又于翌年二月初六,第三次亲征,出师宁夏,亲自部署出兵征剿及招徕青海台吉等事。所谓“用兵之道,要在乘机”之谕,就是康熙在这次行军途中对扈从诸臣所说的。其全文是:“凡用兵之道,要在乘机。噶尔丹穷迫已极,宜乘此际,速行剿灭,断不可缓。朕今亲临宁夏,相度机宜,调遣军士,贼闻之必魂魄俱丧,其部属亦必张皇。而别部蒙古闻朕亲临宁夏,各欲见功,扼噶尔丹而图乏。彼若不自尽,亦必为人擒献。克成大事,正在此举。”康熙在这里就强调了连续亲征,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的必要性。由于西藏第巴受到斥责,并慑服于皇帝的兵威,态度开始转变,因此招徕青海诸台吉异常顺利,遣使往谕,“俱己归顺”。西路征剿之师于闰三月十二日派出后,四月十五日便接到噶尔丹自杀的死讯。康熙总结,认为全歼噶尔丹至关重要,“使少留余息,彼必复聚,难以遽灭矣”。
康熙三次出师是统一的一个整体步骤,缺一不可。康熙在他的《论息兵安民》一文中这样说:“方噶尔丹之盘踞土刺河也,诸蒙古为之心动。非毅然亲统六师直穷巢穴,迫而与之一战,必不能丧其魄而歼其众。及其败遁也,非严冬再出,久驻塞外,绝其所往,或奔匿230他所,更费经营。春和之期,非跋履山川,分道进讨,示予不惮寒暑勤劳,必欲灭此而后已,则彼尚或支吾岁月,妄图苟延。三举一有不决,则机左师老,必致疲我苍赤。”康熙对古代兵书中的谋略思想并不完全否定,他能主动吸纳并付诸于实践。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经议准,认为《孙子》、(俣予、《司马法》三书“议论近正”,武举者试可依此三书出题。
但他主张有选择的阅读,要摒弃其中脱离实际、荒诞不经的内容,并要结合实际运用,反对生搬硬套。他在槲筵绪论》中就这样写道:
“自十二年用兵以来,尝取前人韬略武备等书阅之,亦皆纸上谈兵,无益于事。间有用符咒法术者,尤属不经。”他总结古代车战之法被废的原因时指出:“由今思之,不独山林原隰难于驰驱,即平衍之地亦不易用。盖一车之中,左主射,右主击刺,居中者主御,或有一人不用命,则胜负所关不小。此后世所以难行也。”他在《阅史绪论》
中,对宋高宗时吴磷以新立“叠阵法”取胜,也表示出了怀疑。他写道:“锋镝相接,迅不及停,何暇约计为百步则用神臂弓,七十步则用强弓,从容拟议?若是耶,是皆全不知兵,徒于纸上谈之,乃谓以此取胜,恐未必然。”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九月,总兵官马见怕以《武经七书》注解各异,请选定一部颁行。康熙对此评论说:
“赋经七书》,朕俱阅过,其书甚杂,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战,皆是虚文。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台湾,平定蒙古,朕料理军务甚多,亦曾亲身征讨,深知用兵之道。七书之言岂可全用。”接着他还举例说:“昔吴三桂反时,江南徽州所属叛去一县。将军额楚往征之。有人献策于贼云:‘满洲兵不能步战,若令人诱至稻田中,即可胜之矣。’岂知满洲兵强勇争先,未及稻田,已将诱者尽杀之。此献策之人,亦为我兵所杀。用赋经七书》之人,皆是此类。”总之,康熙对兵家印象不佳,认为大多近于阴谋诡谲,因此不甚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