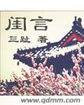“来人……采薇……采芷……”床榻上的清浅声音沙哑,虚弱无力地叫着。
“小姐,你可算是醒了!”采薇喜道。
清浅看了看四周的景象,发现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房间宽敞,颇有雅韵。她睡在烟罗色绡花锦帐里,身上盖着蓬松绵软的云被。“这到底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里?”
“小姐你忘了?那日马惊了,我们几个命悬一线差点就落崖了。”
清浅正想着,觉得背部十分疼痛,稍微一动就撕扯办的疼痛,她不禁吃痛。揉了揉太阳穴,才想起那日被刘喜弟弟追杀,后来马又惊了。“那这里是?”
“这里是雍京的林大人府上,是他救了我们。”采薇从容道。
“那修白呢?修白怎么样?采芷呢?”清浅急切地问。
“没事没事都没事,”采薇拍拍清浅的背,给她顺顺气儿道:“小姐毋须担心,修公子和采芷都无甚大碍,采芷在外间睡着,修公子在隔壁那房里睡着,等他们醒来,自会来看小姐的。”
“没事就好。这林大人是什么人?”
“是雍国的太医林澹台,听他的丫鬟说,那****外出打猎,正巧在树林里看到我们受伤,就把我们救回来了。”
“这样说起来,林大人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采薇,你扶我起来,我去当面谢过他。”
正拾掇间,门被轻轻扣了三声。清浅眼神示意采薇,采薇遂道:“谁啊,进来。”
一人推门而入,是修白。他已换了一袭斜襟的白袍,纤尘不染,长身玉立。真可谓是: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他走到清浅身边,温柔道:“姐姐起来了。伤可好些了么?”
清浅微微道:“无碍。修白,你那日受了多处刀伤,现下可怎样了?”
修白道:“不碍事,伤口都已敷上药,也并未伤到筋骨。只那一下撞击严重些,头还有些昏昏得。”
清浅担忧道:“可别伤着了头脑罢,这必得寻个大夫来给你瞧瞧,我才放心的。话说回来,昨日是怎么回事?怎的你的功夫一下变得那么强?”
修白道:“昨日情急之下,冲破了经脉,想来是太急了,才使出了超越限度的功力罢。”
清浅点头道:“你的功夫能使出来了,我总归是替你高兴的,”忽又陷入深思道:“我想起一事,那日马惊了,可怎的就惊的那么巧合。恰好就有人来追杀,恰好又惊了马?”
“我当时也奇怪,现在想来,倒不是件难懂的事儿了。”
“莫不是当时那个卖马的,和刘喜他弟弟是一伙儿的?让我们就算不被杀死也被马给带下崖去?”清浅说出心中所惑。
“姐姐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事情八成就是这样罢。那小贩趁着给我们套马的机会,不知使了什么手段,让那马走到半途就惊了,然后在这样危险的情形下,再重重给我们来一记追杀,这样就算是阎王不收,我们的命多半也保不齐了。”修白和清浅不谋而合。
“若不是你冲破了经脉,若不是那马终究没有冲下崖去,若不是我们被人所救,此刻我们已在阴间相会了。”想到此节,遂倒吸一口凉气,为了报仇,刘喜弟弟好缜密的心思。
采芷推门进来,见到三人俱在,不由得放下了悬着的心。她憨憨地笑着道:“小姐,修公子,你们都在这。我醒来见到独我一人在一陌生屋子里,还以为你们都怎么了呢,哭了半会子呢。”
采薇见采芷没事,神志也很清明,心下十分安心。却假意恼道:“呸呸呸!莫不是咒小姐和修公子么,若不是看你还有伤,我早把你这舌头给割下来,看你还说不说。”
采芷蹭到采薇身边赔笑道:“好姐姐,我知你最疼我的,喏,我把舌头给你,你自去割吧,我也并无什么怨言。”
采薇笑的忙追着采芷打,说要把她的嘴给封了才罢。清浅捂着嘴在一边儿笑得前仰后合,修白也微微地眯起了眼,嘴角上扬。
清浅止了二人的打闹,正色道:“这次被这林大人所救,该第一时间去当面致谢的,我们这就去罢。”
清浅打发了采芷去问,知道那林大人在前厅等他们,四人遂往前厅而来。一路上曲折游廊,皆以小石子铺路,两边种着各色植物,游廊边还有一小溪流过,十分的精致清雅。及至前厅,又是一番气象,雅致却不奢华。
一个年过半百的男子坐在主位,面目祥和,十分泰然。清浅忖度着这大抵就是林大人没错了,遂走上前去,盈盈行了一礼:“阮清浅参见林大人,谢过大人救命大恩。”修白与采薇采芷三人也依样行礼。
那林大人忙扶了上来,笑道:“不碍事不碍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况且那日林某也是凑巧路过那里,见各位重伤,哪有不救之理。”
清浅正要答话,见门口大剌剌地进来了一个人,那人满目含笑,摇着一纸折扇,扇上却又没有书画,只是白白一片,十分奇怪。远观那人面貌,竟是说不出的俊朗飘逸。丰姿奇秀,眉眼含情,面如冠玉,目若点漆。黑发绵绵如泻,只轻轻绾了垂在背上,一袭玄青色常服,袖口淡淡地绣了几株兰花。大修白几岁的模样,比之修白,竟是另一种的温煦灵动。
那人笑道:“林大人有远客至,在下也来凑凑热闹,不知可欢迎否?”
林大人拘不住脸上的喜悦,哈哈一笑道:“不妨不妨。公子不弃吾等粗鄙已是幸事,夹道相迎尚且来不及,怎会不欢迎。”
那人趁大家不注意,向修白斜斜挑了挑眉毛,却转头对林澹台道:“林大人客气了。”
修白心中有一丝惴惴,自忖这人是否会信守两人诺言,抑或是今日刻意来刁难的。正出神间,听得那人问道:“林大人有客,可否为在下介绍介绍?”
那林大人和颜悦色道:“这是阮小姐,呃,不知这位是?”
清浅见林大人介绍修白,忙道:“这位是我义弟,名修白。”
修白便向林大人行了一礼,却并未抬眼看那人一眼。只听得那人笑道:“好一个阮小姐,竟是如此人物,天人丰姿,这位义弟也是如此俊秀超尘,卓尔不凡。不知阮小姐名什么?表字什么?”
清浅从未听过旁人对她如此直白的赞扬,不由得脸上飞红,因而羞涩答道:“小女名清浅,并无表字。”
那人念念有词道:“清浅,清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好名字。哦,我忘了自我介绍了。”
林大人欲为清浅等人介绍道:“这位是……”
正要说间,那人打断道:“我自己来。”林大人被生生抢白,却丝毫不觉得被拂了面子,戳着他的心口笑道:“你的主意最多。”
那人进而温和对清浅道:“在下姓容名澈,邶国人。与林澹台大人乃是忘年至交。在下常常在各地行商,近日来到雍国,便赖在他这里白吃白喝。行商的妙处在于游览大好河山之时也可赚得齐家之资一二,自是快活。”言笑晏晏,竟还有一丝得意。
清浅心想,这人怎的如连珠炮一般,突突突地说了这许多,看着人是个出尘不俗的面貌,却如何是这等不羁的性子。遂一笑算是回答。
修白向着容澈怒目,意为:你今日如何要来趟我们这趟浑水,还嫌不够乱,若是要耍,趁早去了别处。
容澈偏偏当作没有看见,嘻笑对清浅道:“阮小姐是哪里人?”
清浅只得答道:“小女是卞国人,来雍国寻亲的,不想路上马惊了,幸得林大人相救,才得今日运气在此畅言。”说罢又盈盈向林澹台行了一礼。
林澹台忙扶起,又陪笑着站在边里。容澈斜倚着一张檀木椅,慵慵懒懒,却别有风姿,清浅不觉看得呆了。容澈摇着折扇,打趣道:“那这么说林大人可真是做了件好事,这么天仙似的姑娘,偏偏被你给救了,怎的这好事就从不被我遇到。”
清浅脸上飞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怯生生的模样哪像个公主,分明是寻常人家的娇娇女儿。修白本在一旁怒视容澈,怨他说这么些出格的话,谁料一转眼看见清浅满脸朝霞的模样,竟来不及怒,径自看得痴了。
林大人见气氛尴尬,忙圆场道:“阮小姐、修公子才刚醒,身上伤口还未完全愈合,若是再给累着,便是老夫的错处了。来啊,传膳。阮小姐,修公子,容公子,这边请罢。”
清浅和修白谢过,只听那容澈说道:“你们吃罢,我还有事,晚上再回来。”说罢径自走了。清浅觉得此人好生奇怪,行事作风皆不拘一格不讲礼数,风一样来风一样走,实在是琢磨不透。想罢便随修白一起,由采薇采芷相携着,往饭厅去用膳。
到得饭厅,各式菜色均已上桌,林澹台坐了上座,清浅伴在他的右下首,修白在左下首。采薇采芷虽是丫鬟,但得林大人赐座,再者她二人也还带伤,清浅遂准了二人同桌用膳。席间言笑晏晏,气氛十分和睦。
待得饭毕,林老爷问道:“阮小姐从卞国来,大老远的,吃了不少苦吧?”
清浅一笑道:“吃苦谈不上,与弟弟和丫头们有个照应,路上也可相互作伴。然而路远却是真的,清浅离家已然四月有余。”
林澹台笑道:“姑娘家家的不容易啊,还遇到了惊马这么危险的事儿,不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修白抱拳道:“我和姐姐的命权仗着林大人所救,正所谓滴水之恩该当涌泉相报,若大人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姐弟两个的,尽管开口。修白一定在所不辞。”
林澹台赶忙拦住修白道:“莫再行礼了,老夫这把老骨头都要被折煞了。”
清浅道:“林大人该当的。”
“你的伤也不重,若没有被我爹所救,看你命这么大,多半也不会死。”门外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听起来不甚友好。修白回头一看,是一个姑娘,身量和清浅差不多,着一件流苏粉带裙,外着银丝滚边小褂,环佩叮当,珠翠满头,正面无表情地看着清浅。
林澹台听到,面色一黯,怒气上浮道:“暖苏,你怎的如此无礼,对客人说话怎能毫无教养!”
岂料那叫暖苏的女子连厅也未进来半步,只不轻不重地撂下这一句,便袅袅挪挪地走了。阮老爷的话她好似未闻,头也不回打门口过了。
林澹台顿觉颜面无光,十分愠怒,却又不好对清浅修白等发作,只得道:“阮小姐,修公子,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这是犬女林暖苏,她并不是针对你无礼,而是用这种态度来气我。”
修白道:“林小姐这是为何?”
林澹台“唉”的一声道:“修公子有所不知。雍国惯例,凡是雍国七品以上官员,但凡有女年满十四还未婚配者,则必须参选三年一次的选秀。今年暖苏刚好十四,恰逢新届选秀。她被我惯坏了,竟养成了个不受束缚的性子。与家里管家的大儿子是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情分,不知何时竟非君不嫁了。孽障啊,小姐和奴才怎能举案齐眉。我为她报名去参加选秀,她怨我恨我,已有一段时间了。”
清浅似有感悟道:“其实情有独钟,哪分什么高低贵贱呢?林小姐乃是痴情之人,奈何惯例在此,不得不从。命定何人,自有天数。这样不平也是无用的。天子撂了牌子倒好,若是一旦留了牌子,那就毕生都是宫里人了。”
林澹台道:“眼看这选秀之期眨眼就到,她知道不可逃避,就如此针锋相对。”
清浅不禁想起父皇**的那些女人,包括自己的母亲,有哪一个是幸福终老的,为名分斗,为利益斗,为后嗣斗,斗来斗去,陪了性命还搭上了青春。就像是花园里的花朵,盛开过,美丽过,终究零落成泥碾作尘,凋谢得静悄悄。
修白道:“林老爷莫要伤神,在下相信林小姐若是明白大人苦心,一定会懂事的。”
林澹台无奈地点点头,又为三人查验了伤口,都无什么大碍了。清浅谢过,又与林澹台交谈几句,遂领着丫头和修白回房了。